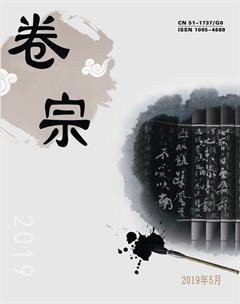論楊伯峻《論語譯注》的語言文獻價值及疑誤分析
摘 要:楊伯峻《論語譯注》是研究《論語》的重要注本。其對語言文字的嚴謹考究與訓釋應當引起從事古代文學研究學者的充分借鑒,它澄清了眾多前代學者對《論語》研究的紕漏之處,使字句訓詁與思想闡發更具科學性。本文主要研究《論語譯注》的語言文獻價值,在合理認識語言尤其是上古“文言”與文章義理之間的密切聯系后,深入分析闡釋《論語譯注》中語言文字的考證對解讀《論語》的影響,有利于促進學者對《論語》思想的深度剖析挖掘。但受古漢語語言特征和文獻因素影響,楊伯峻的《論語譯注》仍存在著些許弊端,部分語言文字訓詁不當導致人們對孔子思想的解讀出現疏漏,這必須引起人們的重視,并對其中的疑誤問題作出合理闡微。
關鍵詞:論語譯注;論語;語言文獻;疑誤
從《論語》的各種版本或研究著作來看,語言學問題似乎成為解讀《論語》的重要影響因素。語言是文學的基礎,語言闡釋出現問題則直接妨礙了人們深入挖掘文章的義理內容。楊伯峻在《論語譯注》中論證“《論語》大概成書于戰國時期”,依此判斷,《論語》中的語言尚可歸于先秦古漢語體系。陳桐生在《商周文學語言因革論》一文中明確指出“春秋戰國時期的語言面貌尤其是語法現象沿襲了上古甲骨文卜辭、銘文、西周散文所體現出來的特點,古今字、通假字、特殊句式以及此類活用等語言文字現象成為春秋戰國時期 ‘文言的主要語體特征”。《論語》作為該時期“文言”的代表作正體現了這一特征。但必須注意的是,正因其語言文字呈現出的簡奧性才導致世人對《論語》的解讀或注釋萌生了很多模糊之處,諸如錢穆《論語新解》、程樹德的《論語集釋》等相關著作都觸及該問題。而楊伯峻《譯注》格外注意到訓詁學對思想闡釋的影響,著重從語言文獻考釋的角度出發,對字句進行嚴密推敲和斟酌,成為眾多版本的翹楚,體現了其身為語言學家、古文獻學家在考究詞句上的嚴謹精神。吳文學曾對《論語譯注》評價稱“注重字音詞義、語法規律、修辭規律及名物制度、風俗習慣的考證,論證周祥、語言流暢,表述清晰準確,不但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更是普遍讀者了解《論語》的一本入門參考書。”即便如此,《論語譯注》亦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語言訓釋方法的弊病,須引起我們仔細審視。
1 《論語譯注》的語言文獻價值
1.1 《論語譯注》對語言文字的訓釋
《論語譯注》最大的特點便是對《論語》字句的考證和訓釋,這也是超乎一般注書的學術價值所在。但凡有細微的語言障礙,楊伯峻都會引用古代字書以及其它《論語》注本進行訓釋,這也構成了《譯注》與錢穆《論語新解》、毛子水《論語今譯》等著作的顯著差異。首先,體現在楊伯峻對《論語》語言文字的全面注釋上。《譯注》于開篇《導言》里就對“論語”一詞作了精細的解釋,作者分別例舉了班固《漢書·藝文志》和清代劉熙《釋名·釋典藝》的意義,而后把“論語”總結為“語言的論纂”。該定義相較于其它版本更具備學理性價值。《論語·憲問》“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楊伯峻將“溝瀆”訓釋為《孟子·梁惠王》出現的“溝壑”,同時又引王夫之《四書稗疏》,這里指地名,即《左傳》的“句瀆”,《史記》的“笙瀆”,如果依此解釋,那么孔子的“匹夫匹婦”就是指“召忽”而言,恐不可信。楊伯峻為使文意闡述明晰,廣泛引用了對同一詞解釋的不同著作,盡可能還原當時語境;再如《論語·鄉黨十》“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譯注》“躩,音躩,皇侃《義疏》引江熙云:‘不暇閑步,躩,速貌也。”楊伯峻引用了皇侃的《論語義疏》作為釋詞依據;《論語·先進》“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譯注》“槨,也作‘槨,音果。古代大官棺木至少用兩重,里面的一層叫棺,外面的一層叫槨,平常我們說‘內棺外槨就是這個意思。”楊伯峻對《論語》字詞的考證不僅停留在單純的訓釋上,更從語音、文字現象等方面著手為字詞作了較為綜合全面的訓釋,這在《譯注》中頻頻出現,為人們研究《論語》提供了比較精確的語言基礎和文獻資料。
其次,楊伯峻《論語譯注》為深入考證里面的字句而旁征博引,廣泛搜集了古今文獻材料,他例舉了《論語注疏》、北宋朱熹《論語集注》、清劉寶楠《論語正義》、程樹德《論語集釋》、楊樹達《論語疏證》以及皇侃《論語義疏》等重要有關《論語》的研究成果和文獻,并從中吸納了許多觀點,亦遵循歷史性原則,所征音文獻數量蔚為大觀。尤其是從名物典制、地理山川等各方面進行考證。如《論語·八佾》“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吾愛其禮。”在《譯注》中,楊伯峻明確地把“告朔餼羊”釋為古代的一種制度。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歷書頒發給諸侯。這歷書包括那年有無閏月,每月初一是哪一天,固之叫“頒告朔”。諸侯接受了這一歷書,藏于祖廟。每逢初一,便殺一只活羊祭于廟,然后回到朝廷聽政。這祭廟叫作“告朔”,聽政叫作“視朔”,或者“聽朔”。當時西周時期的禮儀制度被諸侯國采納接受,事關宗廟社稷,不可輕視。在《禮記》等記載周代禮儀制度的書中可以發現很多與此相關的典章儀式。楊伯峻充分認識到了《論語》中蘊含的周代禮儀文化,同時又引用其他文獻進行佐證,這在《譯注》中十分常見;再者如《論語·子罕》“‘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對此,楊伯峻引陸機《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將“唐棣”解釋為“郁李(薔薇科,落葉灌木)”,又引李時珍《本草綱目》“枎栘(薔薇科,落葉喬木)”之意。雖然本句話的內涵與“唐棣”究竟為何意的關系并不密切,但楊伯峻還是秉持著文獻學家的嚴謹態度征引它文為原本模糊的字詞作出合理解釋。《本草綱目》為醫學著作,和文學關系十分生疏,楊伯峻沒有遺漏其里面記載的植物名稱和特征,進而細細搜求,足以見得他對語言文字的考證之全面深入,打破了眾多注本僅僅從原著出發進行考證的僵局,開拓了訓詁學的新局面。
除此之外,楊伯峻對《論語》中同一問題在其它文獻的不同詮釋采取了合理的分析態度。他并沒有按部就班,而是經過明辨之后選擇。如《論語·顏淵》“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也。”《譯注》將“遠”釋成“難以存在”意,但“遠”本是“離開”、“逋逃”之意,很多《論語》注本亦如此解釋。而楊伯峻卻認為“難以存在”更符合子夏本意,他在旁征博引的同時卻并未忘記斟酌思考,并予以仔細斟酌,對《論語》中頗受爭議的字詞作出了合理的解釋,通過還原具體語境來佐證詞義的靈活性。《譯注》對語言文字考證之細密、分析之合理超出了很多當今《論語》的注本,即便是同樣有一些訓釋誤區,但就其引用的文獻之多,涉及領域之廣,亦使得《論語》的注釋更具科學性。其意義遠超出過分牽強附會的注本,促進了人們在解讀經典時對語言文字等基本文獻的思考。
1.2 《論語譯注》先秦古漢語語法發微
《論語》其作為上古先秦時期的語錄體著作保留了上古甲骨文卜辭、銘文、西周散文的語言特征,尤其是語法方面。在語言學現象中,語法變化最為緩慢,故《論語》作為 “文言”亦繼承了前代文學語言的語法規律特征。楊伯峻在訓釋《論語》時敏銳地注意到了語法問題,所以他并不滿足于單純釋詞解字,更重古漢語文言語法特征對闡述文意的影響,周密分析《論語》的語法現象。
其一,楊伯峻《論語譯注》仔細甄別通假字、古今字、異體字等現象。如《論語·雍也》“子曰:‘君子博學以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楊伯峻將“畔”釋為通“叛”,兩者是通假字;《論語·公冶長》“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棁,何如其知也?”,楊伯峻于《譯注》中釋“知”為“智”,明確了兩者為古今字,意義相當。《譯注》中對文字現象的語法闡釋極其常見。
其二,楊伯峻《論語譯注》對詞類活用的解釋較為周全合理。如《論語·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楊伯峻把“行”解釋為作名詞用,舊讀去聲;《論語·學而》“有子曰:‘信近于義,言可復也。恭近于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楊伯峻仔細分析了“遠恥辱也”的“遠”意,這里的“遠”應該讀去聲,因為作動詞,是使動用法,釋成“使之遠離”的意思。詞類活用的現象在先秦語法中時常出現,《論語》里不勝枚舉。《譯注》使人們清楚地認識到詞類活用現象,有助于準確理解文意。同時,楊伯峻于《譯注》最后部分創新性地設置了《論語》詞典篇,統計歸納了同一詞在《論語》里出現的不同場景而分別體現出來的詞類活用意義,突出了楊伯峻身為文獻學家的索引意識。
其三,楊伯峻《論語譯注》對詞法、句法語法構造規律的分析明晰嚴謹。如《論語·為政》“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存,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楊伯峻將“施于有政”的“有”字釋成無意,加于名詞之前,并分析稱這是古代構詞法的一種形態,引楊遇先生“政謂卿相大臣,以職言,不以事言”;《論語·雍也》“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楊伯峻說道:“之”字不是代詞,不是“亡”的賓語,因為“亡”字在這里不應該有賓語,只是湊成一個音節罷了。古代常用這種形似賓語而賓非賓語的“之”字,楊伯峻對《論語》的語法進行解釋時著重參照了《文言語法》,以統一的語法規則來具體分析《論語》中形形色色的語言現象,足見其對句中語法規律的認識;《論語·雍也》“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楊伯峻釋“也”為語氣詞,表“人之生”是一詞組作主語,這里作一停頓,下文“直”是謂語。他從句法規則出發,細密地分析了句子中的每個成分,對其語法現象做了詳盡的敘述,助人們在艱深晦澀、復雜的文言古漢語語法中克服困境,更易觸及思想實質。
其四,楊伯峻《論語譯注》的今譯更側重對整個句子進行完整清晰的表述,盡量顧全句子成分,將原句模糊兩可的地方盡量補足解釋,而非意譯。如《論語·公冶長》:“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譯注》謂:“子貢說:‘老師關于文獻方面的學問,我們聽得到;老師關于天性和天道的言論,我們聽不到。”原文中沒有主語,但楊伯峻在翻譯補了出來,這樣才使得句法成分完整,句意流暢自然。文言表達原本簡練精奧,詞義具有凝結性,如若忽視,很可能在今譯因錯失成分而使義理闡發陰陽顛倒。孔子的思想理念因《論語》今譯不當而導致誤讀的后果司空見慣,楊伯峻從文言的表達效果出發進行翻譯,一定程度上使人們規避了閱讀盲區。
2 《論語譯注》的疑誤分析
楊伯峻《論語譯注》由于受個人對孔子整個思想體系理解的局限、文獻考證、以及意識形態的傳統性等因素影響,對《論語》的解讀出現些許紕漏,引起了人們的疑惑。以往學界對《論語》的研究更多地建立在對孔子思想的批判或認同基礎之上,而并未太多從《論語》本身出發進行文獻學角度的研究,導致里面存在的疑誤現象尚未得到解決。盡管《譯注》確實是諸本中的權威,但它對某些語言文字的誤釋嚴重歪曲了孔子的思想體系,在某種程度上削減了《譯注》的說服力和可信度。
如《論語·泰伯》第九章道“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根據鄭玄、何晏、朱熹等人的注解,楊伯峻將這句話譯為:“孔子說:‘老百姓,可以使他們照著我們的道路走去,不可以使他們知道那是為什么。”所以長期以來人們都把這句話定義為孔子的愚民思想。暫且不說其它問題,若宏觀地從孔子整個思想體系來看,該處就應引起充分審視與思考。孔子極力提倡教育,且在當時興辦了最早的私學。他自然希望更多人掌握知識以致其所創立的儒家學說可為廣泛傳播,并為眾弟子與其它知識分子所接受。如果孔子認定 “民”“不可使知之”,那他就完全沒必要“教民”,也不可能達到其“克己復禮”的政治目的與人生信念,二者自相矛盾。故從鄭玄到楊伯峻以來的通行解讀 ,盡管斷句不曾失誤,但解釋上卻違反邏輯,更違反孔子思想體系。
而郭店楚簡《尊德義》篇簡21、22說:“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 (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強也。”簡文的“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與《論語·泰伯》“民可導也,而不可強也 ”語意非常接近。“民可導也”,從“民可使道之 ”出,“不可強也”,從 “不可使知之”衍生。
但《論語》此章的“知”字郭店簡為什么要用“強”來解釋呢? 據清華大學教授廖名春在《從<論語>研究看古文獻學的重要性》分析,他認為要以“知”為本字來說通“強”字是不可能的,當另求別解。因此,他頗疑“知”非本字,當為“折”字之借。原因如下:
《說文·艸部》:“折,斷也。”本義是以斧斷木,引申則有以強力阻止、挫敗、折服、制伏之意 。《漢書·游俠傳》:“權行州域,,力折公侯。”又《蒯通傳》:“折北不救。”顏師古注:“折 ,挫也。”《尚書·呂刑》:“伯夷降典 ,折民惟刑。”陸德明《經典釋文》:“折:馬云:智也。”孔穎達疏 :“折斷下民,惟以典法。”又:“哲人惟刑。”孔安國傳:“言智人惟用刑。”王引之曰:“‘哲當讀為‘折,‘折之言制也。‘哲人惟刑,言制民人者惟刑也。《墨子·尚賢》篇引作‘哲民惟刑。‘折正字也;‘哲,借字也。‘哲人惟刑猶云‘折民惟刑耳。”“折民 ”即“制民”,折就是制,就是用強力制伏、壓迫。
因此,簡文“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強也”當理解為“民可使導之,而不可使折之。民可導也,而不可強也。”即是說老百姓可以讓人引導他們,而不能讓人用暴力去震懾、壓制他們;老百姓可以引導,但不能強迫、威逼他們。“導”是引導,“折”是以強力阻止、挫敗、折服、制伏,其義正好相反。由于“強”與“折”義近,故簡文以 “強”釋“折”。這樣一來,整個句意便合乎情理。
通過上述文獻資料的分析,我們便可知《論語》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當讀為 “迪”,導也。而“知”當讀為“折”,義為阻止、挫敗、折服。孔子的意思是:民眾可以讓人引導,而不能用暴力去使其挫敗。這正是孔子重視民眾力量、關懷民生的表現,怎能輕易將其解讀為孔子的愚民理念?楊伯峻雖然于《譯注》中仔細訓釋了語言文字,卻忽視了孔子整個思想體系發揮的關鍵性作用,以至于片面相信歷來《論語》權威注本的解釋,出現了解讀的盲區。當然,楊伯峻與此類似的疑誤之處在《譯注》中還有體現。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因與文獻學考證脫節所致。雖然其本人身為古文獻學家,但他卻在對《論語》進行考證時過分仰仗自古以來的權威性注本,而未對文獻學與語言學以外的思想層面進行深入挖掘,乃至在嚴謹追究《論語》的語言文字現象時又陷入語言的泥潭。
又《論語·子路》“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一直以來,無論是學界還是《論語》的通行注本,都將這句話簡單理解為孔子提倡絕對的親情觀念,父子間無論誰犯錯,都應依據血親關系予以包庇,以致徇私枉法,導致孔子受到后世嚴重批判,甚至相關學者據此極力貶斥儒學為封建階級的庇護傘。《譯注》中亦如此解釋。但嚴格站在孔子系統的思想體系中分析,我們務必要謹慎考索其中的“隱”字。《荀子·非相》楊倞注:“檃栝,正曲木之木也。”徐鍇《說文解字系傳》云:“檃,即正邪曲之器也。”又云:“檃,古今皆借隱字為之。”又被引申為矯治糾正的意思。《尚書·盤庚》:“嗚呼! 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 尚皆隱哉。”據孔傳的解釋,“言當庶幾相隱括共為善政”,此處“隱”的意義是相互矯正。
據此,我們可以把這句話暫且理解為“父親要在兒子犯錯時予以訓誡,兒子在父親犯法是要適當地予以糾正”,這就還原了孔子情義觀的本質。此外,語言文獻的考證固然是重點,而人們更應該從孔子的“修身治國”的思想中尋求真理。在孔子的學說中,家國是同構的,國是放大了的家。人只有在家孝親敬長,遵循秩序,才能在一國中恪盡職守,事國忠君,成全大義。正所謂《大學》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孔子倡導“天下為公”的社會面貌,而如果在一家中父子互相包庇,藐視禮法;還能于社會中堅持公平正義,實現最終的天道嗎?這當然和孔子的政治使命與價值關懷背道而馳。所以無論是語言訓詁層面,還是思想邏輯層面,“隱”解釋為“矯正 ”更合適。這使得后人能夠重新認識孔子所倡導的家國同構的社會模式,同時使得孔子思想的內在精髓得以重新詮釋。
3 結論
楊伯峻《論語譯注》在學界占據重要地位,其征引文獻數量之龐大、考證之精切、訓釋之嚴密等眾多優勢促進了學界對《論語》以及孔子儒家學說的研究。楊伯峻身為語言文字學家,深刻意識到為經典作注釋時理應將語言文字的考究這一工作置于首位,其參考不同類型的古籍文獻進行校勘訂正,對文字的嚴密訓詁遠超出了眾多《論語》注本,為深入探究孔子思想實質奠定基礎,值得學界進一步探討。而楊伯峻有時因訓詁方式過于單調刻板、文獻之間相互校讎之不足等情況使得《論語》產生很多疑誤之處,間接妨害了人們對孔子整個思想體系的剖析。《論語》作為上古文言文獻具有艱深晦澀的特征,因此人們更應充分重視其語言文字的具體應用現象,并融入孔子的理念中進行綜合考量。
作者簡介
張書僑(1994-),女,滿族,山東,碩士,河北師范大學,研究方向:古典文獻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