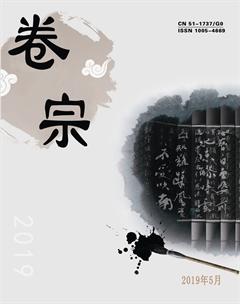《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研究綜述
陸阿玲
摘 要:馬克思在1845年寫的批判費爾巴哈的提綱,提綱由11條思想片段構成,類似于隨筆性質,在他生前沒有發表。在馬克思去世后的1888年,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序言中提到這個文件,并稱之為“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歷史唯物主義的起源”“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并將其第一次發表。對這么重要的萌芽性質的手稿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馬克思主義思想天才的閃光點。本文將從哲學、教育學、文獻翻譯三個角度進行分析探討。
關鍵詞: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研究綜述;馬克思
1 研究現狀
在中國知網的主題搜索框輸入“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可以找到606條結果(截止2019年3月12日),2018-2009最近十年每年新發論文數分別為,32,41,57,41,18,37,45,33,35,33。可以看出,論文的數量并不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呈現穩步上升的趨勢的,2014年對《提綱》研究明顯下降了。而且在知網所有研究費爾巴哈的論文學科分類中,屬于馬克思主義學科的有378篇、哲學學科的有202篇、高等教育學科20篇、教育理論與教育管理學科12篇、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學科8篇、經濟理論及經濟思想史5篇,其他的學科均不足4篇,由此可見,對《提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馬克思主義學科為首的少數幾個社會科學學科中。
2 研究視角
2.1 哲學視角
2.1.1 初窺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
魯克儉在《超越傳統主客二分——對馬克思實踐概念的一種 解 讀》中,以主客二分預設理解馬克思的實踐觀,在馬克思區分了作為實踐生成的與作為類的普遍性的“人的類本質,他就對費爾巴哈的“類”與‘社會畫等號的做法提出了質疑。“但馬克思真正進入唯物史觀視域的關鍵一步,是在紛繁的歷史現象中抓住并領會了動態實踐這一環節。”也就是說人的本質是在實踐中生成的。
鄒詩鵬教在《實踐唯物主義與唯物史觀的相通性》中,對《提綱》中的實踐觀點和傳統的唯物史觀進行區分和闡釋,并且認為只有貫徹了實踐的觀點和實踐唯物主義才可能形成唯物史觀。
可以看出,國內對于《提綱》第一條中的實踐觀的討論還是比較多的。主要集中在對實踐論的闡釋、對比、解讀等各個角度。
2.1.2 馬克思主義“人的本質”的研究
馬克思在《提綱》中寫道:“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句話說明了人的本質。
曾永成在《人的本質:從費爾巴哈到馬克思》中曾指出,費爾巴哈已經開始從社會關系的角度來界定人的本質了,但是,馬克思是從人和自然的實踐關系的角度來理解人的本質的。
石晨在《關于馬克思人的本質理論再認識——以<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為文本》中指出,馬克思從實踐的角度批判了費爾巴哈的人本理論,近年來生態危急的出現是因為人的本質變得異態化,新時代生態文明的構建需要重新認識人的本質理論,并且能夠在時間中實現人與自然的良性互動。
鄧永歡在《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理論——<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人的本質的試解讀》中提出,不能因為提綱中說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就理解成人的本質等同于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應該從現實出發,而萬事萬物又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當然也包括人的本質。“人的本質”的研究中,絕大部分的研究人員是對文本部分的闡釋以及對新時代的我們的啟迪意義。
2.2 教育學視角
《提綱》并沒有直接提到與教育有關的內容,但是其中包含了豐富的涉及教育學的思想,例如實踐與認識,實踐的能動性、人的本質等等。
顏悅南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的教育思想及時代意義》中提到,馬克思的認識論是以往的資本主義教育理論中不可能具有的,實踐是改造主客觀世界的一致基礎。由于馬克思把人看作是現實的、社會的、實踐的,那么,人也就是在諸多社會關系和社會實踐的作用下,形成、發展和完善自己。
吳云和夏康康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中,分別對時實踐觀和人本理論進行文本闡釋,討論它們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啟示。認為我國課堂思想政治課堂單一,應發揮實踐的作用,帶學生走出課堂,在實踐中提升學生的思想道德水平,用提高的思想道德水平再促進實踐的發展,引導學生在更大范圍內發揮其主觀能動性。以人為本的理論要求學校在教書育人的時候要緊緊以學生為中心。
由此可見,對《提綱》中教育思想的研究,基本上是圍繞實踐、認識、實踐的能動性,人本主義展開的,并且談論對我們今天思想政治教育的的啟示意義。
2.3 文獻翻譯視角
《提綱》的最原始版本是馬克思用德文寫下的,傳入我國就不可避免地涉及翻譯問題。
張立波和楊哲在合著《<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在中國的譯介與闡釋》系統地梳理了1929年在中國傳播以來的各種版本,并對各種譯本進行翻譯方法上的歸類,分為附錄化譯介、大綱式解讀、文獻學考證,并且對各種翻譯方法翻譯《提綱》給出了自己的見解。這是一項非常費功夫而且有意義的解讀方式,對筆者這樣不了解文獻的人,提供了更加便捷和直觀地接近文獻原本的方式。
魯克儉在《基于MEGA2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文本研究:一個路線圖》中,對馬克思寫作動機和寫作順序以及原始手稿的改動之處都有探討,也對《提綱》的中文譯本的某些詞句進行了討論,如“客觀性”改譯為“對象性”,“主觀”改譯為“主體”,第一條中“活動”的翻譯問題,第三條和第十條的翻譯問題等等。李毅嘉在《對
<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二條的釋讀和翻譯》中,從德文語法的角度對第一、二、三句進行了邏輯和含義上的梳理研究。
舒遠招在《“nicht”、“die menschliche Wirklichkeit”、“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幾個德文詞的理解和翻譯》中提出要把“nicht”從現行翻譯為“不”或“不是”改譯為“沒有”,對德文詞“die menschliche Wirklichkeit”的理解要從《提綱》的系統性和全面性來把握,把第一條和第六條聯系起來看。他還談到對“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的看法,認為馬克思不是用來泛指歷史上出現過的人類社會,而是馬克思揚棄私有財產的共產主義社會。
3 總結
綜上,國內學者對于馬克思在《提綱》大部分集中在人文社科領域,在哲學視角下,對《提綱》中的馬克思實踐觀和人本思想的研究較多,實踐觀和人本主義很容易與別的哲學思維結合起來研究。《提綱》滲透著教育學思想,實踐論和認識論、人本思想、人的主觀能動性都對教育學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啟迪作用。在文獻翻譯視角下,研究人員都對文本翻譯提出自己的看法。稍顯遺憾的是,在教育學視角下,大部分論文缺乏新意。自1929年《提綱》傳入中國,市面上譯本形形色色良莠不齊,然而關于文本翻譯學術討論較少,這也跟前幾年國內外文水平有關,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外文學科的發展,這一現象會慢慢好轉。
參考文獻
[1]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2]魯克儉,《超越傳統主客二分——對馬克思實踐概念的一種解讀》
[3]鄒詩鵬,《實踐唯物主義與唯物史觀的相通性》
[4]石晨,《關于馬克思人的本質理論再認識——以<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為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