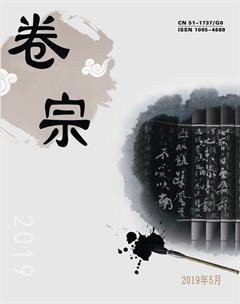“陶然”釋義
1 “陶”的字源
陶,原作“匋”,徒刀切,音桃。據《說文解字》卷十四《部》載,“陶……再成丘也,在濟陰,從匋聲。”濟陰,系濟水之南菏澤古鎮。《夏書》曰:“東至于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徒刀切。”《注》曰:“一成為敦丘。再成為陶丘。禹貢曰道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泆為熒。東出于陶丘北。地理志曰濟陰郡定陶縣。禹貢陶丘在西南。按定陶故城在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西南。古陶丘在焉。”《竹書紀年》記為“堯八十九年作游宮于陶,九十年帝游居于陶”。《廣韻》尸子曰:“夏桀臣昆吾作陶”。《史記·越世家》載“范蠡止于陶”。由以上典籍可清楚知曉,“陶” 自春秋至西漢八百多年間,一直是中原地區的水陸交通中心和全國性經濟都會,享有“天下之中”美譽。堯、舜時期為古陶國,夏商有三翮國。周武王封其六弟振鐸為曹伯,建曹國,定都于陶丘,位于今山東菏澤市定陶區西南。自傳說時代以降,上古先秦多代君王諸侯都曾將此處辟為制造陶器之所。
“陶”之制瓦之意不難從其字源字形中得到印證。“陶”之本“匋”字甲骨文無載。金文字形宛如一人彎身伸手,正在用一把杵制作瓦器的樣子,本義為瓦器。其現存異體字包括“匋 ”,皆可表現人制瓦器之象,系六書中象形獨體造字。(見圖1)后意象進一步豐富,加“阜”(左“阝”),意為從土山取陶土制器。(見圖2)《汲冢周書》載“神農作瓦器”。
圖1 圖2
除陶土制器以外,“陶”又有“喜悅”之意,并逐漸擴大適用范圍。《禮記·檀弓》在訓導君子應控制自己的情緒,即喜哀悲傷等感情特征時說:“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註》、《疏》曰:“鬰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人的喜慍之情,分別有不同的層次,喜有陶、詠、猶、舞等表達程度;而“陶”即指心中初泛喜悅情緒、未及張口表達的細微的心理狀態。“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詩經中《君子陽陽》表現君子的快樂在于喜歡音樂,歌舞會為他們帶來無窮的樂趣,極好的詮釋了“陶”和樂喜悅的意境。
2 若陶之狀的“陶然”
“陶然”作為一個獨立詞匯,最早見于《說文》。漢魏以前,“陶然”一詞共見于《尚書》、《詩經》、《禮記》、《揚子法言》等文獻,其中“陶”皆為其本義,即“陶器”、“陶土”;“陶然”即指若陶之狀。據《大雅·緜》,“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箋,云復者復于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本其在豳時也。”從中不難見“陶”之“省形存聲”的意象。
又,《說文·穴部》記“窯”為“燒瓦窯陶然。是謂經之陶,即窯字之叚借也”,《說文·缶部》記“匋”為“作瓦器也,復穴皆如陶然。作瓦器者,?之燒之,皆是其事,故匋之字次于?。今字作陶,陶行而匋廢矣”。
《毛詩》中也有“陶復陶穴”的記載:“箋云復者復于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毛鄭皆以復為覆。”由此可知,自先秦至后漢漫長的文學歷史間,“陶然”皆以其本意,即“若陶之狀”見于文史記載。
3 古代詩文中的“陶然”
漢魏年間,內憂外患接踵而來。黨派對立,黨錮之禍時常發生,而文人則首當其沖。在這種社會環境下,儒學衰微,許多文士被迫害。面對政治紊亂,同僚被害的局面,魏晉文人多裝聾作啞,寄情聲色,或談玄道佛,或隱居田園,多獨立特行,又頗喜雅集,常聚于林中喝酒縱歌,清靜無為,灑脫倜儻。更有郁郁不得志者,借酒澆愁,不滯于物,不拘禮節。“陶然”作為文人士大夫抒發個人生活體驗和感情、描繪那種酒精刺激神經系統后心中恰到好處的歡愉的情緒,開始在文學作品中具象化,并迅速大量使用。
南北朝薛道衡《秋日游昆明池詩》有語:“琴逢鶴欲舞,酒遇菊花開。羇心與秋興,陶然寄一杯。”漢魏典籍中,集聚意象、風骨、氣韻的“陶然微醺”的文學審美,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趣;各類文藝形式之間相互溝通,形成沿用于后世的美學追求。如十六國時期傳奇隱士公孫鳳,“夏每并食于一器,久之蛆臭,然后乃食,彈琴吟詠,陶然自得,人咸異之”,其人悠然暢意之形象躍然紙上,引人綺思。又如北魏名士、賢臣崔光,勤于政務,勸諫魏帝,朝政清明,“隱愍鴻濟之澤,三樂擊壤之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于堯舜之世。”
由亂世而衍生出的一群特殊的“風流”名士,以飲酒、服藥、清談和縱情山水的生活方式為時尚,無為任誕,清新脫俗。其旨意在南北朝逸士李謐所作《神士賦》中體現的淋漓盡致:“周孔重儒教,莊老貴無為。二途雖如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不愜,死名用何施。可心聊自樂,終不為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長期的社會戰亂離愁,過于輕易的生離死別,妻離子散,使魏晉南北朝名士意識到生命的短暫和可貴,改變了他們的人生哲學觀。張揚個性、醉生夢死、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成了他們的不二之選;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
在這一時期,“詩酒陶然”這一意象在陶潛之文中得到了最佳詮釋。他在其自傳體詩文《五柳先生傳》中寫道:“性嗜酒……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時運其二》記游詩中之語“揮茲一觴,陶然自樂”即表達了暮春乃漱乃濯修褉事時自得其樂的瀟灑心情:“駟牡骙骙,萬馬龍飛。陶然斯猶,阜會京畿。”
繼魏晉之后的另一個“詩酒陶然”繁盛之世,莫過于唐朝。在其文化繁榮的背后,總能看到酒的影子,這便形成了唐朝獨特的酒文化。隨著隋文帝免除酒稅、隋唐兩代打擊門閥士族和打破文化的壟斷、科舉考試寒門的興起,最重要的還是酒的解禁,唐朝終于形成了亦詩亦酒的獨特文化。文學最癲狂者為詩,飲品最癲狂者為酒;而每醉必賦詩,每詩必陶然。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論書畫之興廢》即有“近得荀陳之會,大父請纘為判官,約與主客,皆高謝榮宦,琴尊自樂,終日陶然,士流企望莫及也”之語。
唐代詩酒陶然之文汗牛充棟,僅以盛唐與中唐詩人中最好飲、也最喜用“陶然”的兩位——李白和白居易為例。李白的一千余首詩文中,談到飲酒的共有近二百首,為百分之十六強。中國的詩酒文學到了李白的手中,達到前所未有的高潮。
李白是詩仙,也是酒仙。酒不僅是李白生活的組成,還是其生命的組成。李白本來就集盛唐人俊爽朗健的精神、傲岸不屈的品格、恢宏豪宕的氣度、超凡脫俗的情以及“任俠”的英雄氣質于一身,而在凜冽美酒的作用下,使得這一切在李白身上進一步融合、濃化。酒帶給李白的是一種飛動的氣勢、一種飄逸的靈性、一種往來于天地的絕對自由。“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流露了詩人相攜歡言,置酒共揮,長歌風松,賞心樂事,自然陶醉忘機的感情。
李白還喜以陶然之貌向想象中的上古時代致敬。“百里獨太古,陶然臥羲皇”,想像中的伏羲氏時代的人無憂無慮,生活安閑,和樂自如;“虞人陶然歌詠其德,官則敬,去則思”,以“陶然”一語贊頌了良相治理下民風淳樸,社會安定,像遠古伏羲氏時代一樣的景象;“長嘯一無言,陶然上皇逸”,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則是只有堯舜的太古時代才有的陶然和樂的民風;“物不知化,陶然自春”,萬物所呈現出的昂昂生機并不以得教化為轉移。
據宋人統計,白居易留下“詩二千八百,言飲者九百首。”(方勺《泊宅編》)詩的數量和飲酒詩的數量之多,在古代詩人中首屈一指。現存《白氏長慶集》中以此詞表醉后和樂之狀者有十數處之多。“朝亦獨醉歌,暮亦獨醉睡。未盡一壺酒,已成三獨醉。勿嫌飲太少,且喜歡易致。一杯復兩杯,多不過三四。便得心中適,盡忘身外事。更復強一杯,陶然遺萬累。一飲一石者,徒以多為貴。及其酩酊時,與我亦無異。笑謝多飲者,酒錢徒自費。”這首《效陶潛體詩十六首》直可視為贊頌酒神、膜拜醴泉之檄文了——面對生死無常的人生,借酒極盡生之樂;煎熬于生之孤獨,借酒排遣此種生存的不適;遭受功業難就,借酒淡泊名利;無奈于天命難測,借酒排遣心中憤懣;而諸多情緒心境,都以一句“陶然遺萬累”消弭于墨痕中。
白居易仿陶潛《五柳先生傳》筆法,自號“醉吟先生”,以“醉吟”二字為文眼,抒發“嗜酒耽琴吟詩”的“陶然”之樂:“吟罷自曬,揭甕撥醅,又飲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由是得以夢身世,云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于酒者,故自號為醉吟先生。”“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于石上矣”,“楚醴來尊里,秦聲送耳邊。何時紅燭下,相對一陶然”,“偶遇閏秋重九日東籬獨酌一陶然”,“妻孥不悅甥侄悶,而我醉臥方陶然……死生無可無不可,達哉達哉白樂天。”
在醉鄉中求得“陶然”之趣,超脫于愁苦之外,這是中國古代文人所內化的痛苦的行為表現,也是獨行騷客的自言自語。古代文人堅守著節操,他們痛苦、哀怨、言行怪異,但就是不與世俗同流合污,不降低人格以求容,從這點上來講,“詩酒陶然”所承載的“孤獨感”是雋永而高貴的。
4 陶然亭的“陶然”
陶然亭,中國四大歷史名亭之一,名曰陶然,名聞遐邇,名副其實。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監理黑窯廠,于北京南城慈悲庵以西構筑小亭一座。由于其錦繡旖旎,音清韻幽,因此常有群賢少長絡繹而至,或去國懷鄉,或暢敘幽情,正所謂“周侯藉卉之所,右軍修禊之地”。江藻的“陶然亭”,正得名于白居易的“陶然”。
“少時猶不憂生計,老后誰能惜酒錢。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閑征稚子窮經史,醉聽清吟勝管弦。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作這首《與夢得沽酒閑飲且約后期》時,白居易正被放閑職,屢遭冷遇,可謂閱盡人世滄桑,飽經政治憂患,宦海浮沉半生,思之感慨萬端。“更待菊黃家醖熟,共君一醉一陶然”,這一尾聯把眼前的聚會引向未來,把友情和詩意推向高峰。此番“閑飲”似乎猶未盡興,于是摯友又相約在“菊黃”的重陽佳節時到家再謀會飲,那時家釀的美酒已熟,必然比市售之酒更醇更美,也更能解愁。“共君一醉一陶然”,既表現了摯友間的深情厚誼,又流露出極為深重的哀傷和愁苦。
陶然亭既得名于此詩,白詩中的“陶然”,自然是對陶然亭之名的最好詮釋。有清一代,北京宣南成為詩人士子集會賞樂、詩文相和之地,引領風騷數百年。清順治五年(1648年), 清廷頒布“凡漢官及商民人等盡徙南城”的諭令。宣南一帶遂成為全國游宦士子的聚居區。王士禛、吳梅村、龔鼎孳、孔尚任等詩人都曾寓居于此,結社吟詩。清嘉慶、道光年間,陶澍、顧莼、朱珔、夏修恕、黃安濤等詩人結成宣南詩社”,活躍文壇數十載,先后有近百位文人參與,是京城聞名遐邇的詩人社團。晚清時期的龔自珍、林則徐、黃爵滋、魏源等憂國憂民的愛國詩人皆為宣南詩壇的代表人物。
彼時的陶然亭,摯友相聚,解囊沽酒,豪爽痛飲,有著訴不盡的曠達與閑適。登斯亭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而當去國懷鄉,憂讒畏譏,飽歷憂患,雄志不達,心緒浮沉雨打萍之時,登斯亭也,則有閱歷人世,失意寂寞,滿目蕭然,感極而悲。因此彼時的“陶然”,實為在醉酒當歌的放誕喜悅中,深藏的那種閑而不適、醉而不能忘憂的復雜情感。
今日的陶然亭,已成為共和國建國后北京市政府最早興建的現代園林公園——陶然亭公園中的靈魂建筑。陶然亭公園地處首都核心區,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促進發揮首都核心職能和帶動區域均衡發展的重要陣地,是南城生態系統的核心組成部分,也是周邊市民的活動空間。昔日的燕京名勝、“都門勝地”,僧侶正法善根之土,騷客吟哦放歌之地,如今已成為糅合了秀麗的園林風光,豐富的文化內涵,光輝的革命史跡的旅游觀光勝地。公園內林木蔥蘢,花草繁茂,樓閣參差,亭臺掩映;中央島上錦秋墩、燕頭山,與陶然亭成鼎足之勢,望湖觀山,景色大觀。更有總角孩童、蒼顏白發,或蹣跚學步,或舞劍走拳,或勁歌熱舞,或肴蔌宴酣,共同譜寫出一副豐富多彩、盎然蓬勃的北京城南市民的文化生活風貌。自上世紀末起,大雪山、游樂場、游船、電影院和大舞池就成為北京民眾流連忘返的娛樂場所。如今公園定期舉辦的冰雪嘉年華、春花文化節、地書比賽等文化活動更是聲名遠播,深受群眾喜愛。今天的陶然亭,實是思想解放、民主自由時代,老百姓“陶然歌舞”的好去處了。
從悲喜雜糅、醉酒放達,到喜笑顏開、歡樂心醉,陶然亭的“陶然”經歷了數百年風雨,承載了千萬人俯仰一世的悲喜情緒,最終定格于和諧社會中男女老少的張張笑靨。人們不論悲喜窮達,都可在陶然古亭中,留下胸中感慨憂愁,帶走滿心陶然自足,“陶然”的內涵在新時代再次得到了詮釋。
參考文獻
[1]白居易:《白氏長慶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12年版。
[2]常璩:《華陽國志》,中華書局1985年版。
[3]陳初生:《金文常用字典》,陜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4]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6]李白:《李太白集》,岳麓書社1989年版。
[7]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0年版。
[8]王文錦:《禮記譯解》,中華書局2013年版。
[9]魏收:《魏書》,中華書局2000年版。
[10]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2013年版。
[11]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中華書局2003年版。
[12]張懷通:《逸周書新研》,中華書局2013年版。
[13]周振甫:《詩經譯注》,中華書局2002年版。
[14]周祖謨:《廣韻校本》,中華書局2011年版。
作者簡介
田婧(1986-),女,漢族,北京市人,博士,北京市陶然亭公園管理處,研究方向:全球史、博物館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