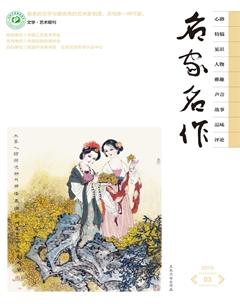且臨此處品墨香
賈遼源



山西師范大學正門十字路口東南一個不起眼的角樓,進側門,樓梯被書法作品和一群孩子的笑臉環繞著。盤旋而上,曲徑通幽,開朗處便是花木“禪房”。兩扇老門板拼接的桌面,四根枯木支撐的桌腿;磨盤,瓦當,葫蘆,馬燈,花盆古意,綠蘿蒼翠;迎面一副金字墨聯:“紫竹林中觀自在,蓮花座上現如來”,好一派隱士風度!一窗之隔,都市嘈雜,凡塵萬千,倏然遁跡,不由你就會端茶品茗,回歸自然。
“雙驥堂”在此,楊馮虎的世界便由此展開。
不管馮虎是否認可,對眾多讀者來說,2014年,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中國書畫百杰作品集·楊馮虎》的出版應當是對他書法求索的階段性總結,預示著他思想觀念、寫作技法、作品風格的轉變和提升。在此之前,他的書法多有樸澀,甚而凝拙。樸澀,就是質樸得純粹,把自己的心肺掏出來示人;凝拙,就是率真,有生澀感。他全力堅守這種風格,以至于幾乎獨一無二。石濤曾言:書畫非小道,詩人形似耳,出筆混沌開,入拙聰明死。馮虎的聰明就在于極善揣摩古人。過去,他似乎更多地偏愛隸書,漢魏碑帖的高古雄強賦予他奇峻灑脫、如臨淵崖的藝術風格。“翻書香染指,舞墨韻傳神”,你能感受到北方凜冽雪封的大地,山巒靜默,萬蹤隱跡,崔巍聳天的巖壁間,干枝弄舞,旁逸斜出,傲雪剛勁卻又情趣頑皮。他追求線條的波動,刻意展示殘破的剝落感,借此給每一個漢字注入這個民族千年的不安和跌宕,仿佛破廟里的一根蠟燭,搖搖晃晃,將息將倒,卻又頑強堅韌,光耀人間。品讀他的行書,似乎每一幅作品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就像一個好演員,一上臺就是那個人物,一招一式,形神兼備。馮虎行書隱藏著摩崖的質感,仿佛一個歷史老人把酒臨風,喋喋不休地述說繁縟的家史。張弛疏密在用墨的燥潤間自然展現,氣脈呼應在運筆的疾緩里穿插濡染。
馮虎書法風格的形成同諸多書家一樣,天賦和勤奮是其關鍵。年少時極喜繪畫,畫偉人像,摹連環畫,細致觀察,準確下筆,無不生于天然。十八九歲入伍繪制幻燈片,描摹部隊好人好事,讓他很快走上繪畫道路。轉入書法源于一次意想不到的慚愧。當地舉辦的一個書畫展上,一位頗有名氣的大家對他的畫作極是喜愛,但話鋒一轉,說對題款的書法實在不敢恭維,畫留下,讓他回去要好好寫字。馮虎臉發燒,心羞愧,從此作畫不敢貿然題款,總是先想好幾個字,遍尋名人大家字帖一遍遍臨摹,直到有了把握,才敢戰戰兢兢落款。如此這般,臨字的時間總是遠遠多于繪畫,干脆就用書法參展,不成想,偶然得到一個優秀獎,就此燃起心中火焰,鉆研書法,綿延至今。
雖說起步較晚,但楊馮虎農村孩子清苦的出身給了他勤奮的習性。臨池宜長,讀帖宜博。他遍覽名家書帖,根據自己的喜好潛心臨摹,沉溺于斯,樂此不疲。20世紀80年代末,他參加臨汾地方書展拔得頭籌,布展現場幸識書法大家樊習一,嗣后拜師入門,步入殿堂,寒門孝子,喜逢貴人。老師說,踏踏實實臨帖,少創作,不會吃虧。時至今日,年逾八十的老師罹患眼疾,依然堅持收藏刊登書法作品的報紙雜志,每日臨摹不輟,并把感悟用小楷寫在旁邊,儼然一幅幅精美作品。這對馮虎的藝術追求有著極大的引導激勵作用。中國書法界素有碑帖之爭,民國初期康有為作《廣藝舟雙楫》提出“魏碑無不美者”,從理論上將碑派書法推上了足以抗衡甚或以絕對優勢壓倒帖學的地位。楊馮虎顯然偏向碑學,但他也不放過名帖。他堅持靠近古人,擁抱石刻卻又兼收并蓄,以碑入帖,以帖融碑,過了漢隸關,再從民間尋找趣味。《張遷碑》《石門頌》,八大山人、顏真卿,乃至鐘鼎簡牘,一一涉獵,均有取法。他臨帖,不僅形似,更求神交,悉心體味古人心境,揣摩碑帖雄強氣韻。他臨摹顏真卿《爭座位帖》,以6米巨幅呈現,以假亂真,神似真跡。山西省書協舉辦首屆臨帖大展,他報送《祭侄文稿》。因為沒有合適的紙張,隨手抽用了兩張毛邊紙,竟然獲得大獎。孫過庭說,“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臨帖要像,但在這個千百年顛撲不破的道理面前,無疑更需要無數的理念和偏方。100%的書法愛好者無不常年臨帖,可往往90%的人自學一輩子都難以入門,同樣的努力,結果迥異,何以如此?馮虎一語道破:臨帖不得法也!
為書之道,關乎性情,通乎造化。楊馮虎雖是彪形大漢,但心思縝密。飯桌上豪氣沖天,坐下來靜如處子,綿善溫婉。他非常善于體察或者說喜歡古人書寫時傾注的那份情愫,尤其鐘情于類似顏真卿哭侄的悲憤無奈,更能深深體味朱耷的哭笑人生和悲涼情懷。他書寫的時候常常體悟到一種感覺:心到了,筆下就有不同的處理,結構,線與線的轉折,寫著寫著也就運用自如,形成風格了。近年來,他的書法呈現變化態勢,比如,隸書尋求金文的簡約,描摹古人的動態;行書愈加酣暢,蒼勁靈動。過去蒼茫跌宕,大起大落,取法刁鉆,結字左右起伏,宛如飛天抖肩,長袖待舒,似乎要顯示他人生追求的急迫與不甘。可現在,倏然釋懷,一切都看得開,放得下,沉穩靜穆,悠然豁達。“萬丈紅塵三杯酒,千秋大業一壺茶”;“谷米調得清和味,慈云飛舞妙天香”。他這個年齡,已經擁有豐富的人生閱歷,盡覽滄桑,閱遍悲涼,自然書如其人,人如其字,蓋氣質使然。
今天的馮虎更喜歡獨自靜坐,清茶一杯,幽蘭吐香。廟堂梵音,古箏悠揚,半部論語,家訓盈胸,忽然一個音符,一個字詞,說不定就會觸動他的創作欲望。用什么樣的形式表現出這些不經意的感觸,如何才能讓作品打動自己,打動別人,這是他要琢磨的一個重要問題。在章法上,他追求一種傳統經典與現代品位互融互通的美學要求,畢竟作品是呈獻給今天的讀者,更多作品的欣賞者恐怕并非書家或專業人士,因此他的每一幅作品都要在格局上呈現一種裝飾之美。膜拜傳統和迎合當代并不矛盾,他既遵循書法之道,從線與墨的表達中凸顯書法之美,又要在古雅里翻卷出時代的浪花。一篇作品,或行或楷,或隸或草,都要精心布排;用墨濃淡焦潤,定有對比。這種對章法獨具匠心的追求在某種程度上又展示了他個人超乎書外的幾多才情。話說回來,在當下,這也是作品最后呈現的必要形式。內容與形式的貼合是作品呈現的關鍵。袁枚在《隨園詩話》里提出“忘足,履之適,忘韻,詩之適”。書法藝術同理,只有把技法、筆墨等工具性、套路性、形式性的東西適度地、恰如其分地應用到自己想要表達的內容中,自然就會產生最好的表達,獲得最佳的效果,創造出完美的審美形象。
書法藝術對楊馮虎來說既是成就人生、修身養性的法寶又是安身立命之所在。近幾年,他一直致力于書法藝術的普及教育,可謂教學相長,桃李天下。他始終強調取法古人,胸懷石刻。示范教學,總讓學生細心觀察筆鋒細微的動態、抖動、轉承、頓挫以及運筆的力量所在;品評作業,他堅持求真務實,絕不刻意奉承。跟他學過書法的孩子們屢屢獲獎,老同志棄俗守正。馮虎的真實堅守、倔強追求一如他的書法:剛強有韌,不失氣節!
楊馮虎喜歡駿馬昂揚向上、奔騰灑脫的精神氣質,他的名字里也有一個“馬”字,由是,宅號“雙驥堂”。且臨此處,墨香,禪意,古韻,文氣,深沉如秋,渾然兼有。
楊馮虎簡介:
楊馮虎,中國書法家協會注冊高級書法教師,中國書法藝術研究院特聘書畫家,中國教育電視臺水墨丹青書畫院書法家,中國硬筆書法協會會員,山西省書法家協會會員,山西省青年書法家協會會員, ?臨汾市書法家協會副秘書長,臨汾市堯都區書法家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臨汾市老年大學書法教師。
書法作品獲“華夏之獎”中國書畫藝術交流大展賽銅獎;“金九福”杯全國書畫電視大賽三等獎;世界書畫名家作品交流展銅獎。作品入展中國文聯中國近現代書畫展,山西省第六屆、第七屆書法篆刻展等重要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