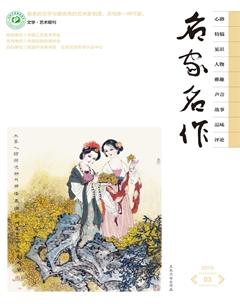逃之夭夭,灼灼其華
[摘 ? ? ? 要]從《七月與安生》中自由與安生、漂泊與回家、生存與死亡、文藝與現實四組二元對立關系談起,結合影片的具體情節對“追與逃”的二元對立產生的動因以及藝術美感進行分析,探討追與逃對人生的意義。
[關 ?鍵 ?詞]《七月與安生》;逃避;追求;自由;二元對立
《七月與安生》主要講述了一位渴望自由與一位追求安穩的姐妹花,在共同愛上一個男人之后命運發生改變的故事。三個人不斷追求、逃遁,最終生命的軌跡與心之所向相背離,卻抵達了各自靈魂的歸宿。影片最難能可貴的是打破每個人物之間臉譜化的性格標簽,塑造了一種能折射到每個人靈魂深處的多面鏡像,人物在追與逃之間找到各自生命的答案。
影片以“追”與“逃”為敘述的內在邏輯,并且在片中二者互為對立,最終達到精神的統一,即追求是為了逃避,逃避亦是一種追求。
一、追與逃的二元對立分析
(一)自由與平穩
影片名叫《七月與安生》,從名字的設定上就可以看出編劇對自由與平穩這兩個對立面畫下了濃重的筆墨。
電影前半段都在講述一對姐妹按照各自的人生愿景,努力追求的故事。從十三歲開始,安生就在用叛逆、反抗、流浪追求著自由,而七月則選擇安安生生地考試、升學,用好名次換來父母、老師、鄰居的喜愛。安生在上了職業技校之后就跟隨流浪歌手四海為家,七月則和高中就在一起的男朋友規劃著大學的生活。
但圓夢卻被逃離的夢魘纏繞,李安生對自由的追求,并非個體意義上的出走,而是為了讓她和七月的友誼鏈條能更加穩固的逃離;七月對安穩的追求,不僅是因為“被安生帶走了闖世界的激情”,更是為了逃避過去和安生一起的安穩,邁向不確定的愛情。追求自由,開始就是為了逃避自由;追求安生,開始就是為了不再安生。
電影后半段,人物內心深處的掙扎終于暴露出來,仿佛被彈簧拉扯住了身體,追求得越用力,反彈力就越疼痛。
安生不再追求自由,讓蘇家明與七月回歸安穩;七月卻不愿再用安穩的童話綁架一段不幸的婚姻,還給自己自由。兩個人都學會了正視自己標榜的追求與真實的逃離之間的鏡像,走上與設想南轅北轍卻是真正的人生道路。
(二)漂泊與回家
安生從小生活的家庭里,父親早逝,母親不歸,她總是對母親嚷嚷著“我不要讓你回家”,想要逃離這個冰冷的家庭,卻對七月母親些微的關懷就付出多倍的回報,甚至是偷耳環來討她歡心,選擇漂泊也是為了成全七月的安穩,在母親去世后,讓自己將來還有家可歸。七月的家小而溫馨,鎮上每個人都和她相熟,但幸福的家卻同時也是桎梏,和睦的家庭把她束縛在既定的軌道上,每每想向遠方張望,就被家庭的線拉扯回來,成為一個乖巧的木偶。
最終安生撫養著七月的孩子,盡心做一個好母親,溫暖她內心深處無比渴求的家庭;七月從按部就班的追求中逃離出來,難產而亡抑或四海為家,都是她再也不愿回家的內心寫照。漂泊的人會回家,有家的人已遠行。
(三)生存和死亡
安生總說一輩子太長了,她只想活到二十七歲。七月規劃著自己的人生,二十六歲結婚,二十七歲生孩子。但是最具戲劇性的是,七月在二十七歲生下一個孩子后,卻永遠活在了二十七歲。
七月的死亡不僅是對現實被動地偶然逃離,是對她過往沉湎于虛幻的愛情、放棄追求生命本真自由、寄希望于平靜的小鎮生活的懲罰。更是她一步步主動追求的必然選擇,是她勇敢放手、邁出小鎮、走向自由的解脫。盡管生命因難產而消逝,但她渴望自由、掙脫束縛的愿望終于在“七月”的筆下得以實現。同時在27歲誕下的小生命,更是一種生命的回歸,讓七月與安生向死而生的愿望得以寄托。
(四)文藝與現實
黑格爾曾說“審美帶有令人解放的性質”。 李安生在簽下死亡通知書的一刻,曾痛哭流涕地說:“我才不簽字呢。”但鏡頭切換到電腦屏幕時,她卻在鍵盤上敲出一行字:“二十七歲,在路上。”文學世界寄托了她和七月對解放自我的追求,也能讓她逃避現實的苦難、重拾生活信念。
不僅僅是李安生在文學作品中找到了最后的精神家園,每一個觀眾也在《七月與安生》這部電影作品構造的文藝世界中,找到自己心目中七月的歸宿,乃至自己的歸宿——
一個七月被安生用文字勾勒出來,她最終解脫束縛,遨游世界成為“本我”,一個七月被安生埋藏在現實下面,難以扭轉多年軌跡的方向,難產而亡成為“自我”,一個七月被安生在向蘇家明講述時出現,她平安地生下孩子,將孩子交給安生照顧,自己重獲新生成為“超我”。
三重設定模糊了現實與文藝的邊界,讓每一個觀眾都跟隨虛構的劇情,逃離開現實的自己,追求內心深處的答案。
二、追與逃的動因分析
追與逃這樣一種每個人青春期乃至一生中都會遭遇的一種精神狀態是如何在《七月與安生》中產生、激烈碰撞最后釀出悲劇的呢?筆者認為有以下兩點原因:
(一)精神生態
魯樞元曾指出:“精神生態學是以人的內在情感生活為研究對象,是一門作為精神性存在的主題與其生存環境(包括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之間相互關系的學科。一方面關涉到精神主體的健康成長,另一方面還關涉到一個生態系統在精神變量協調下的平衡、穩定和演進。”
電影《七月與安生》兩個互為影子的個體就處在不同的精神生態中,也處于不同的生態危機中,造就了追與逃之間的沖突與融合。安生面對著變化萬千的自然環境、人情淡薄的家庭環境、叛逆突破的文化環境,培養出了渴望溫暖、重視真情的精神形態,她不斷在環境中逃離,卻愈加追到了真實的自己,最終達到了精神的和諧。七月身處千篇一律的自然環境、溫暖幸福的家庭環境、束手束腳的文化環境,但最終孕育了一個大膽反抗、渴望自由的內心,最終沒有尋到兩者的平衡,命運危機爆發。
同時促使兩人在自我和精神環境之間發生對立沖突的直接誘因,在于現實生活環境遭到巨變,即蘇家明的出現。人格模式在轉瞬間解體,被壓抑的一極突然釋放出來,安生犧牲自己成全七月的告別瞬間,讓人領會到她善良求全的人格;七月躲藏在乖乖女面具下自私的真面目讓人感受到她表里不一的矛盾。正是精神生態的巨變賦予了二人強烈的戲劇張力。
(二)內在歸因
1.李安生——生命的無屬
片中的遠方與家鄉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對立矛盾。它們預示著唯有不斷追求與逃離才有可能找到生命可依存的終點。對自由的狂妄追求與糾結逃離實際上反映了現代人對生命無屬的困惑以及尋找出路、歸屬的焦灼和渴望。影片最后以李安生為七月選擇了走向燈塔作結,將自由作為可選的幻想對象的功能弱化,成為導演認為的歸屬。
2.林七月——個人的偏見
影片中促使七月在追與逃之間游移的推手莫過于家庭、社會的偏見,現代社會雖然人煙輻輳,鬧熱熙攘,但小地方的生活法則卻決定了人最終還是生活在一片情感的荒原,唯一有情感共鳴的安生,也因為自己的偏見而遠走他鄉。母親一味的“相夫教子”的規勸讓她戴上了乖乖女的面具,她的內心卻充滿掙扎;社會對好學生的偏愛,讓她一輩子不敢突破安穩過日子的藩籬,最終的爆發卻換來了生命的終結。
(3)蘇家明——抉擇的盲目
而讓蘇家明不斷追求和逃離的動因則更多是對抉擇的盲目。他一邊牽起七月的手,一邊又將隨身的玉佩送給安生,甚至在關系破裂的前夕都沒有任何主見,安生的放手、七月的割愛在他看來不過是擺脫選擇的痛苦的途徑。他行動的盲目也注定了他不可能主宰自己的命運,在追與逃之間搖擺。
三、追與逃的美感分析
1.對立和諧美
美在于和諧,而和諧起于差異的對立。《七月與安生》無論是人物塑造、場景設置或是情節沖突都呈現出二元對立。但對立的二元項的邊界卻又常常因追逃而模糊。追與逃的過程為對立的聚與散、遠與近、愛與恨找到了走向統一的途徑,七月與安生都在不斷地逃離環境追回自我的過程中,構建了和諧之美。
2.悲劇超越美
《七月與安生》的藝術美感引人遐思,其悲劇性尤為令人感懷。它不僅強烈地表現了個人精神與現實世界的矛盾爭斗,還展示了渺小的個體和崇高的心靈所帶來的張力美。
而片中七月的死亡抗爭更具有悲劇的超越性,她對生活枷鎖的不斷退讓躲避,換不來生命的真正安穩,在結尾她終于敢于擺脫安穩的假象,卻還是因懷了蘇家明的孩子而使理想破滅,最終難產而亡。正是這長久的躲避和最后的自由追求體現了她的生命激情與悲劇精神,呈現出非自覺超越的悲劇審美形態。
逃之夭夭,亦是一種拼命追逐;灼灼其華,亦是一種生命永恒。愿每個人都能如七月般最終在追與逃之后尋得靈魂的歸宿,更愿每個人都如安生在追與逃之后讓生命閃耀著灼熱的光輝。
參考文獻:
[1]E.云格爾.死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
[2]黑格爾.美學(第一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3]魯樞元.生態文藝學[M].西安: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作者簡介:張藝璇,女,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本科生在讀,主要研究方向:藝術學理論。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