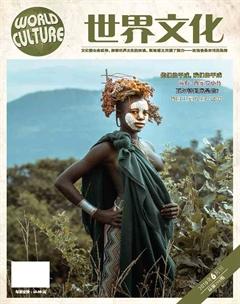活于當(dāng)下,向死而生
劉淼文
2019年度索爾仁尼琴獎頒獎典禮于4月18日在莫斯科“俄羅斯僑民之家”舉行,俄羅斯當(dāng)代著名作家、文藝學(xué)家、語文學(xué)博士葉甫蓋尼·克爾曼諾維奇·沃達拉茲金(Евгений Германович Водолазкин)因在小說《拉夫爾》(《Лавр》)中將“俄羅斯固有的深厚的精神與心理小說傳統(tǒng)同崇高的語文學(xué)文化結(jié)合起來”,加之其“天才的藝術(shù)書寫風(fēng)格”而獲此殊榮。
沃達拉茲金長居彼得堡,此次專程抵達莫斯科領(lǐng)取索爾仁尼琴獎。他對彼得堡一家媒體說:“索爾仁尼琴獎對我而言非常珍貴。實際上,索爾仁尼琴(1918—2008,俄羅斯作家、諾貝爾文學(xué)獎獲得者)也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我在青年時代就癡迷于他的作品,他對各類事情的看法也深刻地影響了我的世界觀。所以無論從什么角度看,獲得此獎都是我的榮幸。”
索爾仁尼琴獎是俄羅斯境內(nèi)比較有影響力的文學(xué)獎項,自1998年開始頒發(fā),但早在1978年索爾仁尼琴就有了設(shè)立此獎項的構(gòu)想。根據(jù)作家的意愿,該獎需“不錯過名副其實的佳作,也不獎勵平淡空洞之文”。沃達拉茲金此次獲獎并非偶然。2013年他攜剛出版的小說《拉夫爾》一舉摘得當(dāng)年的“大書獎”第一名——新晉作家獲此殊榮極為罕見;同時還獲得了當(dāng)年的“亞斯納亞波良納”獎,進入了“俄羅斯布克獎”短名單。該作品很快被翻譯成十幾種外語,被英國《衛(wèi)報》評為關(guān)于上帝的最好的10部小說之一。
當(dāng)代俄羅斯作家有個特點:他們受教育程度都不低,且大多具有語文學(xué)教育背景,像高爾基這種未受過系統(tǒng)教育,靠自學(xué)成才的作家越來越少。一些專業(yè)從事文藝批評的批評家也投身小說創(chuàng)作,他們參與到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來就好比新浪潮電影批評家親自操刀拍電影——這種現(xiàn)象正應(yīng)了俄羅斯文學(xué)批評家兼小說家什克洛夫斯基的那句話:每一個正派的文藝學(xué)家都應(yīng)該會寫小說。
沃達拉茲金就是這么一個正派的文藝學(xué)家。1964年,他出生在有著“羅斯城市之母”之稱的基輔城。1986年從基輔國立大學(xué)畢業(yè)后,沃達拉茲金考入俄羅斯科學(xué)院下屬的俄羅斯文學(xué)院——普希金之家,師從俄羅斯文化巨擘利哈喬夫院士,攻讀古俄羅斯文學(xué)副博士學(xué)位;留校任教期間,他又獲得語文學(xué)博士學(xué)位,并且出版專著數(shù)部,發(fā)表文章上百篇。學(xué)術(shù)研究之余,沃達拉茲金也從事文藝創(chuàng)作,但真正在文壇嶄露頭角是憑借小說《索洛維約夫與拉里奧諾夫》(《Соловьев иЛарионов》)。2009年作家憑借這部作品摘得安德烈·別雷獎。獲得“大書獎”后,他還有系列短篇小說和兩部長篇小說《飛行員》(《Авиатор》)、《布里斯班》(《Брисбен》)面世。2018年出版的小說《布里斯班》講述了一個世界知名的音樂家患有帕金森癥的故事,帶有強烈的存在主義氣息。主人公格列普·雅諾夫斯基,一個技藝高超的吉他手在自己事業(yè)巔峰之際,卻因病失去了登臺演出的機會。于是他開始探索人存在的意義,尋找新的人生支點。該書已入圍2019年“大書獎”長名單。沃達拉茲金目前是《俄羅斯文學(xué)》(《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雜志編委、《文本與傳統(tǒng)》 (《Текст и традиция》)雜志主編,以及總統(tǒng)文化藝術(shù)委員會成員。
沃達拉茲金的語文學(xué)研究經(jīng)歷和精湛的古羅斯文學(xué)修養(yǎng)充分體現(xiàn)在了《拉夫爾》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小說情節(jié)并不復(fù)雜:主人公阿爾謝尼是個孤兒,父母均死于霍亂。他住在墓地邊上的一所房子里,由祖父赫里斯托夫爾撫養(yǎng)長大,祖父教授他民間醫(yī)學(xué)和藝術(shù)。阿爾謝尼不僅成為一位醫(yī)術(shù)精湛的草藥師,而且具有先知一般的預(yù)言能力。小說描寫的是他通過自我救贖,最后成為圣徒的故事。主人公生活的每個新階段(草藥師,朝圣者,僧侶,圣徒)都是他在平靜生活和以信仰與愛的名義建功立業(yè)之間做出抉擇的結(jié)果,并且每個階段都伴隨著主人公名字和空間環(huán)境的變化。主人公多次更換自己的名字,每一次變換都是一種重生,也是一種救贖。他與少女烏斯京娜秘密相愛,烏斯京娜最后因難產(chǎn)而死成為阿爾謝尼一生沉重的罪孽。在烏斯京娜死后,他自己化名烏斯京,以愛人的名義走遍各個村落,四處行醫(yī),成為圣愚;瘟疫過后他擁有了圣徒的名譽,兩鬢斑白的他來到普斯科夫城,進入白湖基里爾修道院,獲名阿姆夫羅西;之后在修道院接受了最高的苦行戒律,這天是8月18日,正是圣徒拉夫爾以圣父圣子圣靈名義出家的日子,阿姆夫羅西便獲得了拉夫爾這一名字。他一生都愛著死去的烏斯京娜和他們共同的孩子。小說最后,他為懷孕的安娜斯塔西婭接生,孩子呱呱墜地,拉夫爾完成救贖,在黎明前安靜地離世。“安娜斯塔西婭”在俄語中便是救贖之意,拉夫爾的逝世,也伴隨著孩子的新生,孩子是拉夫爾生命的延續(xù)。1520年的8月18日,救人無數(shù)的拉夫爾的遺體被從修道院禪修室抬起,穿過森林。全羅斯的信眾都趕來參加他的安魂祈禱,數(shù)十萬人里里外外擠滿教堂,盛況空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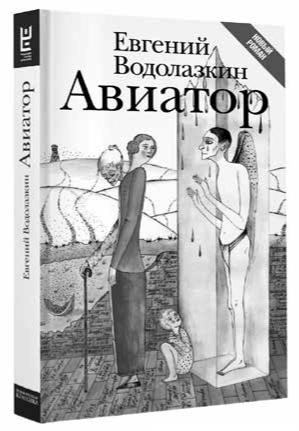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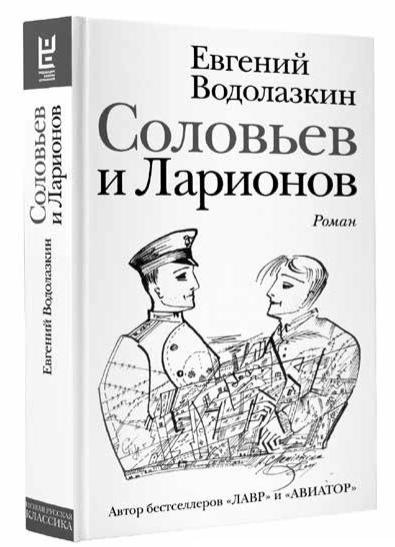
主人公四次更換的名字頗有內(nèi)涵:阿爾謝尼是他受洗之時所取的名字,寓意勇敢,而歷史上兩位叫阿爾謝尼的圣徒事跡也不斷在主人公的生命中出現(xiàn)。第二個名字烏斯京取自逝去的愛人名字,寓意正義,可以說是對他人生中圣愚階段的本質(zhì)界定。第三個名字阿姆夫羅西意為上帝的、永恒的,點明了主人公精神的發(fā)展走向。最后一個名字拉夫爾,也是這部小說的名字,象征永恒的生命以及主人公對烏斯京娜靈魂的救贖。主人公的爺爺赫里斯托夫爾是一個相當(dāng)重要的角色,“赫里斯托夫爾”這個名字即為信仰上帝之意。正是他早早看出了阿爾謝尼非凡的特質(zhì),向其傳授知識和對待生活的態(tài)度,使阿爾謝尼得以成為一代圣徒。
小說《拉夫爾》的敘述語言由現(xiàn)代俄語和古俄語雜糅改良而成,故事背景也被放置在15世紀(jì)。小說的敘述者具有雙重性,一方面是古羅斯式的,另一方面是現(xiàn)代的;這種雙重性不僅體現(xiàn)在語言上,而且體現(xiàn)在思維意識中。當(dāng)然,古詞今用、風(fēng)格雜糅的語言在俄羅斯文學(xué)中并不算奇特,好的作家都是語言大師,岡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普拉東諾夫和索羅金都有高超的運用化用古詞的技巧。
2013年《拉夫爾》甫一獲得“大書獎”,立刻引起學(xué)者和批評家們的爭議,爭議點之一就是這部作品的體裁。很明顯,作品使用了歷史材料以塑造一個古羅斯世界,并在其中嵌入虛構(gòu)情節(jié);其濃郁的歷史感不僅表現(xiàn)在語言、故事背景和體裁上,而且關(guān)于日常細節(jié)的描述也都包含這種特性,小說中的不少名人名言取自古羅斯著名文集《蜂蜜》中的篇目,還有不少來自《關(guān)于印度王國的傳說》等古羅斯文獻。但作家卻直接在書的封面上標(biāo)明“非歷史小說”字樣。實際上,這部小說的確不是單純的歷史小說,它有明顯的古俄羅斯圣徒行傳的體裁特征,小說主要講述的就是圣徒拉夫爾的一生。沃達拉茲金借用的古羅斯文學(xué)傳統(tǒng)并不只是圣徒傳一種,還有編年史的體裁。作家本人是古羅斯文學(xué)專業(yè)出身,編年史是他最熟悉的文本之一,小說的風(fēng)格正是化用了編年史文獻的特征。沃達拉茲金之所以強調(diào)這本書是“非歷史小說”,是因為歷史小說這個體裁在作家看來不太嚴(yán)肅,屬于當(dāng)代流行的類型文學(xué)之一種,與偵探小說、愛情小說和玄幻小說如出一轍。而沃達拉茲金對《拉夫爾》頗為珍視,認為自己并不是在描述歷史,而是在刻畫心靈的故事。作家還在小說中使用了一些小技巧,以消除小說的歷史感,混淆時代。比如小說中描寫的大齋戒周末食譜是黑魚子配蔥或者紅魚子配辣椒。眾所周知,辣椒原產(chǎn)自美洲,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之后才將辣椒、西紅柿、玉米等作物帶到歐洲;辣椒在世界范圍內(nèi)種植并廣泛食用已是16世紀(jì)末的事情了。小說中的故事主線講述到1520年,那時候的俄羅斯不可能有辣椒。小說中甚至還出現(xiàn)了工業(yè)時代的塑料瓶子。沃達拉茲金本人說,小說中出現(xiàn)塑料瓶子不值得驚訝,主人公一會兒講教堂斯拉夫語,一會兒講現(xiàn)代口語比這更奇怪。混淆的語言,錯亂的時間,作家正是以這種刻意的“知識性錯誤”來提醒讀者小說的虛構(gòu)性、非歷史小說性。

沃達拉茲金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就是死亡,用作家自己的話說,他創(chuàng)作的繆斯就是死亡。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死亡也是《拉夫爾》這部小說的重要主題。死亡主題開篇就被凸顯出來:主人公住在靠近墓地的房子里,他父母死于瘟疫;此外,主人公的職業(yè)是一名草藥師,又在瘟疫肆虐的村莊行醫(yī),所見無外乎死亡。小說以死亡開篇,以拉夫爾的逝世結(jié)束,開頭與結(jié)尾都在盧基村的基里爾修道院。生命開始于此,也終結(jié)于此,歸于愛與信仰,走向永恒。
沃達拉茲金認為愛情與生命是天賜之禮,它存在就可能失去。當(dāng)你愛的時候,會害怕離別;當(dāng)你活著的時候,會害怕死亡,此乃人之常情。這種恐懼不僅對人無害,反而是最有活力的情感。這種情感迫使人們更好地去評價自身擁有的東西,去過好這一生。實際上,作家所謂的死亡,關(guān)乎的仍是人生意義這一永恒母題。在一次采訪中他談道:“法國記者問誰是我的繆斯,我回答說是死亡,把他們都嚇壞了。在西方,他們一點兒都不喜歡談?wù)撍劳觥5俏抑溃枰f出一切你認為需要說的東西。死亡教會我們責(zé)任,并讓我們安排好生活。這就好比你在課堂上寫一篇文章,最初你想寫個草稿,當(dāng)你看看時鐘,發(fā)現(xiàn)沒有足夠的時間,你會馬上直接開寫。從某種意義而言,人不應(yīng)該為未來而活,而是要活在當(dāng)下;不是向前,而是向上。要做到這一點,你必須更清楚地認識自己,并且永遠不要絕望。事實上,我所有的小說講述的都是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