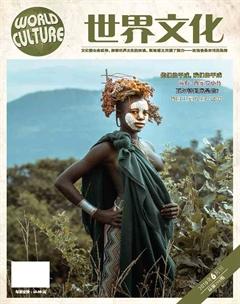愈老愈“瘋狂”
高山

他是中國(guó)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譯家。
他在史上留下了多項(xiàng)“第一”和“之最”:第一位到達(dá)印度的中國(guó)僧人;第一位連續(xù)走完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國(guó)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年過(guò)花甲還到外國(guó)取經(jīng)的高僧;第一位對(duì)取經(jīng)經(jīng)過(guò)之地都留下記載的高僧;還是西行取經(jīng)走得最遠(yuǎn)、到的地方最多的高僧。
法顯(334—420)是中國(guó)歷史上西行求法的第一人。東晉隆安三年(399年),已是65歲高齡的法顯自長(zhǎng)安出發(fā),西渡流沙,越蔥嶺至天竺,游三十余國(guó),歷盡艱險(xiǎn),收集了大批梵文佛典,前后歷時(shí)13年。先是由陸上絲綢之路抵達(dá)印度,后由海上絲綢之路乘船回國(guó),在山東青島嶗山登陸,于義熙九年(413年)抵首都建康(今南京)。
法顯本姓龔,他有三個(gè)哥哥,都在童年夭亡,他的父母擔(dān)心他也夭折,在其3歲時(shí)便把他度為沙彌(即送他到佛寺當(dāng)了小和尚)。到了東晉隆安三年,法顯已在佛教界度過(guò)了62個(gè)春秋,60多年的閱歷,使他深切地感到,佛經(jīng)的翻譯趕不上佛教大發(fā)展的需要,特別是由于戒律經(jīng)典缺乏,使廣大佛教徒無(wú)法可循,以致上層僧侶窮奢極欲,無(wú)惡不作。為了維護(hù)佛教“真理”,矯正時(shí)弊,年近古稀的法顯毅然決定西赴天竺,尋求戒律。
這年春天,法顯同慧景、道整、慧應(yīng)、慧嵬四人一起,從長(zhǎng)安起身,向西進(jìn)發(fā),開(kāi)始了漫長(zhǎng)而艱苦卓絕的旅行。次年,他們到了張掖,遇到了智嚴(yán)、慧簡(jiǎn)、僧紹、寶云、僧景等五人,組成了十人的“巡禮團(tuán)”,后來(lái)又增加了一個(gè)慧達(dá),總共十一人。晉元興三年( 404年),他們來(lái)到了佛教的發(fā)祥地——拘薩羅國(guó)舍衛(wèi)城的祇園精舍。傳說(shuō)釋迦牟尼生前在這里居住和說(shuō)法時(shí)間最長(zhǎng),這里的僧人對(duì)法顯不遠(yuǎn)萬(wàn)里來(lái)此求法深表欽佩。《佛國(guó)記》載:“彼眾僧嘆曰:奇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上相承,未見(jiàn)漢道人來(lái)到此地也。”這一年,法顯還參訪了釋迦牟尼的誕生地——迦維羅衛(wèi)城。

晉義熙元年( 405年),法顯走到了佛教極其興盛的達(dá)摩竭提國(guó)巴連弗邑。他在這里學(xué)習(xí)梵書(shū)梵語(yǔ),抄寫(xiě)經(jīng)律,收集了《摩訶僧祇律》《薩婆多部鈔律》《雜阿毗曇心》《方等般泥洹經(jīng)》《綖經(jīng)》《摩訶僧祇阿毗曇》等六部佛教經(jīng)典,一共住了3年。道整在巴連弗邑十分仰慕人家有沙門(mén)法則和眾僧威儀,追嘆故鄉(xiāng)僧律殘缺,發(fā)誓留住這里不回國(guó)了。而法顯一心想著將戒律傳回祖國(guó),便一個(gè)人繼續(xù)旅行。他周游了南天竺和東天竺,又在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國(guó)(印度泰姆魯克)寫(xiě)經(jīng)畫(huà)(佛)像,住了兩年。
東晉義熙五年( 409年)年底,法顯離開(kāi)多摩梨,搭乘商船,縱渡孟加拉灣,到達(dá)了獅子國(guó)(今斯里蘭卡)。他在獅子國(guó)住在王城的無(wú)畏山精舍,求得了《彌沙塞律》《長(zhǎng)阿含》《雜阿含》以及《雜藏》等四部經(jīng)典。至此,法顯身入異城已經(jīng)12年了。他經(jīng)常思念遙遠(yuǎn)的祖國(guó),又想著一開(kāi)始的“巡禮團(tuán)”,或留或亡,今日孤身一人,形影相吊,心里無(wú)限悲傷。有一次,他在無(wú)畏山精舍看到商人以一把中國(guó)的白絹團(tuán)扇供佛,觸物傷情,不覺(jué)潸然淚下。
東晉義熙七年( 411年)8月,法顯完成了取經(jīng)求法的任務(wù),坐上商人的大船,沿海上絲綢之路東歸。行船途中,幾次遇到暴風(fēng),險(xiǎn)些船沉大海。經(jīng)過(guò)將近一年的海上旅行,最后在青州(今山東青島)登陸。青州長(zhǎng)廣郡太守李嶷聽(tīng)到法顯從海外取經(jīng)歸來(lái)的消息,立即親自趕到海邊迎接。時(shí)為東晉義熙八年( 412年)7月14日,法顯已是78歲高齡了。
法顯在山東半島登陸后,旋即經(jīng)彭城、京口,到了建康。他在建康道場(chǎng)寺住了5年后,又來(lái)到荊州(湖北江陵)辛寺,元熙二年( 420年),圓寂于此,卒年86歲。
法顯在臨終前的7年多時(shí)間里,一直緊張艱苦地進(jìn)行著翻譯經(jīng)典的工作,共譯出了經(jīng)典6部63卷,計(jì)萬(wàn)余言。他翻譯的《摩訶僧祗律》也叫大眾律,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對(duì)后來(lái)的中國(guó)佛教界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在抓緊翻譯經(jīng)綸的同時(shí),法顯還將自己十三載西行取經(jīng)的見(jiàn)聞,融合佛學(xué)智慧,寫(xiě)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國(guó)記》。
《佛國(guó)記》別名《法顯行傳》《法顯傳》《歷游天竺紀(jì)傳》《佛游天竺記》等,全文9500余字,是一部傳記文學(xué)的杰作,也是一部重要的歷史文獻(xiàn),對(duì)行經(jīng)諸國(guó)的山川形勢(shì)、佛教名勝和宗教活動(dòng)等都有真實(shí)記載,是研究當(dāng)時(shí)西域和印度歷史的極為重要的史料。法顯去印度時(shí),正是印度史上的黃金時(shí)代——笈多王朝(320—480)有名的超日王在位的時(shí)代,關(guān)于笈多王朝古史缺乏系統(tǒng)的文獻(xiàn)記載,超日王時(shí)的歷史,只有依靠《佛國(guó)記》來(lái)補(bǔ)充。中國(guó)西域地區(qū)的鄯善、于闐、龜茲等古國(guó)湮滅已久,傳記無(wú)存,《佛國(guó)記》中所記載的這些地區(qū)的情形,可以彌補(bǔ)史書(shū)的不足。《佛國(guó)記》還詳盡記述了印度的佛教古跡和僧侶生活,因而后來(lái)被佛教徒們作為佛學(xué)典籍著錄引用。此外《,佛國(guó)記》也是中國(guó)南海交通史上的巨著。中國(guó)與印度、波斯等國(guó)的海上貿(mào)易,早在東漢時(shí)期已經(jīng)開(kāi)始,而史書(shū)上卻沒(méi)有關(guān)于海風(fēng)和航船的具體記述。《佛國(guó)記》對(duì)信風(fēng)和航船的詳細(xì)描述和系統(tǒng)記載,成為中國(guó)最早的記錄。

中國(guó)去往西域和印度取經(jīng)者眾多,但只有法顯一人以年過(guò)花甲的高齡,完成了穿行亞洲大陸又經(jīng)南洋海路歸國(guó)的遠(yuǎn)途陸海旅行的驚人壯舉。其他的取經(jīng)者都是二三十歲身強(qiáng)體壯的年輕人,如唐初玄奘大師去印度取經(jīng)時(shí),年不過(guò)25歲,回國(guó)時(shí)也才41歲。
法顯留下的杰作《佛國(guó)記》,不僅在佛教界受到稱譽(yù),而且也得到中外學(xué)者的高度評(píng)價(jià)。唐代名僧義凈說(shuō):“自古神州之地,輕生殉法之賓,(法)顯法師則他辟荒途,(玄)奘法師乃中開(kāi)正路。”近代學(xué)者梁?jiǎn)⒊f(shuō):“法顯橫雪山而入天竺,赍佛典多種以歸,著《佛國(guó)記》,我國(guó)人之至印度者,此為第一。”斯里蘭卡史學(xué)家尼古拉斯·沙勒說(shuō):“人們知道訪問(wèn)過(guò)印度尼西亞的中國(guó)人的第一個(gè)名字是法顯。”他還把《佛國(guó)記》中關(guān)于耶婆提的描述稱為“中國(guó)關(guān)于印度尼西亞第一次比較詳細(xì)的記載”。日本學(xué)者足立喜六把《佛國(guó)記》譽(yù)為西域探險(xiǎn)家及印度佛跡調(diào)查者的指南。印度學(xué)者恩·克·辛哈等人也稱贊說(shuō):“中國(guó)的旅行家,如法顯和玄奘,給我們留下有關(guān)印度的寶貴記載。”眾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研究印度古代歷史,必須依賴于外國(guó)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國(guó)古代典籍最為重要;而在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游記更為突出。僧人游記數(shù)量極多,而繁簡(jiǎn)不同,時(shí)代先后不同,《法顯傳》可謂最古老、最全面者之一。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學(xué)者(包括印度學(xué)者在內(nèi)),都視之為瑰寶。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學(xué)家曾寫(xiě)信說(shuō):“如果沒(méi)有法顯、玄奘和馬歡的著作,重建印度歷史是不可能的。”
1600年來(lái),法顯始終沒(méi)有被人們所遺忘。法顯所創(chuàng)作的《佛國(guó)記》,更是代代相傳,被翻譯為英、法、日、印度文等多國(guó)版本,成為世界宗教史、東方文化史上的千秋瑰寶,為中外文化交流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