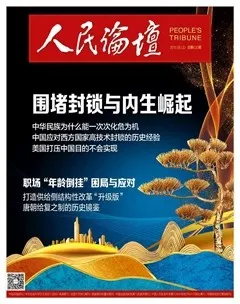“三治”融合實現鄉村善治
【摘要】在新的發展環境下,鄉村社會各種矛盾凸顯,如何在鄉村社會中更好地發揮自治、法治、德治的作用,成為亟待破解的問題。“三治”的有機融合是實現鄉村治理的關鍵環節,也是完善鄉村治理體系建設,發揮新時代鄉村治理體系協同效應的重要抓手。
【關鍵詞】鄉村治理 協同治理 “三治” 【中圖分類號】D267.2 【文獻標識碼】A
新時代鄉村治理體系的戰略定位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以下簡稱“三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是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是黨中央在深刻認識“三農”發展新階段、新規律、新任務基礎上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同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具有高度的耦合性。長期以來,我國鄉村治理沿用傳統治理手段和模式,未能及時提升運用新時代治理手段的能力,導致在復雜的鄉村社會中,“三治”逐漸喪失其有效性。治理手段實施的無效和治理要素組合的不力,迫切要求對鄉村治理體系進行有效性理論提升和融合性實踐探索。“三治”如何有效發揮作用,從而進一步實現有機融合,關系到新時代鄉村治理體系的目標實現和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實施。
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出,要增強鄉村治理能力。這充分表明黨中央對鄉村治理的重視,對新時代鄉村治理效果的要求和期待。新時代鄉村治理體系的構建,是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目標上與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高度一致。在新的歷史方位下,鄉村內外部環境新的變化賦予鄉村治理新的內涵和要求,伴隨著鄉村社會各種矛盾的不斷凸顯,如何在鄉村社會中更好地發揮自治、法治、德治的作用,成為亟待破解的問題。新時代鄉村治理體系中“三治”有效性的探討成為解決諸多基層社會矛盾的關鍵,鄉村治理體系的有效性就是用最低的綜合成本達到最佳的基層社會治理效果——鄉村善治。而“三治”有效性是鄉村治理體系的根本和前提,是解決紛繁復雜鄉村治理問題的重要手段,鄉村治理體系的有效性理應是以“三治”為主要治理手段的有機組合。
自治、法治、德治在新時代鄉村治理體系中的重要作用
鄉村自治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和豐富的實踐沃土,存在并作用于鄉村社會延續至今。中國傳統社會基于“家戶”元素的原因,自治主要是解決以個人或家戶為單元的“自我”事務,因此是一種自發、自主、自愿的原發行為。傳統社會自治的有效性雖然不足,但卻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鄉村社會生產力的發展。1987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以下簡稱《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提出村民自治,村民自治成為法律支持的一種集體行為,其有效性的內容和范圍都有擴大。新時代我國鄉村社會復雜性的本質屬性沒有發生改變,但鄉村社會內外部環境卻發生了巨大變化,鄉村自治的績效要求和有效性的標準也在不斷提高。因此,為保證新時代鄉村治理體系中自治的有效性,首先要加強基層黨組織的領導能力,加強黨組織帶領各類治理主體處理公共事務的能力,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其次要提高村民主動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管理的積極性,村民有效參與是提高自治有效性的基礎,也是基層民主的具體表現形式;此外要推動村級組織及鄉村各種性質組織的健康發展。村級組織是村莊公共事務管理的主要力量,其自身建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各種性質組織的建立發展則是鄉村自治主體的補充和完善。
法治在鄉村社會的發展最為明顯的就是在近代社會,而法治觀念形成和法治體系的成熟則是在現代社會。法治是道德規范的底線,是一種強制約束,在“三治”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中,法治是自治基礎上的進一步規范,在鄉村治理體系中發揮了保障作用。當前村民法治觀念依舊不強、村干部法治思維也較為滯后,黑惡勢力干擾村委會換屆選舉、惡意上訪等鄉村社會中違法現象頻發,嚴重影響到基層社會的穩定,給國家安全穩定帶來很大隱患。法治有效性的發揮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首先,必須加強基層黨組織成員法治思維的培育,加強基層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合法領導地位;其次,充分保障村民自治權的實現和實施,保證村民對村莊公共事務的管理權、知情權、監督權和決策權,使村民充分行使《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國家其他法律所規定的全部權利;再次,在鄉村社會積極營造學法、懂法、用法的法治環境,使法治思維成為鄉村社會中村民的行為習慣。
德治在傳統社會以儒家學派倡導為主,隨著歷史的發展早已融入統治者的治國之道。德治是建立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并使之成為國家的治國之道。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十分重視德治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在黨內和全社會中積極培育共產主義道德,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德治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所發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鄉村社會德治的發揮面臨挑戰。黨中央從頂層設計提出構建“三治合一”的鄉村治理體系,德治作為重要的手段之一,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基層社會的培育,基層黨組織要發揮好領導示范作用;必須加強新時代村規民約的構建,使其成為鄉村社會的一種習慣和風尚;必須發揮“新鄉賢”的典范作用,使其成為鄉村社會的一種“潤滑劑”和“調節器”;必須結合鄉村社會復雜性的實際,在尊重文化差異的基礎上因地制宜培育和發揮德治作用;積極展開“好媳婦”“好丈夫”“好婆婆”“五星家庭”等評選活動,為德治踐行拓寬渠道。
增強鄉村治理能力需要“三治”融合發展
新時代鄉村治理體系要達到治理有效的目的,必須將“三治”進行有機融合,“三治”有機融合是達到鄉村治理有效的關鍵環節和手段。唯有如此,才能實現鄉村治理理論邏輯上的完善,并發揮出新時代鄉村治理體系的協同效應。
首先,打造治理平臺的融合。“三治”融合首先必須通過一定的載體即平臺進行融合,尤其是以村級組織為代表的各相關組織,以及為其提供溝通融合的相關制度。村民委員會、村民代表、村務監督組織、理事會、鄉賢會、村莊經濟合作社等組織的建設和完善是“三治”融合的重要平臺,是其融合的“硬件”構成部分。鄉村各種制度如兩委聯席會議制度、村民代表制度、村務監督和管理制度、公共衛生管理條例制度、村干部離任審查制度等的建立和完善則為“三治合一”的鄉村治理提供了“軟”平臺,同時又為其融合進行了約束和規范。
其次,推進協同治理的融合。“三治合一”鄉村治理體系不是三者各行其道的平行治理,而是三者有機結合的協同治理。“三治合一”的新時代鄉村治理體系也不是機械呆板、固定不變的僵化模式,而是一種動態互補、靈活包容的治理理念。自治是法治和德治的基礎,在自治過程中必須將法治思維和優秀傳統文化貫穿其中;法治在鄉村社會為自治提供保障并為德治提供底線思維;德治貫穿于自治和法治的全過程,為其提供潤滑劑作用,也是新時代鄉村社會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途徑。
最后,謀求空間的融合。“三治合一”的鄉村治理體系一定是時間和空間上的高度融合,時間上的融合主要表現為過程的融合,空間上的融合則主要是鄉村社會治理內部空間及內外部空間的融合。其中,內部空間的融合要求將村治精英、制度、村民、鄉村等治理要素統一于由“三治”構建的立體式、多主體參與的鄉村治理體系中,充分考慮各治理要素的特征,科學安排并合理定位各自在治理體系空間中的作用和功能。同時,“三治合一”的鄉村治理體系還必須是開放的體系,體現為鄉村社會同國家社會空間上的統一,“三治合一”的鄉村治理體系在空間上是同國家治理體系相融合的,新時代鄉村治理體系可以借助和接納鄉村社會空間以外的社會力量來發展和完善自我。
(作者為山西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山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治理現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區鄉土社會與現代國家關系研究”(項目編號:17FZZ003)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徐朝衛、董江愛,《資源型村莊治理中集體經濟的多重效應》,《貴州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