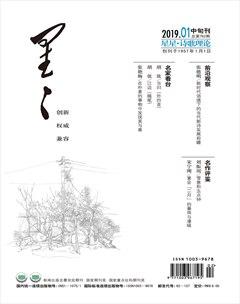重會“二月”的暴雨與凄暗
宋寧剛
二 月
【蘇俄】鮑利斯?帕斯捷爾納克
二月。蘸好墨水就得哭!
當噗嚕噗嚕響的泥水
泛著黑色春光的時候,
寫二月就免不了流淚。
花幾角錢雇一輛馬車,
聽著禱前鐘聲和車輪叫聲,
到田野上去,田野上的暴雨
比墨水和淚水更猛。
無數的禿嘴烏鴉
像曬焦的梨似的從樹上落下,
落在一個個水洼兒里,
織成一幅凄涼、憂傷的圖畫。
化凍的地方又黑又陰暗,
風的吼叫聲又大又凄慘,
詩越是寫得出人意外,
越能如實地表現悲愴的境界。
(力岡、吳笛 譯)
閱讀譯詩是有風險的,談論譯詩更是如此。帕斯捷爾納克(1890-1960)的這首《二月》,一度在中國流傳很廣,甚至比《日瓦戈醫生》中的那些詩篇還要有名。其中,最著名的中譯版本之一,就是力岡和吳笛的譯詩。而力岡,也是《日瓦戈醫生》的譯者之一。
幾年前翻閱《帕斯捷爾納克詩全集》(顧蘊璞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中譯本,驚訝地發現,《二月》被置于三卷本詩集的卷首。詩末標明的寫作時間是“1912年”。不過,1912年并非詩人寫作的開端。《詩全集》收入的帕斯捷爾納克詩作,還有寫于1909年的。那么,從1909年至1911年寫的詩,為什么沒有被置于《詩全集》的篇首?一個解釋是,詩人認為此前所寫還不夠成熟。就此來說,《二月》可以被看作是帕斯捷爾納克早期詩作中他自己比較滿意的一首。
在《二月》的諸多譯本中,力岡、吳笛譯本是很不錯的一種。這個譯本清楚明白,具體平實。一首外國詩,在中國流傳廣泛并產生影響,首要的因素是,能讓說另一種語言的人讀懂。在那個閉塞和貧乏的年代,《二月》帶來的是新鮮、沖擊,陌生的經驗。
第一節的四行,“二月。蘸好墨水就得哭!/當噗嚕噗嚕響的泥水/泛著黑色春光的時候,/寫二月就免不了流淚。”意思就很清楚,會叫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契訶夫筆下滿是泥水的大街或道路。只不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生活的那個年代,俄羅斯還沒有出現像20世紀上半葉那樣的巨變,所以,雖然涅克拉索夫發出過“在俄羅斯,誰能過上好日子”的憤懣和感慨,卻不會像后來的俄國詩人在20世紀所感受到的那種,整個祖國都在經歷受難般的創痛。“蘸好墨水就得哭”,表達的就是這樣一種創痛感。
心情如此悲愴、痛苦,怎么辦?去戶外。“花幾角錢雇一輛馬車,/聽著禱前鐘聲和車輪叫聲,/到田野上去”。然而,到了田野也不見得好——“田野上的暴雨/比墨水和淚水更猛。”悲愴的心情不但沒有得到排解,相反遭遇到暴雨,仿佛暴雨也在為難他,或者為苦難的俄羅斯難過。好吧,那就盡情地釋放,讓淚水在暴雨的掩護下盡情傾灑。無論“蘸好墨水就得哭”,還是“暴雨/比墨水和淚水更猛”,經歷過苦難的中國讀者,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讀到這些詩句時都會有深深的共鳴吧。
第三節,寫整首詩都沒有明確提到、但從頭至尾都是潛在的主體所看到的田野上的景象:“無數的禿嘴烏鴉/像曬焦的梨似的從樹上落下,/落在一個個水洼兒里,/織成一幅凄涼、憂傷的圖畫。”“禿嘴烏鴉”改為“禿嘴鴉”似乎更好一些。一是詞語的節奏,二是相比“烏鴉”在中文表述中的特指性,“鴉”的涵蓋性更大。詩人寫禿嘴鴉“像曬焦的梨”,比喻極為生動、貼切,既寫出禿嘴鴉的外在形象,也用“曬焦的梨”暗示了詩人內心的焦苦(有內在的焦苦,才想得到“曬焦的梨”)。禿嘴鴉從樹上落下來,落在水洼里,“織成一幅凄涼、憂傷的圖畫”。“織”字也用得好,將禿嘴鴉從樹上落下以及落在水洼里這些點狀的事實聯結成一個網狀的結構——“一幅凄涼、憂傷的圖畫”。
第四節,從“圖景”的最后落點,也即“水洼”寫起。水洼既由雨水而來,也由二月里部分的解凍而來。“化凍的地方又黑又陰暗,/風的吼叫聲又大又凄慘”。化凍處的暗黑,風聲的凄厲,都應和了詩中主體此時的心緒(也可以說詩中主體的心緒使得他更多地注意到化凍處的暗黑和風的凄厲)。現在看來,像“又黑又陰暗”“又大又凄慘”這樣刻意追求排比和齊整的句式,都有時代的痕跡。如此情景與詩有何關系?詩人告訴我們,面對此情此景,“詩越是寫得出人意外,/越能如實地表現悲愴的境界”。如果孤立地看最后兩行,就有點“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意味。但實際上不是。因為它有一個我們從詩中讀出來的前提:面對此情此景,“詩越是寫得出人意外/越能……”。
《二月》是從室內寫起的,“蘸好墨水就得哭”,詩人終于情難自禁,走向戶外,結果發現雨水比墨水和淚水更加猛烈。于是,在悲切和高度釋放的心緒中看到禿嘴鴉、水洼組成的凄惻的圖景,化凍處的(土地和)水洼的暗黑,以及風的凄厲,詩人感到,只有超出常情、出人意表的奇崛詩句,才能如實地表現所看到和感受到的這種悲愴情境。全詩雖然寫得悲情,但其敘述和內在邏輯是清晰明暢的。
現在來看,《二月》更像一首具有預言性質的詩。22歲的帕斯捷爾納克在以后的生活中“蘸好墨水就得哭”的時候會更多、更強烈。比如十月革命后的一系列社會變革、斯大林時期的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詩中與帕斯捷爾納克相遇、并深受震動的中國詩人王家新,曾在20世紀90年代初寫過一首《帕斯捷爾納克》,向詩人致敬。詩中說:“從一次次劫難里你找到我/檢驗我,使我的生命驟然疼痛/從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轟然泥濘的/公共汽車上讀你的詩,我在心中/呼喊那些高貴的名字/那些放逐、犧牲、見證……”無論雪,還是泥濘,都暗自呼應著《二月》中所寫的情形。這是詩人間的精神吸引和傳遞,也是帕斯捷爾納克對中國當代詩歌影響的一個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