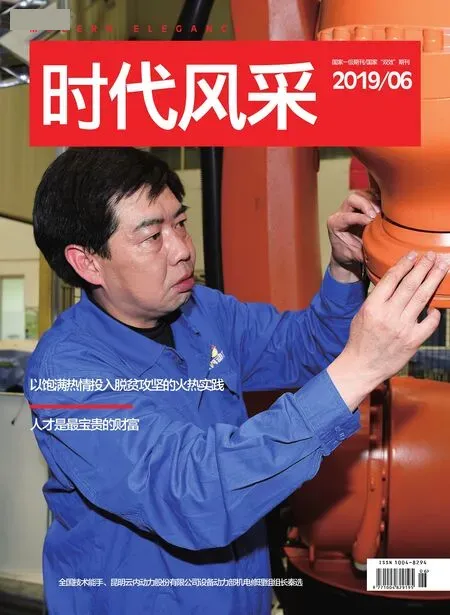起底“套路貸”的花招與暗網(wǎng)
文 姜偉超 張智敏 胡偉杰
“低利息、無需抵押、快速放款”的廣告,在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上隨處可見,受害者不假太多思索邁出了“借款”那一步,從此自己的人生便被一連串套路“套”住。日益猖獗的“套路貸”有著令人防不勝防的花招與暗網(wǎng)。
騙到一萬元,覬覦一百萬
去年3月,李麗麗不小心弄壞了別人的手機(jī),得掏錢賠給人家。李麗麗下載了一個叫做“米貸金融”的App,此平臺宣稱無需抵押,“秒放款”,正合李麗麗心意。但李麗麗要付出的代價是,將手機(jī)通訊錄向網(wǎng)貸平臺開放。
當(dāng)李麗麗填完個人信息并提交后,很快有業(yè)務(wù)人員與她聯(lián)系,在簽了一份手機(jī)租賃合同和其他一大堆看不懂的合同后,李麗麗成功貸到3000元,但到手只有2100元,其余900元是利息,已經(jīng)事先扣除——這就是此種放款方式必有的“砍頭息”。李麗麗需在一周內(nèi)還掉3000元本金,逾期要繳納逾期費(fèi),每天300元,也就是本金的10%。
李麗麗逾期了。一發(fā)不可收拾的悲劇由此開場。接下來一年里,李麗麗通訊錄上的常用聯(lián)系人全“瘋”了。她的家人、親戚朋友都因?yàn)槭懿涣蓑}擾,多次更換電話號碼。但催收公司的陰云始終籠罩在他們頭頂,每當(dāng)他們新?lián)Q了號碼,催收的電話馬上就會打來,繼續(xù)騷擾。
一年時間里,李麗麗的父母為她償還了59萬元的利息及罰金,但居然還欠著米貸金融20多萬元。感覺李麗麗榨不出什么油水了,這個團(tuán)伙便將其劃歸為“無效客戶”,但這不意味著放過了她。李麗麗的信息被轉(zhuǎn)賣給另一家類似平臺,催命一般的電話繼續(xù)撕扯著李麗麗的世界。到警方介入時,李麗麗父母已經(jīng)為她的一時沖動付出了70多萬元。
“從被‘套路’直到報案,她幾乎遭遇了所有的軟暴力催收手段。”偵辦此案的某公安局刑警支隊(duì)警官張怡說,“套路貸”不是在受害人身上騙一筆就收手,而是不計(jì)后果地榨干受害人。“你兜里有一萬,騙子騙完拉倒,是普通詐騙;你兜里有一萬,騙子想騙走一百萬甚至幾百萬,就是‘套路貸’。”
織就蜘蛛網(wǎng),只待可憐蟲
讓人不寒而栗的是,“套路”不但縛住許多受害人的生活,還縛住了他們的頭腦。不止一位還不起借款和利息的受害人轉(zhuǎn)而“賣身還貸”“為虎作倀”,成為加害者的一員。
李麗麗被騙案件涉案的一家網(wǎng)貸平臺中,有位被抓獲的犯罪嫌疑人王坤。先前,家境貧寒、父母離異的他,由母親做家政供到了大學(xué)。為減輕母親壓力,2018年王坤從網(wǎng)貸平臺借款3000元用于交學(xué)費(fèi),并計(jì)劃通過勤工助學(xué)還清貸款。沒成想,這3000元轉(zhuǎn)眼滾成了9萬元,遠(yuǎn)遠(yuǎn)超出王坤償還能力。
無奈之下,王坤的母親想方設(shè)法幫兒子還債,但只能還上5萬多元。為將剩下的“欠款”一筆勾銷,在貸款平臺業(yè)務(wù)員的游說下,王坤辦理休學(xué),加入該“套路貸”公司“打工”還貸,由此走上了犯罪道路。
隨著警方掌握的“套路貸”團(tuán)伙情況日益充分,大家發(fā)現(xiàn),此類團(tuán)伙的“人事制度”不但善于把原本的放債對象轉(zhuǎn)化為“業(yè)務(wù)骨干”,團(tuán)伙內(nèi)部分工協(xié)作的“蜘蛛網(wǎng)”也相當(dāng)發(fā)達(dá)。
他們?yōu)榱颂颖芄矙C(jī)關(guān)打擊,會把業(yè)務(wù)外包給多個催收公司,如果公安機(jī)關(guān)查到某家催收公司的違法事實(shí),他們便馬上斷絕與該公司所有聯(lián)系,物理“隔斷”,給公安機(jī)關(guān)偵查制造了相當(dāng)大的障礙。業(yè)務(wù)觸角最發(fā)達(dá)的公司,外包網(wǎng)絡(luò)由24家公司組成,可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套路”的“技術(shù)含量”
隨著警方偵查的深入,“套路貸”危害性更隱蔽的一面向世人揭開面具:如今,眾多“套路貸”團(tuán)伙不僅以“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偽裝自己,更讓大數(shù)據(jù)等智能化技術(shù)成為為虎作倀的手段。
袁程程是一家咖啡連鎖店的工作人員,生活原本平淡而安靜。去年9月的一天,她用手機(jī)下載了一款做菜的App,把自己喜歡的幾個菜式收藏下來,打算下班后學(xué)一下。沒想到,回到家后這款A(yù)pp卻“變”了,做菜的內(nèi)容全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滿屏“網(wǎng)貸”App鏈接。
袁程程有點(diǎn)莫名其妙,隨即關(guān)閉了App,但映入眼簾的“秒放款”“無抵押”“輕松還貸”等字樣,一直在她心里揮之不去。幾天之后,袁程程又打開了它,點(diǎn)下了申請貸款的按鍵。
袁程程只借了4500元,但在以后的3個月時間里,被迫在十幾個“網(wǎng)貸”平臺轉(zhuǎn)單平賬,先后還款6萬多元,債務(wù)卻越欠越多。一天之中,袁程程會接到幾十個甚至上百個催款電話,“每天一睜眼,就想著怎么能籌點(diǎn)錢還上,好把今天熬過去”。
就在袁程程輾轉(zhuǎn)各個“套路貸”平臺轉(zhuǎn)單平賬的同時,警方的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部門盯上了這個App。警方發(fā)現(xiàn),這個App兼具兩面,一面是功能尋常的App,一面則是“套路貸”犯罪團(tuán)伙開發(fā)的網(wǎng)貸平臺,警方把它命名為“AB面”App。
隨著偵查范圍擴(kuò)大,警方發(fā)現(xiàn),手機(jī)應(yīng)用平臺上,這種App還不少。“套路貸”團(tuán)伙開發(fā)了大量的“AB面”App,在平臺上招徠用戶的A面提供做菜、旅游、天氣、閱讀一類功能,B面則暗藏“套路貸”貸款平臺入口。什么時候讓用戶看A面,什么時候切換到B面,都由后臺控制。一個App往往連接著幾十個“套路貸”平臺。
“套路”的“智能程度”
“在追蹤‘套路貸’的時候,深刻感受到‘知識就是金錢’。”警方一名民警開玩笑地說。
參與“套路貸”的不法分子有的有大型網(wǎng)絡(luò)公司工作經(jīng)歷,從業(yè)經(jīng)驗(yàn)豐富,有的做過網(wǎng)絡(luò)公司的個性推廣,有的是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專業(yè)人士出身,還有的諳熟現(xiàn)代企業(yè)管理……讓他們走到一起的,除了對暴利的渴求,還有各自在從業(yè)中發(fā)現(xiàn)的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行業(yè)的風(fēng)險與漏洞。
現(xiàn)在的“套路貸”平臺越來越“正規(guī)”,這些公司不乏入駐高檔寫字樓者,有的甚至披上了“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的華麗外衣,更不必說內(nèi)部組織架構(gòu)已經(jīng)相當(dāng)嚴(yán)密,分工井然,平臺維護(hù)部、業(yè)務(wù)部、財務(wù)部、法務(wù)部等一應(yīng)俱全,還引入了前、后端風(fēng)險防控機(jī)制。公司風(fēng)頭之盛,到了吸引不知情的當(dāng)?shù)馗咝G皝碓O(shè)立學(xué)生實(shí)習(xí)基地的地步。
據(jù)介紹,以前“套路貸”是撒網(wǎng)式騙人,在各個網(wǎng)上平臺無差別散布“低息無抵押快速貸款”信息,等待借款人主動聯(lián)系。現(xiàn)在他們大量開發(fā)網(wǎng)絡(luò)應(yīng)用,并且用上了大數(shù)據(jù)分析技術(shù),一旦用戶下載“上鉤”,便把獲取到的用戶信息運(yùn)用大數(shù)據(jù)模型加以分析,區(qū)分其“可騙價值”,以便精準(zhǔn)“套路”。
在破獲的某特大“套路貸”專案中,涉案的“套路貸”公司利用“AB面”App和其他手段非法獲取了482萬人的個人信息,給什么人看A面,給什么人看B面,都是根據(jù)受害人信息“精確計(jì)算”得出的。比如,同一個“AB面”App,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個地區(qū)人下載后只能看到A面,因?yàn)檫@些地區(qū)的人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行騙得手不易;對公檢法工作人員及其家屬也顯示A面,因?yàn)檫@些人有相關(guān)的違法行為辨別能力,“惹不起”……
“借款要先通過公司風(fēng)控系統(tǒng)審查,我們會讀取借款者的通話記錄和通訊錄,如果發(fā)現(xiàn)里面有催收公司的電話,就不借了。”犯罪嫌疑人王某某說,他們還引入人臉識別系統(tǒng),來驗(yàn)證借款人提供的身份證信息是否真實(shí)。
“套路貸”公司拿到借款人的隱私信息后,會根據(jù)手機(jī)通話記錄列出與借款人關(guān)系親密者排名。這些數(shù)據(jù)都會上傳后臺,催收公司獲授權(quán)后可登錄查看,以此決定打借款人哪個聯(lián)系人的電話,或者采取哪種方式催收。
不管什么貸,監(jiān)管責(zé)無旁貸
房貸、車貸……如今,各種消費(fèi)貸款已成為人們生活中耳熟能詳?shù)拿~,帶動了年輕一代為主體的社會人群形成更開放的金錢觀,超前消費(fèi)需求日益上升。在正規(guī)貸款機(jī)構(gòu)門檻過“高”的情況下,這一群體就為不法網(wǎng)絡(luò)貸款機(jī)構(gòu)的生存提供了土壤。
問題還有更值得反思的一面,多方位的監(jiān)管缺失,更為這些網(wǎng)貸機(jī)構(gòu)違法犯罪提供了直接的可乘之機(jī)。
首先,2015年出臺的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指導(dǎo)意見只是原則性規(guī)定網(wǎng)絡(luò)借貸業(yè)務(wù)由銀監(jiān)會監(jiān)管,而未明確網(wǎng)絡(luò)借貸行為的性質(zhì),這就使得該行為的諸多新變種難以納入我國金融行業(yè)“一行三會”監(jiān)管體系,這是監(jiān)管缺失的源頭。
監(jiān)管缺失,折射出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的滯后與缺位。
據(jù)介紹,網(wǎng)絡(luò)金融作為金融創(chuàng)新的產(chǎn)物,產(chǎn)品與服務(wù)推陳出新的速度確實(shí)令法律法規(guī)出臺的腳步望塵莫及,“時間差”始終存在;法律法規(guī)的滯后又使得監(jiān)管部門在實(shí)際工作中每每感到責(zé)權(quán)不明晰,猶豫之間缺位已出現(xiàn);我國目前出臺的網(wǎng)絡(luò)金融監(jiān)管法規(guī)大多由地方政府制定,層級低、針對性過于具體,難以統(tǒng)領(lǐng)需要多部門協(xié)同監(jiān)管的種種新生復(fù)雜現(xiàn)象。
更重要的是,長期以來我國關(guān)于民間借貸與網(wǎng)絡(luò)金融的法律規(guī)定,零散分布在種種行政規(guī)范性文件和司法解釋中,性質(zhì)界定不夠明確,缺乏必要的配套實(shí)施細(xì)則,操作性不強(qiáng),對迅速準(zhǔn)確判定貸款方是否構(gòu)成違法犯罪有一定障礙。
打造一套規(guī)范而有效率、兼顧靈活性與前瞻性的監(jiān)管制度才是有效監(jiān)管網(wǎng)絡(luò)金融的治本之策。尤其應(yīng)盡快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企業(yè)與相關(guān)部門通力合作,搭建效度力度兼?zhèn)涞姆欠ń鹑诨顒语L(fēng)險防控平臺,把非法網(wǎng)絡(luò)金融行為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 (所涉受害人與犯罪嫌疑人均為化名) (來源:半月談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