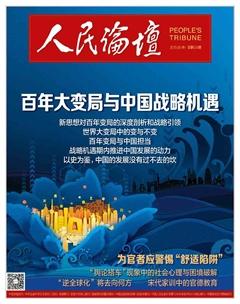宋代家訓中的官德教育
張熙惟
【摘要】宋代是中國古代家庭教育的繁榮期,家訓教育獨有千秋,家訓文獻卷帙浩繁。寓于家訓中的官德教育以修身養(yǎng)性、志存高遠,忠孝立身、傾心報效,廉潔奉公、勤政為要為基本內(nèi)涵,流風遺韻,澤被后世。
【關鍵詞】宋代 家訓 官德
【中圖分類號】K24 【文獻標識碼】A

今山東鄒城市鐵山公園孟子書院內(nèi),矗立著一通明代石碑,上刻北宋名臣陳瓘的十六字家訓——“事親以孝,事君以忠,為吏以廉,立身以學”,簡明扼要地展示出宋代家訓文化中“修齊治平”的深刻內(nèi)涵與“家國天下”的抱負情懷。
“天下之本在家。”“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家訓則是我國傳統(tǒng)家庭教育的教科書,正所謂“人必有家,家必有訓”。廣義的家訓,不唯有建章立制、形諸筆墨的傳世文獻,還有言傳身教、耳提面命的躬身示范。家訓既具勸諭性,也具約束性。宋代是中國古代家庭教育的繁榮期,家訓教育獨有千秋,熠熠生輝。家訓文獻體式浩繁,有片紙短章式的警句格言如《包拯家訓》,有卷帙繁富的輯錄之作如《溫公家訓》,有流傳甚廣頗具社會影響力的童蒙讀物如《童蒙訓》,有家訓總集的編纂如《戒子通錄》,還有數(shù)以千計的家訓詩賦如《集事詩鑒》等,擷英集萃,蔚為大觀,成為家訓文化興隆昌盛的顯著標志。
宋代家訓因家庭或家族各異,訓誡內(nèi)容千差萬別,各有千秋,但對敦親睦族、修齊治平的訓誨,卻是異曲同工,殊途同歸。修身正己、為政以德亦成為家訓中官德教育之主旨,流風遺韻,澤被后世。
官德修養(yǎng)之基:修身養(yǎng)性,志存高遠
宋代家訓以“修齊治平”為綱,立足于修身,著重培養(yǎng)具有理想抱負、志向高遠的人格品質(zhì),把勤學、立志、謙恭、節(jié)儉、功名、誠信等作為修身養(yǎng)性、為官之德的具體教育內(nèi)容。
宋代“崇文右儒”“以文治天下”,科舉制成為最基本的選官之制,“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成為普遍的社會共識和追求。署名宋真宗的《勸學詩》已直言不諱地將富貴利祿作為讀書向?qū)W的誘餌。讀書入仕成為不同階層家庭子弟通向榮華富貴的便捷之途,“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并非虛幻的社會現(xiàn)實。正緣于此,宋代家訓把勵志勉學、成才報國作為重要的教育內(nèi)容。
宋代家訓中多有修身立志的教誨,強調(diào)立身以立學為先,立學以讀書為本。宋初宰相范質(zhì)在《誡兒侄八百字》中說:“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yōu)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歐陽修在《誨學說》中說:“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人之性因物則遷,不學則舍君子而為小人,可不念哉?”以讀書增長知識,改變?nèi)说木駳赓|(zhì),教誨子孫。陸游則站得更高,他教育子孫要樹立以天下為己任、讀書為大眾的思想:“萬鐘一品不足論,時來出手蘇元元。”(《五更讀書示子》)朱熹在《朱子家訓》中也勸誡“詩書不可不讀,禮義不可不知”。
古人云:“德者,事業(yè)之基。”人無德不立,國無德不興。“儉以養(yǎng)德”,儉是修身養(yǎng)性的必由之途。儉用養(yǎng)廉、尚節(jié)崇儉是為官清廉的基礎,是入仕為官必備的品格,歷來被各氏家訓奉為美德。唐代李商隱就有“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的詩句。宋代家訓中的官德教育尤為注重對子孫“民生艱難”的教育。如仁宗朝宰相陳堯佐即以“居家以儉約為法”訓誡子弟。在《宋史》中被稱為“布衣宰相”的范純?nèi)实闷涓阜吨傺椭蹋粤畠€、忠恕立身,提出“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的教育思想。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中說,“眾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認為治家之道“以儉素為美”,反對“以奢靡為榮”,認為“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黃庭堅《家誡》中有“無私貪之欲,無橫費之財”之訓。趙鼎《家訓筆錄》認為“節(jié)儉一事,最為美行”。葉夢得《石林治生家訓要略》更是把節(jié)儉視為持家第一要務,說:“夫儉者,守家第一法也。”彭龜年也有“治家以儉”的教育思想:“惟儉與廉,治家及身。”倪思《經(jīng)鋤堂雜志》則說:“儉者,君子之德。世俗以儉為鄙,非遠識也。儉則足用,儉則寡求,儉則可以成家,儉則可以立身,儉則可以傳子孫。奢則用不給,奢則貪求,奢則掩身,奢則破家,奢則不可以訓子孫。”
宋代家訓專注把做人要誠信、立志要高遠作為修身養(yǎng)性的重要內(nèi)容。如《二程遺書》載:“欲當大任,須是篤實。”“學在誠知誠養(yǎng)。”“至誠可以贊化育,可以回造化。”又說:“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不行。”胡安國在家訓中教育子弟要“誠實無私”“以忠信為本”,提出“為政必以風化德禮為先,風化必以至誠為本”的思想。袁采在《袁氏世范》中特別強調(diào)忠、信、篤、敬的修養(yǎng),說:“人貴忠信篤敬。”“言忠信,行篤敬,乃圣人教人取重于鄉(xiāng)曲之術。蓋財物交加,不損人而益己,患難之際,不妨人而利己,所謂忠也。有所許諾,纖毫必償,有所期約,時刻不易,所謂信也。處事近厚,處心誠實,所謂篤也。禮貌卑下,言辭謙恭,所謂敬也。”程門四先生之一的謝良佐在《訓子求同理》中云:“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后世之慮。”南宋理學家胡宏在《知言》中也說:“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這清晰地表現(xiàn)出家訓中志存高遠、益世濟民、勵志教育的豐富內(nèi)涵。
居官入仕之本:忠孝立身,傾心報效
“在家盡孝、為國盡忠是中華民族的優(yōu)良傳統(tǒng)。”盡孝盡忠,崇尚官德,移家風于廟堂,體現(xiàn)著“家國情懷”中愛家與愛國的統(tǒng)一性。宋代家訓已把家庭教育與天下興亡、國家盛衰、家庭榮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家訓教育注重指向道德養(yǎng)成、人格塑造,強調(diào)價值引領,弘揚忠孝理念,以“家國情懷”為安身立命之所,熏染其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令之感受神圣而皈依。《孝經(jīng)》云:“夫孝,德之本也。”孝是立德之本,也是教化之源。“孝慈,則忠。”宋代家訓即把忠孝立身作為官德教育的重要內(nèi)容。范質(zhì)《誡兒侄八百字》詩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弟。”范仲淹《家訓百字銘》首句云:“孝道當竭力,忠勇表丹誠。”仁宗朝宰相賈昌朝在《戒子孫》中提出為官四準則“居家孝,事君忠,與人謙和,臨下慈愛”,把忠孝教育置于家訓之首。葉夢得《石林家訓》指出:“夫孝者,天之經(jīng)也,地之義也,故孝必貴于忠。忠敬不存,所率皆非其道。是以忠不及而失其守,非惟危身,而辱必及其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陸梭山在《居家正本》中說:“今行孝悌,本仁義,則為賢為知;賢知之人,眾所尊仰。”司馬光則提出“治身莫先于孝,治國莫先于公”的教育思想。
宋代家訓強調(diào)忠孝并重、移孝于忠。宋祁《庭戒》中有“入以事親,出以事君”之教。三朝宰相韓琦《戒子侄詩》云:“仁睦周吾親,忠義報吾主。”呂本中《童蒙訓》說,“事君如事親”“處官事如家事”“故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宋代抗金名臣李綱家族“世稟義方,教子以忠”。彭龜年告誡其子曰:“吾仕于國,無一世勤。乃于爾身,受一世恩。是恩欲報,悲忠不可。倘忠于君,即孝于我。”《宋史》記江西新喻劉氏家族“唯知事君,內(nèi)省不愧”。吳越會稽錢氏家族“家傳忠孝,世襲簪纓”。河南洛陽程氏家族“家傳忠孝,世受國恩”。“岳母刺字”是忠孝家教的光輝典范,文天祥在《哭母書》中說,“母嘗教我忠,我不違母志”,與岳母教子“精忠報國”可謂一脈相通。平生留下二百多首家訓詩的陸游,在其生命將盡的冬日里寫下遺言《示兒》:“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這是傳播最廣的家訓詩,鮮明體現(xiàn)了“家國一體”的情懷,飽含了盡忠愛國的教化意蘊。
忠孝教育培育傾心報效的道德情懷,涵養(yǎng)忠誠為公的官德。宋代家訓以“以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為己任”作為訓教目標,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使命教育為至高,培育人應有的擔當和責任感。若忠孝不能兩全時,家訓往往明確教誨子孫要先國后家、先君后親。葉夢得在《石林家訓》中說:“忠敬不存,所率皆非其道。是以忠不及而失其守,非惟危身,而辱必及其親也。”這充分體現(xiàn)了宋代士大夫深知“家國一體”“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
為官從政之道:廉潔奉公,勤慎為要
南宋學者程大昌在《演繁露·學官》中說:“官者,管也。”馬端臨在《文獻通考自序》中也說:“役民者,官也;役于官者,民也。”兩者皆從管理與被管理的視角作了官、民的區(qū)分。所謂“官”,既含有道德屬性,也具有職業(yè)屬性。官與民的區(qū)別,實質(zhì)是職業(yè)分途而非身份地位的高低。權力,治國之公器。“所謂官德,也就是從政道德。”為官操守、從政之道要求為民謀福利,而非為己營私利。哲宗朝宰相蘇頌在《訓子孫詩》中云:“操守不堅純,久必成緇磷。”
廉為政本,政從廉始。宋代家訓教育子弟為官從政,以清廉為第一要務。賈昌朝根據(jù)為官經(jīng)歷,在家訓中闡述為官從政之道“清廉為最”,認為緣此始“能守素業(yè),使門戶不辱”。范仲淹要求其侄“清心做官,莫營私利”。胡太初《晝簾緒論》論“蒞官之要曰廉與勤”。朱熹訓子為官以清廉律己、潔己清心、愛民勤政為急務。被蔡襄譽稱為“四賢”之一的余靖在《從政六箴》中指出:“抱公絕私,是為率職。”只有公而忘私,方能盡職盡責;只有持正公平,方能勤政廉潔。
廉能興邦,貪則喪國。官廉則政舉,官貪則政危。宋代家訓注重清廉勿貪的教育,如自幼接受母訓“清廉志行”教育的歐陽修,教育其子居官堅守清廉,存心盡公。蘇軾的《六事廉為本賦》則曰:“事有六者(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筆者注),本歸一焉。各以廉而為首。”他提出“功廢于貪,行成于廉”,視廉潔為從政做官的至高準則。自少便受父輩“廉直忠孝、世載令聞”教誨的陸游也告誡子孫:做官“一錢亦分明,誰能肆讒毀?”家頤《教子語》有“惟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利”之教。包拯說:“廉者,政之本也,民之表也;貪者,政之禍也,民之賊也。”他在家訓中告誡:“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宋太宗太平興國年間曾從后蜀孟昶的《頒令箴》中摘出“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四句詔告天下,訓誡百官。南宋初年,高宗命黃庭堅書寫這一祖訓頒于各府州縣,刻石立銘,告誡官員要奉公守法,嚴禁貪贓枉法。迄今在山東鄒城市鐵山公園孟子書院內(nèi),仍矗立著黃庭堅任鄒縣令時所書《戒石銘》碑。
勤政是為官之本,從政之道。趙鼎在《家訓筆錄》中提出:“凡在仕宦,以廉勤為本。”“一門四宰相”的官宦世家韓億家族尤為注重官德教育,韓億在《與子書》中即有“服勤職業(yè),一心公忠”之訓。胡安國在家訓中教育子弟為官處政“當一日勤如一日”。王邁撰有“愛民以仁、事親以孝、臨政以勤、律身以儉、聽言以公、制事以斷”等六箴。真德秀在《西山政訓》中把“廉、仁、公、勤”作為“為政之本領”——“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而某區(qū)區(qū)實身率之”。他舉東漢東萊太守楊震“懷四知之畏”而拒不受金之典故,告誡子孫“力修冰蘗之規(guī),各厲玉雪之操”:“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為大惡。”“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圣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況其余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游宴則謂之風流嫻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害也,不可不戒。”
史載真宗朝宰相王旦“以清慎訓諸子”,諸子秉承家訓,“亦恬于進取也”。余靖把“清、公、勤、明、和、慎”作為家訓箴言,提出清廉是從政的最大操守,是為政的重要原則,強調(diào)一心為公、勤政為民。呂本中在《童蒙訓》中說:“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恥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清四庫館臣為此評價:“清、慎、勤三字以為當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也。”康熙皇帝曾御書“清慎勤”三字刻石,賜內(nèi)外群臣。
宋代家訓中的官德教育還包括處事公正、民為政本等思想。如彭龜年即訓誡其子為政之要是“處事以公,舉職以勤,御吏以正,撫民以仁”。朱熹在《朱文公政訓》中云“為守令第一是民事為重”,告誡子孫“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個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彩,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個沒下梢”,提出“平民近民,為政之本”的恤民思想。劉子寰在《壽張倉》寫道:“喬木端由有世臣,傳家事業(yè)飽經(jīng)綸”,道出了家訓對傳承家風、勵志成才的教化作用。家訓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之重要組成部分,是陶冶情操、提升人文情懷的珍貴文化資源,也是歷經(jīng)風雨滄桑、砥礪積淀而成的中華文化基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華民族傳統(tǒng)家庭美德,銘記在中國人的心靈中,融入中國人的血脈中,是支撐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的重要精神力量,是家庭文明建設的寶貴精神財富。”
(作者為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