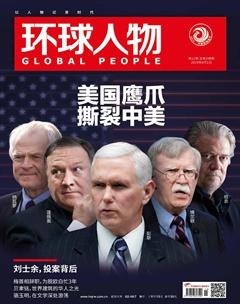駱玉明,在文學深處游蕩
王晶晶

駱玉明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很多相熟的朋友卻打趣他是“魏晉人”。他在復旦大學長年講授《世說新語精讀》,也許是因為由衷熱愛,被那些魏晉士人的風度氣質深深影響,人言駱玉明本人也頗有名士之風,行為灑脫、談吐脫俗。

駱玉明解注的《詩經》。
他喜歡茶酒和圍棋,曾為自己的古代文學史課選課代表,要求:男生,最好會下圍棋,課余以解棋癮。至于要男生的理由,他如此說道:“我總不能半夜兩點鐘打電話給一個女同學說,喂?你到我這里來一下吧?”
《環球人物》記者前去采訪,落座后,他特意問道:“要喝哪種茶?”煮水、燙杯……普普通通的一個杯子,也泡得十分講究。茶香清謐,與駱老師漫談古代文學,仿佛歷史上的那些吟詠、嘯聲,就在眼前。
《詩經》離現代人不遠
駱玉明最近一部與讀者見面的作品,是解注《詩經》。這部距離現代人數千年的著作,被配上精美插圖,隨文注音,悉心注解,以一副輕松、美好的樣貌呈現在讀者面前,創下首印1.2萬套在24小時內售罄的紀錄。
即便如此受歡迎,駱玉明卻很自謙,直言這版《詩經》“不以學術創見見長”,編撰的宗旨就在于文學閱讀的享受性,想讓閱讀本身“變得容易”。
很多年前,駱玉明便與《詩經》結緣。上世紀80年代初,他在復旦中文系當助教,曾跟隨朱東潤先生讀書。這位民國初年留英的學者,早在1933年就連續發表了4篇關于《詩經》的論文,后來集成一本書——《讀詩四論》(再版時改稱《詩三百篇探故》)。
駱玉明跟隨朱東潤先生讀書時,先生指定了3本必讀的本子:陳奐的《詩毛氏傳疏》、王先謙的《詩三家義集疏》、朱熹《詩集傳》,此外還要兼顧其他。每次駱玉明去圖書館看書,場面都很壯觀——他得將數種書在桌上攤開,鋪滿一桌,彼此對照著看。別人看書都坐著,他看書不但要站著,還得來回走動。
每周例行要用一個半天,去先生家談讀書心得,提出疑惑。“老先生比我年長近60歲,看我就像是個孩子。要是書讀得好,會直接拿個橘子獎勵我。”
野有死麕
一場野外邂逅的戀情
野有死麕 白茅包之
有女懷春 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 野有死鹿
白茅純束 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
無感我帨兮
無使尨也吠

駱玉明為《野有死麕》所寫的解題是:一場野外邂逅的戀情。書中還專門配上了關于麕的插圖。
有當年的基礎,駱玉明在解注《詩經》時對已有各家學說可謂了然于胸,“我們所做的工作就是盡可能準確,然后做判斷才能更有把握”。每首詩前面都有一句很簡短的解題,駱玉明寫得非常用心。“現在寫這個,肯定是現在的立場,不同于古代儒家的教化立場,也不同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那種過于政治化的解釋方法。就是說,盡可能地以一種比較實在的觀點回歸語言本身。”
比如《小雅·采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駱玉明的題解是:描述了戍邊軍士服役思歸,既忠于國亦戀其家的復雜心情。“戰爭是不得已的事,最好的生活是一種平靜的、安詳的生活。”
很多人覺得,《詩經》晦澀難懂,仿佛離當代人很遠。駱玉明卻認為:“《詩經》是中國人的一部元典。生活在變化,但人類根本性的關懷始終如一。”《詩經》中最美好的篇章都是關于愛情的。《關雎》為什么重要?它跟一般戀愛詩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它的愛情是跟婚姻聯系在一起的。“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中國的主流文化贊賞的正是這種“溫雅”的生活態度。
3000年前的年輕人,和今天的年輕人一樣,“只要有欲望,就會有愛情”。駱玉明說,比如《召南·野有死麕》(音同君),去見一個女孩,你空手去見是不行的,帶一頭鹿是必要的。連鹿都沒有,你怎么去“誘”女孩?《詩經》里說這些的時候都很坦然、很自然。“有的人讀《詩經》感覺古人好像沒事干才去談戀愛,我的感覺是,你做了很多事情以后,會覺得最后一生只干了一件事:你談過一次戀愛。”
在魏晉,人的內在智慧和人格的完美要重要得多
在復旦乃至整個學界,駱玉明都算是“怪胎”型學者,“我跟很多大學里的老師不同,他們通常把學術研究放在前面,我則只是一個字面意義上的讀書人。學術是要在一個領域不斷深挖的,像挖一口井一樣,我則覺得長期在一個專門領域內搞研究會破壞我讀書的樂趣”。
他像一個散漫、隨興的旅人,閑庭信步,悠然游蕩于文學深處。筆下的作品,彼此間往往跳脫得很遠。
駱玉明寫的第一部著作是明代文學家徐渭的評傳,后來還專門研究過明中葉的江南才士詩;他又寫過《老莊哲學隨談》,也用古詩文來談過禪;他和老師章培恒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由于突破了長期流行的文學史模式,寫得活潑、有趣,曾引起不小的轟動;他還解讀過《西游記》《金瓶梅》《紅樓夢》,合起來著成《游金夢——駱玉明讀古典小說》,讀得或歡樂,或老辣,總能品出不同的東西。

曹操接見匈奴使者,自覺長相不夠威武,就找了個身形高大的人代替自己,他本人則拿著刀站在邊上。
文學百家中,對魏晉士人的研究解讀也許算是駱玉明最為世人所稱道的。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他就給本科生開了兩門課程,一個是古代文學史,一個是《世說新語精讀》。駱老師的課,教室里總是滿滿當當,地上都坐滿了人。王安憶在復旦教書時,每周都會來聽駱玉明的課。作家閆紅曾寫道:“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駱玉明先生。他講課時,有一種魏晉士人的不羈與銳感,常常在不那么正經的談吐中點中本質。這種點評方式幫我甩脫了資深文學青年自建的窠臼,到現在,我都不喜歡太正式的論述,著迷于小李飛刀式的見血封喉。”
在學生們的記憶中,駱玉明總是匆匆忙忙地奔來上課,講課時風采畢現。“把切己的生命體驗融入豐富的知識學問之中,使得已經死去了的歷史、人物復活過來,歌哭談笑,淋漓盡致,仿佛那一切就發生在我們中間。”學者張新穎現在和駱玉明是復旦中文系的同事,但他至今仍記得,當年做學生聽駱老師講課時的那種酣暢淋漓。
在駱玉明的解讀中,魏晉是舊的政治解體、門閥制度形成的時代,“是思想自由、富于創造性的時代,同時也是對生命的痛楚特別敏感的時代”。這樣的轉型時期,人們發現歷史上曾建立的道德、規則,很多是可疑的和不真實的。于是,“在魏晉人的哲學中,他們感到在世俗的成敗中掙扎,往往會背離人更高的精神追求,世俗的成功不是人的最高價值的表現。相比之下,人的內在智慧和人格的完美要重要得多。”
他細細品究當時的文學、文人。比如,在《世說新語》的《識鑒》《容止》《豪爽》等篇目中,他看出了英雄與圣賢的區別,漢魏之際“從崇敬圣賢到崇尚英雄”,圣賢是儒家的完美人格,英雄則是著眼于人。
當時有個故事:曹操接見匈奴使者,自覺長相不夠威武,就找了個身形高大的人代替自己,他本人則拿著刀站在邊上,結果使者在會面后說:曹丞相不怎么樣,倒是邊上拿刀的那個家伙厲害!“可見當時對于人的精神氣質的重視。那時的主流思想是對個體的重視,認為世界上最可貴的是人,而在人中間最可愛的就是自我。”
“我不是一個與社會很有沖突的人”
年輕時,魏晉氣質曾深深影響駱玉明。他去火車站買票,等排到自己的時候才發現隊伍排錯了,于是就跟售票員說,“請隨意給我一張這個窗口賣的車票”,就這樣,放棄原本的目的地,去了銅陵。
但他對魏晉氣質的喜好很快跳過了放蕩不羈、悲苦無端的階段,進入到追求精神的明澈與通透。
上世紀90年代,他已經不再憤世嫉俗,而是一副對整個世界都和藹可親的樣子,惹得學生當面吐槽:“要是您10年前就這個樣子,誰還會把您當才子?”
駱玉明對自己之前那些行為,都評價為“矯情”。他曾說自己只是個俗人,與其他人的不同之處在于,“我知道自己是一個俗人”。采訪當日,提及早年寫過的一部現實感很強的著作,他還對《環球人物》記者強調:“我其實并不是一個與社會很有沖突的人。”他說,對于中國,需要深刻地理解歷史和她的長期變化。
在駱玉明看來,他們這代學者只是橋梁。“文化經歷了那么多年的破壞,重新恢復,我們都還處在這個過程中,這代人可能留下來的東西不多吧,但堅持著,只要能傳下去,也許未來就會有人在歷史中留下些什么。”
他的整個求學、教學生涯也的確是經歷特殊。“從小學四年級開始,除了看小說,我就其他任何事都不做了,不管語文課、數學課,還是別的什么課,只在課堂上悄悄看書。”中學去崇明島插隊,在農場種地,種得很努力,“個子很小,但是挑很重的擔子”。
那時推薦上大學,領導覺得像他這樣的人能吃苦,所以就推薦了他。第一次因為體檢不合格被刷下來,第二次,駱玉明考上了復旦招收的工農兵研究生。入學是1975年,畢業是1977年。念完研究生,原本有工作的人回原單位,沒有單位的就留在復旦。“初中沒畢業,讀了研究生,留校任教,就是這么奇特的年代和經歷。”
剛進復旦,駱玉明覺得自己沒有受過系統的教育,很擔心。后來發現還好,因為讀過的小說比其他同學都多。他從小就癡迷讀書,曾為了不被母親叫去干活,躲在墻的夾縫里讀,誰也找不到他。當年插隊時,知青們體力勞動之余都很無聊,駱玉明同樣被一種空虛所壓迫著。但如果能找到書讀,能夠從書里想一些事情,不管能不能想明白,生活就不至于那么乏味。
在當年的復旦校園,老一輩學者還是很多的,朱東潤、郭紹虞、陳子展、蔣天樞、趙景深……老先生們各有個性。駱玉明的導師是王運熙先生。畢業留校后,又作為青年教師派去跟朱東潤先生讀書,還跟過章培恒先生。三位老師,朱先生威嚴而親切,章先生思想銳利而明快,王先生最溫和。但駱玉明也最怕見王先生,“他特別細膩,每個問題都問得很仔細。”
“我對我的那一輩老師們非常有感情。我知道他們總是守著什么,他們總是在想能為國家做什么。我們這些人也是有這樣的念頭,做一個讀書人就要為國家守住一些東西,使她有更好的發展機會,這是我從我的老師們身上得到的最大的啟示。”
教書多年,常有學生請他題字留念,駱玉明寫得最多的是“人情開滌,日月清朗”,這8個字出自《世說新語》,東晉王胡之到吳興郡的印渚去,看了那里的風景,禁不住如此贊嘆。“人變得開朗后,就會看到世界的美好;人如果是閉塞的,看到的世界也是晦暗的。特別跟學生在一起時,我希望他們做開心的人,思想通達,能夠包容,有愛別人的能力,能看到別人的好、這個世界的好。”
在中國文學的長河里,駱玉明最喜歡的是司馬遷和魯迅。前者叩問生死大義,生命空間無比開闊。后者則帶給他很多共鳴與感動。比如魯迅也非常愛好魏晉。劉半農曾贈魯迅一副對聯:托尼學說,魏晉文章。說他愛好托爾斯泰、尼采的學說,而文章頗得魏晉風神熏染。魯迅的文學非常閎闊,又多有深情。“你讀《孔乙己》 《故鄉》……我最初一直想不明白為什么閏土讓人那么感動,后來忽然之間領會到那是兩個場景的對照,一個是少年活潑的美,黃澄澄的月亮下,帶著銀閃閃的項圈的少年,拿著一柄叉在刺猹;后來再見,卻是那樣一副景象。生命還沒有展開,就萎縮了。”
駱玉明曾說:“現代科技驅散了人們心中的幻夢,而商業文明則培養了精明實在的計較。古典的飄逸散淡作為生活態度大概是再也不可能了。我無意夸張文學在現實生活中的價值,也素不以守衛傳統文化為己任,只是從個人經驗說,覺得在焦慮煩躁的時分,偶爾能回到文學、回到詩意的心情,還是好的。”
這也是駱玉明講讀文學時能打動那么多人的原因,無關什么要義,就是簡簡單單,回歸到人本身。
駱玉明
生于1951年,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代表作有《簡明中國文學史》《近三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世說新語精讀》《美麗古典》《詩里特別有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