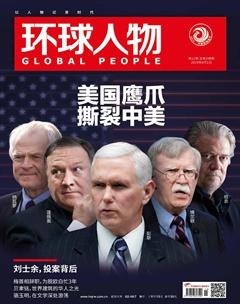雍正皇帝,患上“完美強迫癥”
陳娟
雍正在位時間不長,但爭議頗多。在稗官野史中,他背負著謀父、逼母、弒兄、屠弟、好殺等罪名;在清宮劇中,他糾纏于后宮爭斗、兒女情長;在正史記載中,他鐵腕行事,勤儉刻苦,凡事朝綱獨斷,寡語冷面。在這些早已深入人心的印象背后,雍正無疑還有另一張面孔。而這一面,或可從近日火爆的“雍正故宮文物大展”中細細品出。
“雍正故宮文物大展”日前正在上海奉賢博物館展出,展覽中的120件文物均來自故宮,其中有80件一直是藏品,未曾公開展出過。從雍正用過的璽印、服飾、武器到西洋眼鏡,再到由他參與指導、設計的瓷器、琺瑯器、玉器、硯臺等,記錄著他的日常生活,也印證著他嚴肅外表下,藏著一顆敏感、豐沛的文藝之心。
以退為進,韜光養晦
走過一段朱紅色的高墻,步入展廳,最先出現的是一方印章,上刻“圓明主人”四字。印章為壽山石所造,印紐上刻著3只獅子:大獅蹲坐;一小獅踏著大獅尾向上攀爬;一小獅蹬在大獅背上,前足伸向另一小獅。印章背后的墻上,懸掛著一幅畫,畫中女子身著藍色裘裝,一手搭在暖爐上御寒,一手持鏡自賞。女子身后還有一幅七言詩掛軸,字字墨色酣暢,飛揚飄逸,落款為“破塵居士題”,后綴“壺中天”“圓明主人”兩方印章。
“‘圓明主人‘破塵居士‘壺中天都是雍正皇帝還是雍親王時自取的雅號。”上海奉賢博物館館長張雪松說,這枚印章與其后的美人圖相互印證,共同展示了雍正在皇子時期的生活和心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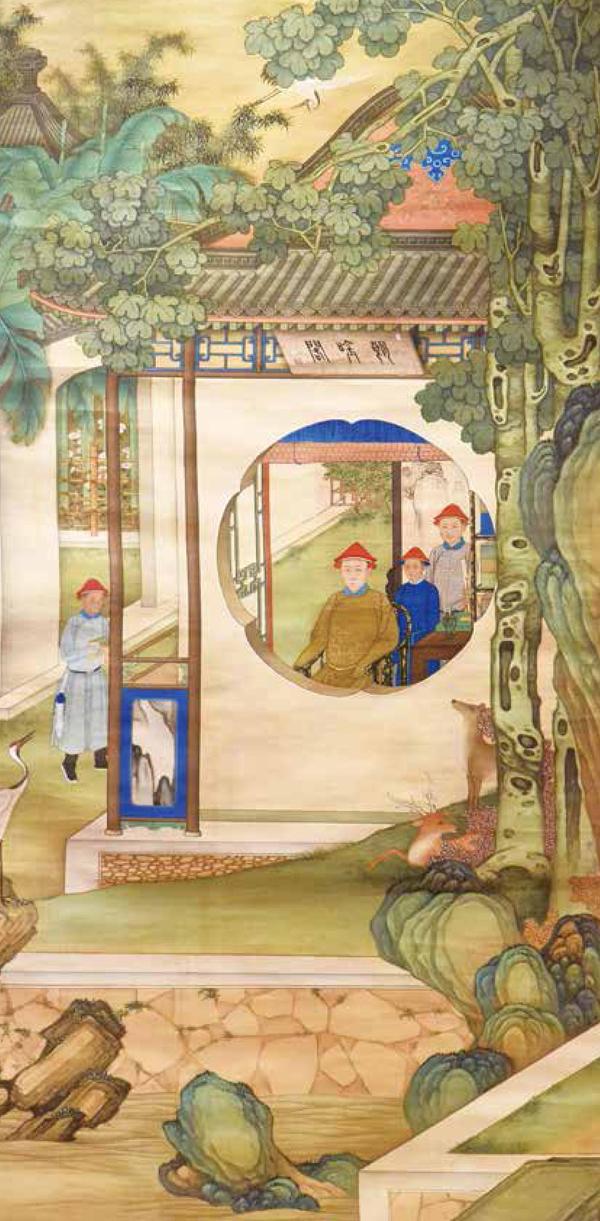
《胤禛朗吟閣圖像》。朗吟閣在圓明園內,雍正做皇子時曾在此居住。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皇四子胤禛被封為和碩雍親王,賜圓明園居住。他自號為圓明主人,展出的美人圖正是那一時期他請人所畫,名為《裘裝對鏡圖》。事實上,這樣的美人圖共有12幅。上世紀50年代,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在清點庫房時,不經意間發現了一組巨大的絹畫,共12幅,每幅高近兩米,寬近一米。一幅一像,都是著漢裝的清秀女子,或品茶,或讀書,或對鏡,或賞蝶。遺憾的是畫作都沒留作者款印,只有印章與題詩證明其與雍正有關。
直到30年后,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朱家溍在內務府的《活計檔》中發現一條記錄,上記載: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由圓明園深柳讀書堂圍屏上拆下美人絹畫十二張……深柳讀書堂位于圓明園福海西岸,雍正為圓明園所作詩中最頻繁出現的主題便是它,可見雍正對這里很是鐘愛。
這次“雍正故宮文物大展”中,還有一幅僅存的記錄雍正年輕時模樣的畫像《胤禛朗吟閣圖像》。畫上的胤禛頭戴涼帽、身著常服,端坐于窗前,周邊是鹿、鶴、嘉木,環境靜謐優雅。關于朗吟閣的美景,胤禛曾在詩作《秋日登朗吟閣寓目詩》中云:“縹緲遙峰帶夕曛,晴光歷歷望中分。橋移虹影當溪臥,風度蟬聲隔岸聞。數片晚霞三徑菊,一潭秋水半床云。高亭避暑才吟罷,又聽金飆送雁群。”
有美景,又有美人,偏居一隅的雍親王果真逍遙自在嗎?并非如此。其實,在圓明園生活的那一時期,對他來說恰恰是一段艱難的時光。當時太子胤礽被兩廢兩立,眾皇子為爭位攻訐暗斗,而胤禛始終沒有占據上風——康熙早年對他有成見,曾公開批評他遇事急躁,“喜怒不定”。于是,他不得不選擇以退為進,韜光養晦,內心的苦悶與郁結,只能隱于詩詞和畫作之中。像這幅《裘裝對鏡圖》,他在畫中題詩:“自驚歲暮頻臨鏡,只恐紅顏減舊時”,表面上是美人對鏡自憐,感慨時光易逝,細品則暗含懷才不遇、壯志難酬的隱衷。
做王爺的那段日子,胤禛每日里吟詩作畫,修習佛法,賞鑒古玩。即位后,他把當時所作詩詞整理成《雍邸詩集》,序言中寫道:“朕昔在雍邸,自幸為天下第一閑人……賦性不樂浮華,既無庸皇皇于富貴,更不煩戚戚于貧賤。”這一“天下第一閑人”把圓明園營造成田園詩般的世外桃源,也因此得到康熙的贊許——康熙曾親臨圓明園雍親王宅邸11次,這是其他皇子所沒有的殊榮。在頻繁的會面中,胤禛逐漸贏得了康熙的矚目和信任。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春天,圓明園中數百株牡丹開得正艷,胤禛提出請父皇來家中賞牡丹,康熙欣然應允。在這里,康熙第一次見到了胤禛的兒子、12歲的弘歷,贊賞有加,之后更是破例將他接到自己身邊養育。這一年的冬天,康熙病逝于暢春園,在遺詔中宣布:“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成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

《裘裝對鏡圖》,是雍正《十二美人圖》之一。
“工作狂”皇帝
1722年,胤禛登上帝位,自此開始了忙碌的治國理政生活。
與康熙仁慈寬厚大不相同,雍正為政勤勉苛刻。康熙朝有資格上奏折的臣工約200人,而雍正將人數擴充到了1000人以上,以至于雍正皇帝每天都要批閱數十件萬余字的奏折,自晨至暮,從未間斷。史書記載,雍正只在自己的生日那天才會休息,他在位的13年間,每天睡眠時間不足4個小時,在數萬件奏折上寫下的批語多達1000多萬字。
在挑燈批閱奏折時,他還常把這種情形順手寫在臣工的奏折上,以激勵文武大臣竭忠效力,勤勉為官。比如:“日間刻無寧晷,時夜漏下二鼓,燈下隨筆所書。”其實是在告訴臣子:白天沒有一刻安寧的時間,現在已是晚上二更時分,也就是后半夜,我依然還在工作。
雍正處理政務、批閱奏章大都是在養心殿的西暖閣,他在墻壁上懸掛著一副自己手書的對聯: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橫批“勤政親賢”。而為了做到“一人治天下”,他首創設立軍機處。這次大展的一大看點就是將故宮的軍機處做了還原。軍機處雖是朝廷的核心機構,實際上卻非常簡陋,由一個炕幾和兩個楠木炕桌組成,桌上擺放著燭臺、長方硯臺和紫毫筆。
雍正七年,清王朝派兵平定準噶爾部的叛亂,一時間軍情如火,急需立即處理,且要嚴守秘密,但當時的政治機構設置不盡如人意。清朝和明朝一樣,以內閣為國家行政中心。內閣設于紫禁城太和門外的文淵閣附近,與養心殿相隔1000余米。宮禁重重,很容易耽誤時機,而且軍報到京后,先經過內閣,也容易泄露機密。為此,雍正在隆宗門一帶的墻根搭建了一排平房,距離養心殿僅50余米,剛開始稱軍需房,后改稱軍機房,又改稱軍機處。
軍機處剛一設立,雍正就規定不管有多少公文,都必須當天完成。他以身作則,雍正五年四月十六日一天之內,就分11批召見了31位官員,做到了“今日事今日畢”。這可苦了軍機大臣,常常是凌晨3點,紫禁城一片漆黑,只有軍機處值廬中燈火通明。約莫五六點鐘,天剛蒙蒙亮,軍機大臣就要去養心殿面見皇帝,此時的皇帝已候在殿中。
在位13年,這位“工作狂”皇帝事事躬親,件件細琢。每年開春,皇家都有一項盛大活動——祭先農壇,他亦親力親為。
先農壇是明清兩代皇帝祭祀神農、祈求豐收的地方。據史料記載,在順康兩朝,皇帝僅是設立之初或者親政之初親自到先農壇祭祀,一般年份多是遣官代祭。到了雍正,除登基第一年未能親祭外,自雍正二年起至雍正十三年,他共親祭先農、親耕耤(音同及,特指帝王親自耕種田地)田12次。
當時的畫師繪制了一幅《雍正帝祭先農壇圖卷》,真實記錄了雍正參加這一皇家活動時的情景。整幅畫卷分上、下兩卷,分別為皇帝祭農神和扶犁耕耤田。此次文物大展展出的是藏于故宮的上卷,下卷現藏于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
畫中有一條御道,由右向左延伸,道路兩邊置燈。左側是眾多身著朝服的官員,離這些官員不遠,有30余名侍衛環列成一個半圓形,他們個個佩帶腰刀,肩扛旌旗,簇擁著一個身穿藍色朝服、露出黃色下擺之人,此人正是雍正。他看起來神情嚴肅,滿懷莊嚴感,緩步走向祭壇。

《雍正帝祭先農壇圖卷》(部分)。
雍正首次親祭先農的第二年秋天,全國各地就報“有瑞谷出現”,之后連續幾年都有嘉禾祥瑞之訊。這后來被認為是他年年親祭的原因之一,“在雍正看來,嘉禾祥瑞正是海宇升平、政治清明的體現,這也是他掌握朝中政治的一種手段”。 張雪松分析道。
“若不如意,朕不依”
繁忙的政務之外,雍正還醉心于藝術品的設計和制造。此次展出的雍正款花瑪瑙葫蘆式杯、雍正款畫琺瑯花蝶紋茶壺、菊瓣盤等,大都素凈文雅,工藝精湛。在這些精美器物的背后,既體現了雍正極高的審美,也有其嚴苛、獨斷的行事之風。
當年,即位不足半月,雍正就下旨命怡親王胤祥整頓養心殿造辦處。造辦處是清代制造皇家御用品的專門機構,于康熙年間成立,至康熙末年一度管理松散。雍正派最信任的兄弟怡親王去主持造辦處,足見對此事務的重視。
雍正曾給造辦處定下嚴格的工藝流程,凡下旨做的活計都要經過如下手續:皇帝下旨;承作者畫紙樣、或漩木樣、或撥蠟樣;呈覽皇帝提出意見;修改;再呈覽;批準;制作。在雍正朝《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里,隨處可見他要求把工藝品改得素凈簡潔些的旨意,遇到不滿意的器物,他常用的批語是“甚俗”“蠢了”。

雍正款菊瓣盤。

雍正款花瑪瑙葫蘆式杯。

雍正款畫琺瑯花蝶紋茶壺。
他曾命人將一件瑪瑙壺上的花紋磨去,“壺把做素的”;收到一方蓮艾硯,覺得很不好,批道“做素靜文雅即好,何必眼上刻花”;說“如意柄上‘萬壽無疆四字俗氣,著去平,照柄地仗壽字樣式刻做”……雍正最為反感的是流于俗套的平庸之作。雍正六年十月,玻璃廠曾呈進各色玻璃鼻煙壺100 個,隨后,郎中海望傳達了皇帝的諭旨:“此鼻煙壺款式甚俗,不好!可惜材料!爾持出放在無用處。”經過雍正的審視,入選的比例僅為59%。
雍正熱衷藝術品,并對藝術有自己獨特的審美,這或多或少受到康熙的影響。康熙興趣廣博,諸藝無所不能,對玻璃、琺瑯、鐘表、漆器都有興致,經常將一些藝術品賞賜給皇子們以增長見識。平日對諸皇子談及花園、房間的布局要廣宏敞居;對不引人注目的樹根、石頭、獸角、爪牙以至木葉之屬,“必隨其質而成一應用之器”。加之雍正自幼便離開生母,在孝懿仁皇后宮中長大,有更多的機會瀏覽各式精美的宮藏藝術品,耳濡目染,鑒賞的眼光自然獨到、犀利。
獨特的審美,使得雍正對藝術品特別挑剔,甚至有點兒完美強迫癥,有時極微小的一個細節,他都讓工匠修改多遍。
雍正十二年二月初,雍正讓造辦處制作一個關公塑像。一個月后,工匠呈上一個蠟像,他覺得關公的臉做得不好,提了一堆意見。10天后,改后的蠟像拿來,他還不滿意,又下旨:“關夫子臉像特低,仰起些來,腿甚粗,收細些,馬鬃少,多添些。廖化的盔不好,另撥好樣式盔。” 幾天后,雍正對第三次修改后的蠟像依然不稱心:“關夫子硬帶勒得甚緊,再撥松些。身背后無衣折,做出衣折來。鞋大鐙蠢,俱收小些。膝旁放高些。持刀的從神手并上身做秀氣著。”第四次呈送時,雍正還在挑剔:“帥旗往后些,旗上火焰不好,著收拾。馬胸及馬腿亦不好,亦著收拾。”工匠反反復復改了5遍,這才終于得到他的認可,說“甚好,準造”。
雍正對宮廷藝術品所作的諭旨,有時洋洋灑灑一大段,有時寥寥幾字,嬉笑怒罵全無避忌。而從這些諭旨,也能看出他本人的性情:他率真——和海望說“只要好,若不如意,朕不依”;他自信——言及琺瑯彩,稱“將來必造可觀”;他幽默詼諧——年羹堯向他求賞一兩件琺瑯器,“以滿臣之貪戀”,他爽快地賜下數件,并說“若不用此一貪字,一件也不給你”。
這些流傳下來的文物和文物背后的故事,或多或少讓后人看到了一個有著文藝心的雍正皇帝。嚴苛、勤勉、文藝、風趣,至于何為更真實的雍正,已無需追究了。正如他即位后找宮廷畫師為自己畫的一組《行樂圖》,在畫中他化身多種身份,或是仙風道骨立于懸崖邊的道士,或是山間題詩的文人,或是手拿鋼叉斗猛虎的勇士,或是松間撫琴的雅客……每一個都是有心裝扮的,但似乎每一個又都是真實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