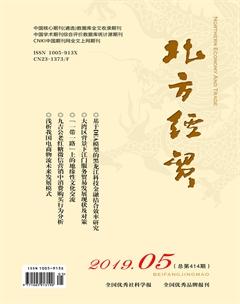“一帶一路”國(guó)家文化差異中企業(yè)對(duì)外投資策略
白云濤 張思娟 蔣經(jīng)緯
摘要:數(shù)據(jù)顯示,去年全球50%以上的并購(gòu)失敗,中國(guó)公司在海外的投資也有30%不盡理想。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跨文化方面的問(wèn)題沒(méi)有得到充分解決。該文利用Hofstede的文化維度理論,分析“一帶一路”相關(guān)國(guó)家的文化差異及其導(dǎo)致的企業(yè)投資與模式的不同,提出了在企業(yè)國(guó)際化的進(jìn)程中,需要合理規(guī)避文化沖突,加快不同文化融合。
關(guān)鍵詞:一帶一路;文化差異;Hofstede文化維度理論;規(guī)避沖突
中圖分類(lèi)號(hào):F812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5-913X(2019)05-0029-04
一、引言
在中國(guó)和平崛起與民族復(fù)興背景下,2013年秋,習(xí)近平主席著眼于國(guó)際國(guó)內(nèi)大局,順應(yīng)全球合作潮流和發(fā)展需要,在西行哈薩克斯坦、南下印度尼西亞時(shí),先后提出建設(shè)“絲綢之路經(jīng)濟(jì)帶”和“21世紀(jì)海上絲綢之路”重大倡議。“一帶一路”涵蓋全球約63%的面積,約44億的人口,沿線(xiàn)民族眾多、文化多樣。
建設(shè)“一帶一路”的合作重點(diǎn)是政策溝通、設(shè)施聯(lián)通、貿(mào)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shè)的社會(huì)之本。只有充分了解沿線(xiàn)國(guó)家的文化才能實(shí)現(xiàn)在文化信仰和價(jià)值理念上的溝通,以“文化相通”推進(jìn)“民心相通”,從而能夠?yàn)槠髽I(yè)“走出去”創(chuàng)造良好的社會(huì)基礎(chǔ)。
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引領(lǐng)下,越來(lái)越多的企業(yè)積極進(jìn)行海外市場(chǎng)開(kāi)拓。而企業(yè)海外市場(chǎng)進(jìn)入模式是企業(yè)國(guó)際化戰(zhàn)略的核心,它是企業(yè)將產(chǎn)品、技術(shù)、人力、管理經(jīng)驗(yàn)和相關(guān)資源轉(zhuǎn)移到其他國(guó)家的制度安排與合適方式,主要分為三類(lèi):出口、非股權(quán)進(jìn)入模式以及股權(quán)進(jìn)入模式(對(duì)外直接投資),包括通過(guò)獨(dú)資并購(gòu)或合資進(jìn)入模式。這些模式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其中與東道國(guó)的文化差異是其中一個(gè)重要因素。企業(yè)原所在國(guó)的文化環(huán)境,以及進(jìn)行商業(yè)活動(dòng)的其他國(guó)家當(dāng)?shù)匚幕拳h(huán)境因素,會(huì)影響該企業(yè)的國(guó)際化進(jìn)程。
企業(yè)在國(guó)際化經(jīng)營(yíng)中必然會(huì)面對(duì)來(lái)自不同地域文化的摩擦和碰撞,這會(huì)帶來(lái)一定的投資風(fēng)險(xiǎn)與經(jīng)營(yíng)阻礙。因此,為了更好地響應(yīng)“一帶一路”倡議,企業(yè)需了解各個(gè)國(guó)家不同文化及其特征。
二、研究現(xiàn)狀
母國(guó)與東道國(guó)之間存在的文化差異,是影響企業(yè)進(jìn)入模式的重要因素。企業(yè)在進(jìn)行直接投資時(shí),需要在獨(dú)資與合資的進(jìn)入模式之間做出選擇。關(guān)于文化差異與企業(yè)海外進(jìn)入模式關(guān)系的研究有較多成果。
蘇潔(2014)認(rèn)為:文化差異越大,企業(yè)在海外市場(chǎng)直接投資時(shí)越希望采取獨(dú)資經(jīng)營(yíng)的進(jìn)入模式。其原因是文化差異越大,在對(duì)投資進(jìn)行組合管理時(shí)增加的公司交易與經(jīng)營(yíng)成本使跨國(guó)公司進(jìn)一步發(fā)展面臨的危險(xiǎn)越大。為了減少交易成本,跨國(guó)公司在進(jìn)入海外市場(chǎng)時(shí)選擇高控制權(quán)的海外進(jìn)入模式。
張遠(yuǎn)等人(2009)則認(rèn)為:東道國(guó)與母國(guó)文化差異越大,跨國(guó)公司在投資時(shí)越傾向于選擇合資經(jīng)營(yíng)的模式;在文化差距大的東道國(guó)市場(chǎng)中放松對(duì)子公司的控制,可以作為減少不確定性和信息交換成本的一種手段。為了避免不確定性帶來(lái)的海外經(jīng)營(yíng)風(fēng)險(xiǎn),跨國(guó)企業(yè)通常會(huì)選擇與東道國(guó)企業(yè)合作的方式,利用東道國(guó)企業(yè)與政府的本土資源來(lái)開(kāi)拓當(dāng)?shù)厥袌?chǎng)。
甘筱青等人(2011)更進(jìn)一步認(rèn)為:不同文化的差異既表現(xiàn)在社會(huì)行為和社會(huì)習(xí)慣方面,也體現(xiàn)在更深層次的價(jià)值觀方面。這些差異會(huì)成為阻止不同文化直接順利交流的障礙,甚至可能產(chǎn)生誤解和沖突。通過(guò)多方面地綜合比較與分析,追尋差異產(chǎn)生的思想體系的根源,可以保證不同的文化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取長(zhǎng)補(bǔ)短,共同發(fā)展。在這個(gè)全球化時(shí)代里,只有彼此了解才能減少全球化所帶來(lái)的負(fù)面影響,避免文化的沖突。
盡管在東道國(guó)與母國(guó)文化差異導(dǎo)致跨國(guó)公司在東道國(guó)市場(chǎng)采取何種進(jìn)入模式方面存在不同看法,但跨國(guó)公司顯然必須充分考慮東道國(guó)的文化環(huán)境對(duì)公司今后的生存、運(yùn)營(yíng)與發(fā)展所帶來(lái)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所造成的額外成本能否找到其他的途徑加以彌補(bǔ),最終決定是選擇合資還是獨(dú)資模式進(jìn)入東道國(guó)市場(chǎng)。
東西方企業(yè)可能會(huì)發(fā)現(xiàn)由于文化影響而形成的諸如組織基礎(chǔ)、職業(yè)道德、進(jìn)取精神、努力成功、責(zé)任認(rèn)可、經(jīng)驗(yàn)獲取、激勵(lì)下屬和運(yùn)用法律等的公司文化差異。在文化因素的影響下,不同國(guó)家的企業(yè)擁有不同的經(jīng)營(yíng)價(jià)值觀,在商業(yè)模式,公司戰(zhàn)略,國(guó)際化模式方面都會(huì)有顯著的不同。
三、文化差異對(duì)跨國(guó)公司進(jìn)入模式的影響
早在十九世紀(jì),E. B. Tylor (1871)就提出了“文化”的定義,他認(rèn)為一個(gè)人身為社會(huì)成員所獲得的復(fù)合整體都可以被稱(chēng)為文化,包括知識(shí)、信仰、藝術(shù)、道德、法律、風(fēng)俗等等,也包括其他的能力和習(xí)慣。也就是說(shuō),文化首先是一個(gè)復(fù)雜的整體,但又包含多個(gè)層面,每個(gè)層面的表現(xiàn)形式有不同。為了進(jìn)一步分析和比較不同的文化,Geert Hofstede提出了他的國(guó)家文化維度理論。Geert Hofstede研究不同國(guó)家的文化特征,在四個(gè)不同的文化維度(power distance權(quán)力距離,Individualism個(gè)人主義,uncertainty avoidance不確定性避免,Masculinity文化性別)上定性和定量地比較分析不同國(guó)家人們的文化和行為。Geert Hofstede 和另一位學(xué)者M(jìn)ichael Harris Bond后來(lái)又提出了第五個(gè)維度“長(zhǎng)期導(dǎo)向-短期導(dǎo)向”,用于補(bǔ)充和發(fā)展他的國(guó)家文化維度理論。
對(duì)各國(guó)價(jià)值觀和文化的測(cè)量,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是Hofstede的成果。他的五個(gè)文化維度是用來(lái)衡量不同國(guó)家文化差異、價(jià)值取向的一個(gè)有效架構(gòu):
權(quán)力距離是指“一個(gè)社會(huì)對(duì)組織機(jī)構(gòu)中權(quán)力分配不平等的情況所能接受的程度。”在權(quán)力距離大的文化中,下屬對(duì)上司有強(qiáng)烈的依附性,人們心目中理想的上司是開(kāi)明專(zhuān)制君主;在權(quán)力距離小的文化中,員工參與決策的程度較高,下屬在其規(guī)定的職責(zé)范圍內(nèi)有相應(yīng)的自主權(quán)。
個(gè)人主義是指一個(gè)松散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假定其中的人們都只關(guān)心自己和最親密的家庭成員;而集體主義是在一個(gè)緊密的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中人們分為內(nèi)部群體與外部群體,人們期望所在的那個(gè)內(nèi)部群體照顧自己,而自己則忠誠(chéng)這個(gè)內(nèi)部群體。
不確定性避免是指一個(gè)社會(huì)對(duì)不確定和模糊態(tài)勢(shì)所感到的威脅程度,試圖保障職業(yè)安全,制訂更為正式的規(guī)則,拒絕越軌的觀點(diǎn)和行為,相信忠誠(chéng)和專(zhuān)業(yè)知識(shí)來(lái)規(guī)避上述態(tài)勢(shì)。
文化性別包括男性氣質(zhì)與女性氣質(zhì),是指“社會(huì)中男性?xún)r(jià)值觀占優(yōu)勢(shì)的程度,即自信、追求金錢(qián)和物質(zhì)、不關(guān)心別人、重視個(gè)人生活質(zhì)量”;其反面則是女性?xún)r(jià)值占優(yōu)勢(shì)。
長(zhǎng)期導(dǎo)向性、短期導(dǎo)向性表明一個(gè)民族對(duì)長(zhǎng)遠(yuǎn)利益和近期利益的價(jià)值觀。具有長(zhǎng)期導(dǎo)向的文化和社會(huì)主要面向未來(lái),較注重對(duì)未來(lái)的考慮,對(duì)待事物以動(dòng)態(tài)的觀點(diǎn)去考察;注重節(jié)儉和儲(chǔ)備;做事留有余地。短期導(dǎo)向性的文化與社會(huì)則著重眼前的利益,注重對(duì)傳統(tǒng)的尊重,注重負(fù)擔(dān)社會(huì)的責(zé)任;在管理上最重要的是此時(shí)的利潤(rùn),上級(jí)對(duì)下級(jí)的考績(jī),要求立見(jiàn)功效,急功近利。
筆者沿用Hofstede的這種劃分方法,選取我國(guó)對(duì)外投資凈額前十位中的部分國(guó)家與我國(guó)的文化指數(shù)進(jìn)行對(duì)比研究。文化維度的各項(xiàng)指標(biāo)如圖表1,其中為了清晰表達(dá),第四、五個(gè)維度用“男性主義、長(zhǎng)期導(dǎo)向”標(biāo)注。
根據(jù)Hofstede的文化維度理論,權(quán)力距離高的國(guó)家,上級(jí)在決策時(shí)權(quán)利較大,所以來(lái)自高權(quán)利距離的國(guó)家可能偏好獨(dú)資進(jìn)入模式;低權(quán)力距離的國(guó)家同事關(guān)系較為平等,因此投資者比較喜愛(ài)控制程度低的合資進(jìn)入模式。
在個(gè)體主義文化中,員工被看成是既擁有經(jīng)濟(jì)需求又有心理需求的人,比較關(guān)心個(gè)人利益,相信成功來(lái)自自我?jiàn)^斗;在集體主義文化中,每個(gè)員工會(huì)根據(jù)自己在群體中的利益行事,善于與人合作。所以,個(gè)人主義指數(shù)較高的國(guó)家越傾向于選擇獨(dú)資的進(jìn)入模式。
不確定性避免指數(shù),反映了一國(guó)管理者對(duì)待和處理不確定環(huán)境的態(tài)度。來(lái)自不確定性避免程度較高的國(guó)家管理者,大多數(shù)是風(fēng)險(xiǎn)規(guī)避型的,他們會(huì)制定嚴(yán)格的內(nèi)部規(guī)章制度來(lái)處理不確定性的問(wèn)題,所以在進(jìn)入海外市場(chǎng)時(shí),他們會(huì)比較謹(jǐn)慎。而來(lái)自于不確定性避免程度較低的國(guó)家的管理者,大多是風(fēng)險(xiǎn)喜好型的,他們較少用嚴(yán)格的規(guī)章制度來(lái)規(guī)避風(fēng)險(xiǎn)。所以,不確定性避免指數(shù)越高的國(guó)家越傾向于選擇合資的進(jìn)入模式。
男性主義指數(shù),反映了一國(guó)管理者對(duì)于社會(huì)中男性角色的態(tài)度。在男性主義國(guó)家中,人們普遍喜歡炫耀,喜歡比較外在的東西。在女性主義國(guó)家中,人們認(rèn)為關(guān)系和合作比金錢(qián)更重要,更關(guān)注于生活的質(zhì)量。
長(zhǎng)期導(dǎo)向指數(shù),意味著培育和鼓勵(lì)以追求未來(lái)回報(bào)為導(dǎo)向的品德——尤其是堅(jiān)韌和節(jié)儉。與之相對(duì)的短期傾向,意味著培育和鼓勵(lì)諸如尊重傳統(tǒng)、維護(hù)面子,以及履行社會(huì)義務(wù)等品德。
從表1中可以看出,在權(quán)力距離指數(shù)方面,亞洲國(guó)家普遍高于歐美國(guó)家。根據(jù)Hofstede 理論,由于自身的文化特點(diǎn),亞洲國(guó)家的企業(yè)進(jìn)行直接投資時(shí)更傾向于采用獨(dú)資的模式,而歐美國(guó)家的企業(yè)更傾向于采用合資的模式。在個(gè)人主義指數(shù)方面,亞洲國(guó)家相對(duì)歐美國(guó)家較低,這些國(guó)家的企業(yè)對(duì)外直接投資時(shí)更傾向于選擇合資的模式。這兩個(gè)方面的推導(dǎo)結(jié)論似乎矛盾,但我們注意到Hofstede 理論的形成是在20世紀(jì)80年代,而在當(dāng)代,上述亞洲國(guó)家均已進(jìn)行了以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為導(dǎo)向的改革,其“個(gè)人主義指數(shù)”已呈較高的增長(zhǎng)態(tài)勢(shì)。
在不確定性規(guī)避指數(shù)方面,美國(guó)和德國(guó)的較高,新加坡的指數(shù)較低,其他國(guó)家與中國(guó)一樣處于中間水平。較高的不確定性規(guī)避指數(shù)決定了德國(guó)和美國(guó)在對(duì)外投資時(shí)選擇合資的模式,而新加坡較低的指數(shù)決定了其對(duì)外直接投資時(shí)傾向于采用獨(dú)資模式。
在男性主義方面,除泰國(guó)外,其他國(guó)家與中國(guó)的男性主義指數(shù)沒(méi)有太大的區(qū)別。較低的男性主義指數(shù)決定了泰國(guó)在對(duì)外直接投資方面,更傾向于選擇合資的模式。在長(zhǎng)期導(dǎo)向指數(shù)方面,中國(guó)明顯高于其他國(guó)家。
四、文化差異對(duì)我國(guó)企業(yè)國(guó)際化模式的影響
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我國(guó)企業(yè)逐步走出國(guó)門(mén)進(jìn)行對(duì)外投資或海外并購(gòu)。由于文化差異的影響,中國(guó)企業(yè)在對(duì)外投資時(shí),一般傾向于采用獨(dú)資的模式,或采用獨(dú)資與合資相結(jié)合的模式,同時(shí)更加注重其企業(yè)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能力。同時(shí),隨著我國(guó)經(jīng)濟(jì)實(shí)力的不斷擴(kuò)大,特別是近二十多年的不斷探索,考慮包括各國(guó)文化差異不同的因素,我國(guó)企業(yè)的國(guó)際化開(kāi)始呈現(xiàn)出一系列新的特點(diǎn)。
(一)對(duì)外投資凈額持續(xù)上升,與“一帶一路”沿線(xiàn)國(guó)家合作成為亮點(diǎn)
我國(guó)的對(duì)外投資合作健康有序發(fā)展,與“一帶一路”沿線(xiàn)國(guó)家合作成為亮點(diǎn),且對(duì)新興市場(chǎng)國(guó)家的投資明顯增加。2016年,我國(guó)企業(yè)共對(duì)全球164個(gè)國(guó)家和地區(qū)的7961家境外企業(yè)進(jìn)行了非金融類(lèi)直接投資,累計(jì)實(shí)現(xiàn)投資1701.1億美元,其中對(duì)“一帶一路”沿線(xiàn)國(guó)家直接投資145.3億美元。如圖1所示,我國(guó)對(duì)東南亞新興市場(chǎng)國(guó)家的投資呈現(xiàn)明顯的增加。
(二)對(duì)外投資結(jié)構(gòu)不斷優(yōu)化,實(shí)體經(jīng)濟(jì)和新興產(chǎn)業(yè)受到重點(diǎn)關(guān)注
2016年,我國(guó)企業(yè)對(duì)制造業(yè),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shù)服務(wù)業(yè)以及科學(xué)研究和技術(shù)服務(wù)業(yè)的投資分別為310.6億美元、203.6億美元和49.5億美元。其中對(duì)制造業(yè)投資占對(duì)外投資總額的比重從2015年的12.1%上升為18.3%;對(duì)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shù)服務(wù)業(yè)投資占對(duì)外投資總額的比重從2015年的4.9%上升為12.0%。
(三)開(kāi)展國(guó)際化經(jīng)營(yíng)的模式不拘一格
考慮到我國(guó)與東道國(guó)的文化差異,為了緩解東道國(guó)的民族情緒,減少政治、經(jīng)濟(jì)風(fēng)險(xiǎn),擴(kuò)大資金來(lái)源以及加強(qiáng)企業(yè)集團(tuán)化的趨勢(shì),在國(guó)際市場(chǎng)開(kāi)拓方面開(kāi)始采用合資與獨(dú)資相結(jié)合,并購(gòu)與收購(gòu)相協(xié)調(diào)的更加靈活多樣的模式。
2016年全年,我國(guó)企業(yè)共實(shí)施對(duì)外投資并購(gòu)項(xiàng)目742起,實(shí)際交易金額1 072億美元,涉及73個(gè)國(guó)家和地區(qū)的18個(gè)行業(yè)大類(lèi)。其中對(duì)制造業(yè),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shù)服務(wù)業(yè)分別實(shí)施并購(gòu)項(xiàng)目197起和109起,占我國(guó)境外并購(gòu)總數(shù)的26.6%和14.7%。
(四)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大融合,為推動(dòng)國(guó)內(nèi)外發(fā)展注入強(qiáng)大動(dòng)力
5年的發(fā)展與奮進(jìn),使“一帶一路”從理念轉(zhuǎn)化為行動(dòng)。5年來(lái),中國(guó)在沿線(xiàn)國(guó)家建設(shè)境外經(jīng)貿(mào)合作區(qū)82個(gè),累計(jì)投資289億美元,為當(dāng)?shù)貏?chuàng)造了24.4萬(wàn)個(gè)就業(yè)崗位,釋放各國(guó)發(fā)展?jié)摿Α5?018年5月,中國(guó)已與24個(gè)國(guó)家和地區(qū)簽訂了16個(gè)自由貿(mào)易協(xié)定,自貿(mào)伙伴遍及四大洲,約一半是“一帶一路”沿線(xiàn)國(gu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