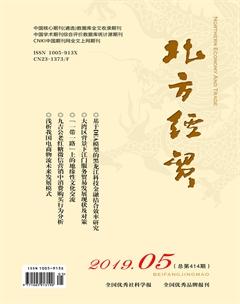組織管理理論視角下新型鄉村社會組織建設
陳祥敏
摘要:基于組織管理理論視角并以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甚至貧困地區的鄉村為主要參照,就新型鄉村社會組織的培育與建設,與“鄉村振興:培育新型鄉村社會組織”一文進行了基本理論、組織與職能及治理力量等三方面進行了商榷,提出了差異性認知觀點。
關鍵詞:組織管理理論;鄉村社會組織;差異認知
中圖分類號:F830.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9)05-0040-02
中國社會科學報公共管理版2018年5月16日刊發的陸丹教授“鄉村振興:培育新型鄉村社會組織”一文,立足國家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結合當前鄉村發展的主要目的與任務,依托中央和各地方政府近幾年來相繼出臺的“積極培育社會組織”政策文件,以欠發達地區尤其是貧困鄉村的社會組織為分析對象,為該類型鄉村新型社會組織的培育與構建進行了創新理論分析,提出了有效的建設性意見。
在此,基于組織管理理論視角并以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甚至貧困地區的鄉村為主要參照的鄉村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等情況持續多年觀察思考,與陸丹教授就三方面差異性認知商榷。
一、基本理論方面商榷
什么是鄉村社會組織?什么是新型鄉村社會組織?搞清這些基本概念對于研究問題具有重要意義,既是有效落實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社會組織培育政策的參考理論依據,又是研究鄉村的社會組織在鄉村振興中的地位、功能與作用等問題的基本前提等。應該說,培育新型鄉村社會組織是討論未來鄉村發展面臨的十分重要的話題,正如文中提出“培育新型鄉村社會組織,對鄉村振興的方案制定與實施路徑具有積極的作用”。然而,文中未對新型鄉村社會組織進行理論定義性界定的明確表述。雖然中國社會組織的內涵、特點、特征和類別早已有理論性界定。但是,把欠發達地區尤其是貧困鄉村的社會組織作為主要分析對象來構建新型鄉村社會組織的理論分析體系是具有創新性的,這從客觀上就確立該新型社會組織不僅具備社會組織的共性和個性理論特征,而且時代的變遷、環境的變化和社會的進展等又將賦予其不同內涵與特征內容。同時,該新型社會組織隨著分析工具、理論依據和觀察視角的創新等因素驅動,也將更加彰顯其特定個性新內涵、新特征內容。因此,無論是作為理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都非常有必要對其從理論上進行重新定義和特征與類型闡述,展現研究的有的放矢、對象精準,從而以強化文中客觀依據性、邏輯適當性。事實上,新型鄉村社會組織從組織理論上定性應為“非正式組織+非經濟組織”,其從組織完整性上相對獨立于正式組織的基層政權、村組織及經濟體,但在很大程度上緊密結合甚至依附于這種政權性及經濟性正式組織,才有其合法存在甚至發展的土壤及非營利下的自我可持續運營資源保障。另外,管理已從分工發展到協同,中國社會整體轉型現代化建設新時代,但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差異,使得一般由規范、地位、角色和權威四個要素構成的新型鄉村社會組織,體現出整合、協調、利益維護、自我完善及目標實現等五項功能,以及在已具備民間性、自愿性、自治性、非營利性、公益性、目標性、競爭性和獨占性特征基礎上,再擴展了功能成長性、制度化結構性、行動規范性和系統開放性等新特征。
同時文中認為,因為“學界一般用社會理論的國家與社會分析工具,以社會理論沖突論的分析視角,將鄉村社會組織放在基層政權的層面考量”“并沒有充分重視各種各樣的地方性差異”而認為上述分析工具、依據理論和觀察視角存在不足或已不適用,需要改良或更換。而且,還指出“發達地區的鄉村社會組織與欠發達地區的鄉村社會組織,并不具有同一性”、資源稟賦差異使“欠發達地區的鄉村尤其是一些貧困鄉村……對政府的依賴程度較高”等事實,提出了貧困鄉村振興,既要鄉(鎮)基層政權和村組織運用政策輸血造血,又要通過吸納有新型鄉村社會組織參與的中國式社會治理進行額外輸血。這些只是策略性、方式性的內容,并沒有明確展現出改良的或新的具體內容來替代或置換已被認為存在不足或已不適用的原分析工具、理論依據和觀察視角,以致從邏輯上有失去理論支撐之嫌——不破不立、破則當立。
二、組織與職能方面商榷
首先,“鄉(鎮)村級基層政權”提法是否有誤?根據2018年3月11日修正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條和第一百一十一條內容,村不屬于基層政權,建議將文中“鄉(鎮)村級基層政權”改為“鄉(鎮)基層政權和村組織”“ 要充分發揮縣鄉(鎮)兩級與鄉村基層政權組織主力軍的作用”改為“要充分發揮縣鄉(鎮)兩級政權與村組織主力軍的作用”等。
其次,社會動員是鄉(鎮)基層政權和村組織的固有職能,無需轉變。文中提出的整合傳統鄉村社會組織需要額外注重發揮的積極性之一為“鼓勵鄉(鎮)村級基層政權組織轉變職能,即從政治動員功能轉向社會動員功能”,而中國特色的現今社會治理架構決定了社會動員是鄉(鎮)基層政權和村組織的固有職能,因此無需轉變,只需強調或強化。同時,作為正式組織的鄉(鎮)基層政權和村組織,其基于政治、經濟和社會管理因素的綜合考量,對非正式組織的“鄉村社會組織”指導或管理不可能也不應該缺位自身固有職能或功能作用的發揮。況且,文中也提到“近幾年來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相繼出臺了‘積極培育社會組織政策文件”,并且十九大報告也提出賦予社會組織與其它組織一致的政治與社會權益,這些都是對基層政權和村組織在管理與培育社會組織職能的責任強化或促進,也正是基層政權和村組織一直以來對該項職能的持續有效履行,才成就了“欠發達地區的鄉村社會組織對政府的依賴略高”這一現狀。
三、治理力量方面商榷
對將威望長者作為欠發達地區尤其是貧困鄉村社會組織治理主流現象有異議。威望長者參與的鄉村社會組織治理,在現今并非主導或主流現象,且并不主要取決于發達、欠發達甚至貧困等經濟性差異,以及資源稟賦的有無因素,倒是與鄉村文化傳承、血緣宗親等更具備附著力。所以,該現象不具有普遍性或代表性。同時,雖基于資源、內生動力等原因在發展速度和數量上欠發達地區尤其是貧困鄉村的社會組織比不上部分發達地區的鄉村社會組織,但因為打工現象的區域綜合互動、多元信息傳播的多途徑連接等因素影響,這些欠發達地區尤其是貧困鄉村社會組織不斷受到發達地區鄉村社會組織的影響甚至同化,并已逐步呈現出多元化苗頭或態勢或局部突破,威望長者治理的補充即使存在也僅僅是眾多元之一而已,并非一種主流代表形態。
另外,針對把“回鄉創業人員的積極性”作為欠發達地區“培育新型鄉村社會組織”主要額外發揮積極力量之一,提出后面“公婆之理”觀點供參考。在欠發達地區尤其是貧困鄉村,經歷過思想與行為洗禮的回鄉創業人員,之所以回鄉創業,是基于多因素的綜合評價后的選擇,事實上大都已脫離了“鄉村”的他們所返的創業之“鄉”基本已偏離傳統“鄉村”范疇,也即所謂的返鄉不歸土。即使個別人員成長為回報故土的鄉賢,也因關聯性不緊密或不可持續而難成現象級,發揮作用有限。同時,很多返鄉的打工二代——他們也可劃入回鄉創業人員范疇,除了基于惠農政策或鄉土牽掛仍保留鄉村宅基地外,基本不愿回到故土型“鄉村”,以致建設新型鄉村社會組織也難以指望上他們。貧困鄉村空心化已是不爭的事實,沒有得到規模化甚至集約化的土地撂荒面積越來越大,以及近日關于眾多四線縣市級城市房價紛紛過萬的報道等事實,也許是“回鄉創業人員的積極性”難以利用的佐證之一。所以,基于鄉村長遠和穩定發展考量,除鄉(鎮)基層政權和村組織依托政策或制度發揮積極主導作用外,真正能成為新型鄉村社會組織建設主導力量是已打工失能或失去打工比較優勢而返鄉的,并立足原生態鄉村的、有思想和見識的返鄉農民,以及參與或介入農村土地集約化利用或涉農的經濟組織或非政府社會服務組織。進村幫扶企業、救助或資助慈善組織為國家精準扶貧政策落實發揮了很積極作用,但因其自身使命或資源額度等必要限制,難以成為“鄉村社會組織慢慢形成”歷程的可持續造血陪伴,因而其組織管理特長等優勢利用有限。
參考文獻:
[1] 陸丹.鄉村振興.培育新型鄉村社會組織[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05-16.
[2] 楊 琴,黃智光.新型社會組織參與鄉村治理研究——以鄉賢參事會為例[J].理論觀察,2017(1).
[3] 宋仕平,王雪霞.鄉村社會非政府組織的發展困境與路徑選擇[J].三峽大學學報,2018(3).
[責任編輯:王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