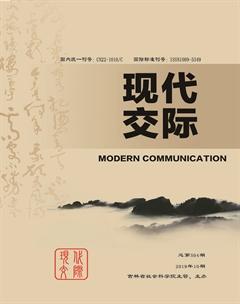戴望舒與現代派詩歌象征手法的變調
莊澤遠 車延宏
摘要:20世紀30年代,現代派詩歌在中國詩壇崛起,它們主張表現現代人在現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現代情緒。同時,現代派詩歌受到法國象征主義詩歌的深刻影響,在藝術表現形式上普遍有所呈現。其象征主義風格以李金發是為濫觴,至戴望舒之早期詩作已浩浩湯湯。然而李詩“但開風氣不為師”,實際上,象征主義經過了李金發對象征主義的粗淺摹仿到郁達夫對象征手法進行本土化改造的變調。本文將論證戴詩對繼李詩以來的現代派詩歌象征手法的革故,并進行一定的橫向比較,呈現出象征手法的具體變遷。
關鍵詞:象征手法 戴望舒 音樂美 傳統經驗
中圖分類號:I22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9)10-0096-02
一、從忽視音樂美到追求音樂美的變調
李金發于1919年赴法國留學,詩風直接受到象征主義詩人影響,尤其是波德萊爾、魏爾倫的影響。他一反通行直說、坦白舒放的詩風,運用奇譎的暗示手法與晦澀冷僻的意象,表現出“新奇怪麗的歌聲”,喚起了詩界的關注。比如《夜之歌》:“我們散步在死草上,悲憤糾纏在膝下”“粉紅之記憶,如道旁朽獸,發出奇臭”“我已破之心輪,永轉動在泥污下”;《棄婦》:“長發披遍我兩眼之前,遂割斷了一切羞惡之疾視,與鮮血之急流,枯骨之沉睡。”這些詩的主題包含丑惡、死亡、污血、死尸等意象,灰色的主題和意象體現了類似《惡之花》般審丑的審美傾向的特質,無怪乎李金發被評論家冠以“詩怪”的稱號。同時,透過詩篇可以勘察出李詩在刻意追求意象、意境的奇異冷僻時,已然忽略了對詩的音樂美的追求與型塑。換言之,音樂美在李金發筆下是缺席的。
反觀戴望舒的詩篇,則盡顯現著雕琢的痕跡,其中以《雨巷》最為突出。葉圣陶曾這么評價:《雨巷》創造了新詩音樂美的新紀元。“新紀元”意味著戴望舒以前的現代詩詩人在音樂旋律感的追尋中,尚達不到戴望舒的水平。需要專門辨析的是,戴詩之所謂“音樂美”,是迥異于新月派之追求音樂美的詩學理想的。新月派主張的音樂美是追求現代漢語所特有的一種節奏,即力圖創造一種新的手法,來營造古典詩詞基于單音節字格律所營造的節奏。但是戴望舒并沒有重復新月派的道路。作為《現代》雜志主要的作者,作為現代派詩人,他所張揚的風格是用現代語言表現現代人的現代情感。而其中指涉的音樂美,是法國象征派詩人魏爾倫、蘭波、馬拉美等人所運用詩歌手法。即在詩歌的句子中間利用特有的技巧,比如重復、停頓把詩的節奏加快或者放慢,從而更好地傳遞詩情。以蘭波為例:
Theres a sense somethings missing…
Wheres the mother of these little things,
Sweet-smiling mother with triumphant eyes
So last night, alone, stooping, she forget
To stir the fading fire into life,
To pile on blankets, eiderdowns,
Before she left the room, calling out ‘Forgive me!
這首《孤兒的新年禮物》書寫母親剛去世的孤苦無依的孩子,他們躲在窗簾后做著母親回來的美夢。第一段引文,“這時人們才發覺,屋里似乎缺少了什么……——這兩個孩子沒有母親,沒有甜甜微笑,脈脈含情的母親?她一定忘記了在夜晚獨自俯身,忘記了撥開熄滅的灰燼,生一堆火,忘記了給他們蓋上毛毯和鴨絨被,忘記了在離開他們之前說聲:對不起。”透過“Forget to…to…to…”(忘記了……忘記了……)的排比手法來放緩整首詩的敘事節奏,從而更好地營造凄苦無依的氣氛。第二段引文,“您心里明白:——這些孩子沒有母親。家里沒有母親!——父親在很遠的地方!……孩子清早起床,興高采烈地起床,動動嘴唇,揉揉眼睛……”對孩子滿懷期待起床的重復回環,凸顯出與母親去世之間的更強烈的張力,震攝人心地彰顯主題。
回看《雨巷》,摹仿特征無比明顯。“撐著油紙傘,獨自/彷徨在悠長、悠長/又寂寥的雨巷”“她靜默地遠了、遠了”和“她彷徨在這寂寥的雨巷/撐著油紙傘/像我一樣/像我一樣地/默默彳亍著”利用“悠長”“遠了”“像我一樣”的重復,拉長了詩歌的節奏,放大了詩中迷茫綿長的情緒和理想夭折的失措之感。“她飄過/像夢一般地/像夢一般地凄婉迷茫”則借“像夢一般地”刻意停頓,增強表現力。“她是有/丁香一樣的顏色/丁香一樣的芬芳/丁香一樣的憂愁”連著三個“丁香一樣的”排比,亦是象征主義常用的手法。象征主義手法在戴望舒的早期詩作中同樣有所表現,如《秋蠅》:“木葉的紅色/木葉的黃色/木葉的土灰色/窗外的下午!”《夜》:“溫柔的是縊死在你的發絲上,它是那么長,那么細,那么香。”正是這種特有的技巧,使戴詩擁有一種遠比李金發、聞一多、徐志摩等現代詩人更富有音樂旋律感的音樂節奏的美。
二、從粗糙嫁接到本土化改造的變調
李金發詩的獨特之處是波詭云譎的意象與晦澀艱深的詩風,其受批判之處亦為此,他的詩風本質上是粗糙嫁接西方文脈的結果。如前文引用的《夜之歌》《棄婦》以及《時之表現》的開篇,“風與雨的海洋里,野鹿死在我心里。看,秋夢展翼去了,空存這委靡之魂。”可見到,詩歌單句拆開觀之皆各有巧思,然合于一體卻不知為何物。“野鹿”“秋夢”“魂”等意象本身別具一格,相互卻不可勾連,似有強力混揉而成,令讀者有不知是搭配成謬還是詩人刻意抹去連接橋梁的恍然之感。朱自清評價說:“仿佛大大小小紅紅綠綠一串珠子,他卻藏起那串兒,你得自己穿著瞧。”的確反映了李金發在吸收外來影響時是比較粗疏的。粗疏的另一方面反映在句法歐化上,朱自清認為“(他的詩)句法過分歐化,教人像讀著翻譯”。如《溫暖》:“并燦爛在園里的花枝上。……我以冒昧的指尖,感到你肌膚的暖氣。”《愛憎》:“我保住的祖先之故宮既頹廢,心頭的愛憎之情消磨大半”,“燦爛在園里的花枝上”是“在園里的花枝上燦爛”的歐化表達,“冒昧的指尖”“保住的祖先之故宮既頹廢”等令人不解,是為濫用抽象動詞。無怪乎唐弢以“金發文字頗多疵病,其詩亦然”之語評之。
戴望舒詩則不是如此。戴望舒出身良好,受到優良的文化熏陶,有很高的傳統古典文化修養。戴詩受法國象征派影響僅反映了其詩歌一個方面而已,另外一個重要的面向是詩風受到中國古典詩詞的良好熏陶,在此基礎上,他實現了中西詩風的結合,完成了對象征主義手法的本土化改造。以《雨巷》為例,詩的核心意象,撐著油紙傘希望碰見像丁香一樣結著愁怨的姑娘,便借鑒了五代詩人李璟的名詩《攤破浣溪沙·手卷真珠上玉鉤》。“青鳥不傳云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信使不曾捎來遠方行人的音訊,雨中的丁香無人欣賞,喚起人凝轉千結的憂愁,這是古詩中常表達的凄苦的心境。中國詩人非常善于傳達愁緒,那種雨打窗頭心頭雨的淅瀝愁苦往往在詩人生花妙筆下書寫得淋漓盡致。《雨巷》顯然受到李璟的影響,轉而用現代漢語,塑造全新的意境生動淋漓地表現出來。《雨巷》及其他類似詩篇的成功無不得益于對中國傳統詩歌藝術經驗的借鑒以及對中西兩大源頭的融會,這同時反映了戴望舒具有李金發所匱乏的良好的文化修養和對詩靈活而悅動的把握。
三、結語
音樂美的律動與中國傳統詩篇的精致典雅構筑了戴詩的光輝流長。戴望舒對法國自然主義藝術手法的深入運用及本土化改造把現代派詩歌的藝術推向了新的階段,同時標志著新詩創作達到了新的水平,其間的變化意味著自李金發到戴望舒,現代派詩歌象征手法經過了簡單到復雜、粗糙到細膩的變調。
參考文獻:
[1]戴望舒.戴望舒作品集[M].北京:現代出版社,2016:8.
[2]張賢明.百年新詩代表作現代卷[M].北京:現代出版社,2017:3.
[3]張新泉.李金發詩集[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7:1.
[4]聞一多.聞一多作品集[M].北京:現代出版社,2016:8.
責任編輯:楊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