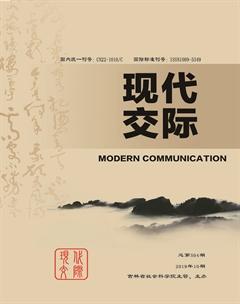時代的鼓手
李靜
摘要:田間由胡風力薦,最初作為七月派的代表詩人在詩壇嶄露頭角。隨后田間又擂響了戰爭之鼓,其詩歌的抗戰書寫曾振奮了一個時代。他是一個受過崇高贊譽與尊敬的詩人,也同樣一生飽受爭議。在戰爭硝煙散去的時代,如何客觀公正地鑒賞田間的詩歌,重估其文學史價值,顯然非常具有研究意義。
關鍵詞:街頭詩 鼓手 抗日救亡 敘事詩
中圖分類號:I2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9)10-0106-02
田間是七月詩派的代表性詩人,在胡風的支持下,他的作品開始被大眾熟知。他在抗戰時期發起的街頭詩運動曾經鼓舞很多人參加到爭取民族獨立的戰爭中去,在不同時期受到的批評和責難也不絕于耳。戰爭年代已經遠去,對田間作品的鑒賞應該回到歷史現場,在抗戰的時代背景下去解讀他的思想與創作動機,才能保持客觀。本文試回顧田間在抗戰時期的創作、詩藝觀,分析其抗戰背景下的詩歌創作實績,進而重估田間的文學史價值。
一、田間抗戰時期的詩歌創作
田間從小飽讀詩書,尤其喜愛《詩經》,接觸了白話新詩以后就走上了詩歌創作的道路。在抗戰爆發的前夕,他在鮮血和殺戮中燃起了愛國的熱情,在上海讀書時和同學蔣弼、周而復等加入了“左聯”。他的處女作是《海之歌》,是他不愿做亡國奴的呼喊。胡風最早發現了詩風淳樸又真摯的田間,傾情推薦他的作品,甚至給他的早期詩集做序。愛國主義詩作招致了禍端,國民黨開始搜捕他。1937年他去日本避禍,在日本又吸收了西方詩歌的藝術成果,尤其是馬雅可夫斯基的詩體形式和革命精神幾乎成為田間詩歌創作的靈感源泉。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田間和眾多文藝愛好者都從各地輾轉來到了抗日前線。他是西北戰地服務團的一員,隨后到了延安,創作了《給戰斗者》以及《中國底春天在號召著全人類》《自由,向我們來了》。他吸收了馬雅可夫斯基詩作中的生命激情,創作有鼓點節奏的短詩。聞一多盛贊他是“時代的鼓手”,認為“簡短而堅實的句子,就是一聲聲的‘鼓點,單調,但是響亮而沉重,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1]田間創作的詩歌節奏歡快而鏗鏘有力,農民和戰士備受鼓舞,對抗戰起到十分有利的宣傳作用。他放棄了知識分子的驕傲,懷著壯志豪情加入抗日的大時代,讓自己的詩歌成為拯救家國的武器。隨著《給戰斗者》的廣泛傳播,大眾點燃了愛國的激情,在心中擂動民族戰爭的鑼鼓。這部詩集的影響力之大,實屬和平年代的人們難以想象的。
抗戰初期,田間發起了一場“街頭詩運動”,他主張把詩寫在傳單上貼在大街小巷,鼓舞民眾的抗戰士氣。他把民族危難中的痛苦與悲憤寫在紙上,鼓舞著滿身彈傷和刀痕的榮譽戰士繼續戰斗。他的詩歌恰似在血雨腥風中繼續用民族尊嚴擂動的戰鼓,召喚著中華民族的萬丈革命豪情,鞏固了中華民族堅持長期抗戰的信念。
1938年以后,田間開始參加不同的政治工作。在堅持寫街頭詩之余,開始撰寫敘事詩《村中紀事》《名將錄》等。長篇敘事詩的佳作較多,例如《鐵的子弟兵》《趕車傳》《親愛的土地》《戎冠秀》。他不但頌揚民族英雄,也為抗戰中的人民群眾立傳。抗戰后期的作品更加樸實,更加生活化,《抗戰詩抄》與詩作《短歌》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品。
田間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鼓點詩作和敘事詩都符合那個年代的抗戰任務。作為宣傳最有利的文體形式,它的光照亮了整個民族。雖然當革命戰爭背景淡去,這些詩作在燦爛的文學星河里似乎失去了色彩,但是對文學作品的鑒賞,不能脫離它產生的時代,只有回到歷史現場,才能還詩人以公正。幸運的是,學術界仍然沒有遺忘田間,他的《給戰斗者》成為了優秀圖書,甚至被學者贊譽為“一塊被重新擦亮的文學豐碑”。
二、田間抗戰時期的詩歌主張
田間在不同時期都不間斷地表達了其獨特的詩藝觀。抗戰時期的詩歌作品是他一生堅持的詩藝觀的理論實踐。
首先,他一直認為詩人就應該是戰士。他不是居功自傲的人,沒有把自己當作民族英雄。他來自于底層人民,自小浸染農村的淳樸民風,親眼目睹農民在戰爭中顛沛流離難以逃脫血腥與殺戮的命運。他的詩作為農民而作,也為加入抗戰的廣大民眾而作。他認為詩人要像戰士一樣赴湯蹈火,在所不惜,應該用盡全力帶動人民走向民族戰爭的疆場。他把詩歌當作刺向敵人心臟的戰刀和指向敵人隊伍的槍炮。
其次,主張詩歌抒發情感,他要為革命發出振奮人心的吶喊。田間作為一個底層民眾,從小深切感受著人民被踐踏被蹂躪的切膚之痛,走進現實主義的抗戰詩歌陣營,是民族責任心使然,是戰爭時代特性使然。他認為作為一個戰爭年代詩人的使命就是“使詩的精神和中國民族的精神,使詩的精神和戰斗的精神很好地結合起來”。[2]無論遭受多少質疑,他仍點燃自己的生命余暉,只為了那一腔的民族家國情懷。
再次,他認為詩歌不能脫離生活,詩歌是創造的,生活是詩歌創作的根基。生活雖然不會隨時給詩人創作的靈感,但是生活經歷經過沉淀必然讓詩人寫出凝練的詩句。他認為詩歌不僅要有真理,也要有形象,主張詩歌要營造意境,達到雅俗共賞的境界,這與其古典文學積累有關。他沒有把自己當作社會精英,而是始終與普羅大眾站在一起,學習民歌,深入民間體驗民情。他倡導詩歌大眾化,踐行當時的文藝界指導思想,于是詩作既面向大眾,又有古典的意境。
三、田間抗戰時期的詩歌創作特點
田間一直是七月派詩人的中堅力量,詩作風格隨著他的抗戰經歷的變化而不斷豐富發展。借鑒了新月派等流派的創作手法,學習了蔣光慈的紅色鼓動詩,他也與詩歌成就很高的艾青互相學習。除馬雅可夫斯基之外,田間也學習歌德與普希金等眾多西方詩人的作品。他兼收并蓄,自成一派,創立了“田間體”。
其一,田間是現實主義詩人,繼承五四以來為人生的文學主張。他倡導“街頭詩運動”,讓詩歌走向大眾,不怕危險,到戰爭紛亂的世間角落體察戰火燃燒下的世態人情。他筆下關于士兵戰士身體與心靈受創傷的題材很多,他描述著被日本兵掃蕩過荒無人煙的村莊,也刻畫著四處逃竄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難民,充滿了現實主義色彩。抗戰中后期,田間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下基層體察民間疾苦,寫了許多敘事詩與政治抒情詩。他吸取民歌藝術,為戰爭中的真實人物寫下千古的贊歌。田間采用中華民族傳統的古典創作藝術,用賦比興的手法,將現實主義的創作理念貫穿始終。
其二,田間的詩歌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田間生長在充滿童趣與閑適色彩的鄉間,自小有深厚的古典文化積淀,屬于詩人的浪漫氣質也在田間身上隨處可見。郭沫若早期的浪漫主義詩歌實驗就以愛國主義和浪漫主義為特色,田間詩歌奔放的情感,熱烈的抒情都師承郭沫若。他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是一個革命的浪漫主義文藝工作者,他的作品從來不乏新奇的想象力和奔騰的情感,不乏獨特的意象。比如,他的代表作《給戰斗者》:“在詩篇上/戰士的墳墓/比奴隸的國家,/要溫暖,/要明亮。”[3]這首詩的比喻是極端的對比,也足見以戰士自居的詩人要誓死捍衛祖國的決心。他的政治抒情詩有紅色的浪漫主義基調,長篇敘事詩也不乏浪漫主義色彩。《趕車傳》的抒情意味濃重,“趕車”本身的象征色彩也十分明顯。石不爛就是傳奇式英雄,戰火之中,無所畏懼,與趙云單騎救主的故事不無二致,刀槍之前面不改色;史明偉就義以后,變作一只“金鳥”;金娃在戰火中猶如“火人”或“飛雷”:故事框架就借鑒了神話演義。
其三,詩歌體式別具一格。他最早接受了胡適的白話新詩理論,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探索,最具特色的就是他創作的鼓點體詩歌,一字或兩字也能成行,簡潔有力,增強了詩歌的節奏,提高了宣傳功效。詩歌在戰爭年代像敲響的戰鼓一樣傳遍抗戰的前線和敵后根據地,《給戰斗者》等詩作無可非議地屬于抗戰書寫的杰作,鼓點體詩作因而在抗戰時期得以揚名。田間提倡的“街頭詩運動”也創立了街頭詩和傳單詩等相關詩體,與哲理詩和明信片詩有良好的承繼關系。因為多抗戰相關的口號,所以政治屬性明顯。此類詩形式自由,短小簡潔,適合大眾學習,宣傳效果明顯,仍然不失詩歌的藝術特色。延安地區因此效仿的群眾詩歌此起彼伏,街頭詩創作進入高潮,抗戰詩歌的整體創作都被帶動起來了。田間抗戰中后期創作的長篇敘事詩,也為該詩體的長足發展做出了跨越性的貢獻。敘事詩吸收了報告詩、史詩等詩體的形式,文藝界敘事詩創作也曾在他的影響下出現了井噴式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改寫的《趕車傳》甚至是敘事詩里最長的杰作,其敘事詩的藝術手法豐富多樣,創作數量屬于歷史之最。田間向民歌學習創作出來的民歌體也是大眾化文藝主張的創作成果,《戎冠秀》就是新詩格律的完美實驗。田間不僅繼承古典詩歌勻稱的節律、整齊的句式,還于整齊中追求變化,在變化中堅持詩意的統一。因此,他的詩歌也推動了詩歌格律化的進步。
四、結語
抗戰時期的詩歌以民歌體敘事詩和政治抒情詩為主,詩歌整體風格以生動形象、簡潔有力、政治宣傳性明顯為特征,創作成績較為顯著的還有艾青和臧克家,他們三人各有所長,抗戰書寫都在民族大義激蕩的年代留下了歷史的回響。田間的詩歌代表著知識分子在民族危難的時刻覺醒的民族意識,塑造了一個個啟蒙大眾的抒情主人公,在抗戰時期備受追捧。他被稱為“第一個拋棄了知識分子底靈魂的戰爭詩人和民眾詩人”。[4]他的《擬一個詩人的志愿書》高喊“我寧肯犧牲自己,不犧牲人民與詩歌”,他的《給戰斗者》告誡中華兒女“這古老的民族/不能/屈辱地活著/也不能/屈辱地死去”。鼓點般的詩歌像閃電一般劃過戰時的天空,每一首詩都是抗日救亡的民族魂的體現。詩人像一個執劍前行的啟蒙者,把政論性的話語幻化成鼓點式的戰斗之歌,感染著每一個沉睡的獅子,發出猛獅的怒吼。一個民族都將滅亡的時刻,藝術個性服務于民族大我是時代的必然選擇。政治屬性占據主導地位的作品在歷史激流奮進的歷程中,飽受爭議,回到硝煙彌漫的歷史現場,田間的抗戰書寫不可否認地曾經像那啼血的杜鵑花一樣嬌艷,渲染了戰火中盛開的民族之花。
參考文獻:
[1]聞一多.聞一多全集(第三卷)[M].天津:開明書店,1948.
[2]白崇義.擂鼓詩人田間[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3]田間.給戰斗者[J].七月,1938.
[4]張傳敏.七月派文獻匯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責任編輯:孫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