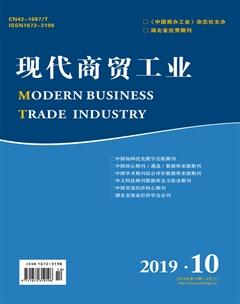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超大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研究
李晗
摘要:黨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對社會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上海結合自身特點,針對關鍵問題,開展超大城市的基層社會治理探索。通過實地調查,對上海創新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成效進行評估,揭示上海創新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問題,提出實現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超大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共建共治共享;超大城市;基層社會治理
中圖分類號:D9文獻標識碼: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9.10.063
1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這是適應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對社會治理提出的新要求。超大城市的經濟社會加快轉型發展,國內和國際移民大量涌入,人口規模快速擴大,城市居民結構多元化,社會階層復雜化,利益主體訴求多樣化,對以居住地為核心的社會治理模式提出了挑戰。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體系需要更具時代性、前瞻性的創新發展。上海一直在積極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點和規律的社會治理新路”2015年,上海針對自身發展的關鍵問題,在市委1號課題調研成果的基礎上出臺了“1+6 文件”。幾年來“1+6”改革已初見成效,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課題組在松江區九里亭街道亭誼居委會、泗涇鎮新凱社區、普陀區桃浦鎮安居錦竹苑居委會和閘北區彭浦新村街道三泉路424弄居委會開展實地調查,評估上海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成效,揭示上海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問題,提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超大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對策建議。
2上海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成效
2.1黨引領基層社會治理的能力提升
街道和鎮設置街道(鎮)、社區、居委會分級黨建工作網絡,將居民區黨建作為區域化黨建的重點,推動黨建資源下沉。同時,通過黨建引領群團建設,整合群團組織資源,積極發揮群團組織在勞動就業、教育培訓、幫困救助等領域的作用。泗涇鎮搭建黨建服務平臺,采用搭建黨建服務站和網絡服務平臺等形式,吸引在職黨員參與社區治理,為群眾提供心理疏導、權益維護、幫困助弱等服務,形成線上線下互動促進、有機融合的良好格局。另外,各街鎮通過完善區域化黨建聯動協調機制、區域化黨建考核評價機制、搭建黨建平臺,推進區域黨建、行業黨建,提升黨組織領導居民區自治的能力。
2.2居委會協調社區力量的能力進一步增強
上海部分居委會通過創新社區工作機制,進一步增強了社區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的有效性。同時,居委會加強了規范管理,增加了與社區力量的溝通與合作,提升了自治能力。一些居委會采用制定社區自治公約、眾籌自治金、培育樓組骨干力量、管理居民區活動室等多種方式,動員居民參與社區自治,吸引更多年輕人和白領參加,使居民深度參與社區自治。部分居委會建立了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公司的互動機制,形成“匯總社區問題-討論解決方案-居委會協調社區資源”的社區問題解決流程,居委會協調社區力量的能力進一步增強。
2.3社區工作者隊伍建設取得進展
首先,人員范疇規范化,實行額度管理。上海各街鎮的基層社區將就業年齡段全日制工作人員、街鎮所屬“中心”的聘用人員、街鎮聘用的社區專職工作人員納入社區工作者范圍。根據社區面積、人口數量、管理幅度、居民區規模和工作需要核定需配備的社區工作者人數。同時,實施總量調控,對不同類別的社區工作者分類確定,強化額度管理。其次,選任招聘流程規范化。居民區采用選任納入、招聘納入的方式配備社區工作者,除選任人員外,其他社區工作者按照“公開、平等、競爭、擇優”原則,面向社會公開招聘。再次,薪酬待遇體系優化。社區工作者建立崗位等級體系,根據工作年限和工作能力實現等級調整,逐步完善社區工作者的待遇結構。最后,社區工作者的日常管理趨于強化。基層社區建立健全社區工作者的培訓、管理、考核和激勵機制,強化了社區工作者隊伍的日常管理。
2.4社區多元共治格局初步形成
上海各街鎮的基層社區在街道黨工委的領導下,搭建社區共治平臺,將駐區單位、社會組織、居民納入其中,引導他們積極參與社區治理。居民及各類社會組織積極發揮作用,實現社區資源的整合和共享,解決了社區就業、養老托幼、濟貧助殘、公共安全、醫療保健、環境綠化等基本的社區問題,初步形成了社區多元共治格局。一些街鎮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分別對治安聯防、市容協管、社團和民非組織實行工作業務服務外包,鼓勵社會組織走進社區,為居民提供多樣化、精細化的服務。基層社區形成了社區黨組織領導,以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公司、社區民警、條線部門、樓組長、志愿者、自治團組、居民代表、黨員代表、群團組織、駐區單位和社會組織等為參與主體的治理結構。
3上海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問題
3.1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的廣度與深度有限
居民參與的積極性調動不夠,參與社區治理的廣度與深度仍然有限,主要表現在:第一,仍以老年人參與為主,總體參與比例較低。由于老年人空閑時間較多,樂于參與社區活動,因此居民區的樓組長、志愿者及文體活動組織仍以老年人為主,年輕人較少參與。第二,參與的活動范圍有所擴展,但仍以政治參與和文體活動為主。由于老人的文化程度有限,沒有能力參與信息化、挑戰性的社區活動,因此他們主要以文體活動參與為主。第三,社區活動內容缺乏吸引力,與居民需求較遠,形式單一。
3.2居委會的行政負擔沒有明顯減少
首先,行政負擔減負不明顯。居民區尚未建立行政工作事項準入機制,街鎮也未形成行政事項清單,仍將大量行政性事務下達給居委會。居委會承擔的社區事務的大多數仍來自街鎮交辦的行政性事務,居委會的行政負擔沒有明顯減少。其次,工作難度增加。要求居委會工作面向居民需求,而社區復雜的人口結構和多樣的居民訴求增加了居委會收集和分析居民需求的難度。再次,職責范圍擴大,居委會不僅要承接街道下達的任務,還要引導社區主體參與自治,協調多元主體間的關系,這些都使居委會的任務更加繁重。
3.3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區治理的作用有限
首先,物業公司收費難、服務差、監督主體缺位。居委會對物業公司的監督有限,物業公司以配合為主,較少主動協助居委會。其次,業主拒繳物業費和物業公司服務不到位形成惡性循環,這在物業征信系統建成前難以解決。再次,業委會和居委會之間的矛盾有時難以和解,影響了社區事務的正常管理。最后,專業社區社會組織參與社區治理有限。專業社區社會組織的總量很少。盡管上海各街鎮有備案的社會組織,但是實際發揮作用的專業社區社會組織總量還比較少。而且,專業社區社會組織的服務能力有限,現階段無法與居委會實現社區服務主體的轉移和對接,這也是居委會減負無法真正實現的原因之一。
4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超大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創新路徑
4.1強化黨組織的整合和協調能力
積極整合單位、區域內的黨建資源,按照“便于資源共享、便于活動開展、便于管理服務”和“行業相近、地域相鄰”的原則,系統地統籌謀劃基層黨建工作,變點狀推進為成片推進。在制度支撐上,構建一套完備的激勵約束機制,將黨建責任追究機制和干部考核體系有機結合。責任追究機制要在黨委書記為第一責任人的架構下,細分責任內容,建立各級黨建工作的“責任清單”,實現基層黨建工作責任制由“虛”到“實”、單項考核向整體評估轉變。干部考核體系要以政治忠誠、敢于擔當為內容,系統考查黨員干部直接聯系群眾、服務群眾以及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水平。增強黨員在社區自治中的作用,引導黨員發揮職業特長開展志愿服務。
4.2提高居委會的動員和組織能力
超大城市的社區居民結構趨于多元,利益主體訴求復雜多樣。因此,要加強居委會隊伍的培訓,尤其是要提升應對復雜社區治理的能力,以及互聯網背景下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同時,要進一步完善居委會隊伍的優化機制和職業發展機制,改變居委會隊伍總體力量不強、后繼乏人的狀況。建立居委會工作督導制度,對各居委會工作落實情況進行綜合督導評估,幫助居委會盡快提升自治能力。
4.3拓寬社會組織參與社區自治的路徑
第一,加大政府職能轉移力度,真正釋放社會組織參與社區自治的空間,向社會組織循序漸進地開放政府資源,形成充分的市場競爭。第二,完善政府購買制度,規范社區項目招投標流程;提高政府技術官員的合同管理能力,提高與社會組織的談判水平;強化政府購買服務項目的監督審計,強化對第三方評估機構的約束和監督,完善政府購買服務的第三方評估機制。第三,引入專業社會組織,以大型居住區居民的需求和利益為導向開展社區服務。繼續增加政府對社會組織發展的支持,不僅要支持社會組織的多元化發展,還要注意鼓勵社會組織之間的力量整合,支持社會組織跨區發展。第四,吸納居民作為社會組織的理事會成員或志愿者,提升居民對社會組織的認同度。
4.4優化社區自治平臺
在社區黨委的領導下,居委會引導物業公司、社區居民和其他社會組織溝通、合作與協商,發揮社區動員和整合功能,動員社區居民參與社區自治,構建社區共同體。政府賦予基層自治組織權力,并且推動社會主體向自我組織、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管理等自主治理發展。同時,政府履行引導監督社會組織的職責。強化社區委員會的議事、協商、評議和監督職能,暢通社區委員會的事權、處置權和決策權。
4.5建立協商機制和自下而上的整合機制
居委會增加與居民、社會組織、業委會等社區自治主體的溝通與合作,在政府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公眾監督、法律保障的原則下,建立健全基層社區的各種利益協調機制、權益保障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促進黨組織、政府、社區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居民的協商互動,發揮化解社會矛盾、調節社會關系的重要作用,保障基層社會的有序運行。同時,基層社區要將居民需求轉化為社區項目,通過吸引居民參與社區項目,建立自下而上的社區整合機制。
4.6培育社區公共性,吸引居民深度參與社區自治
將社區需求項目化,動員居民參與自治項目,構建居民與社區之間的聯結點。居委會引導居民以組織化的形式參與社區自治,鼓勵居民參與志愿者組織或文體組織,增加居民之間的互惠和信任,構建居民與居民之間的聯結點。通過分類參與的方式鼓勵各類居民參與社區自治,如以文體活動吸引退休居民參與,以微信等新媒體手段吸引在職居民參與等。在基層社區建立自下而上的自治議題與自治項目形成機制,開展居民需求導向的社區活動,通過這些方式吸引居民深度參與社區自治。
參考文獻
[1]蓋伊.政府未來的治理模式[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
[2]李和中.城市社區治理模式的現實選擇[M].北京:中國行政管理,2008.
[3]李友梅.關于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新探索[J].清華社會學評論,2017,(01):190-195.
[4]李友梅.我國特大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分析[J].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6,20(02):5-12.
[5]田毅鵬,薛文龍.“后單位社會”基層社會治理及運行機制研究[J].學術研究,2015,(02):4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