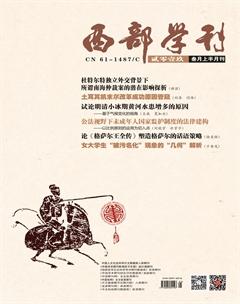唐《元包經傳》考辨
梁明玉
摘要:《元包經傳》在經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該書由北周衛元嵩撰,唐玄宗時國子司業蘇源明作傳,四門助教李江作注,后經宋人韋漢卿釋音得以流傳。其書體例從坤卦開始,傳文、注文多關涉治亂之理,以“陳理亂于邦家”“冀裨帝業”為目的,《元包經傳》的傳文和注文中體現出傳注者的德政思想,對此書進行深入研究,將對現代文化建設深有助益。
關鍵詞:《元包經傳》;德政思想;價值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CN61-1487-(2019)05-0098-03
盛唐之世實行儒釋道并舉的文化政策,統治者重視經籍治世的功用,社會上出現了濃厚的解經、注經風潮。由于戰亂等原因,當時絕大多數著作現已不可考。《元包經傳》一書在經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目前學界尚不夠重視,還未見專文論述。本文對此書的作者、思想內容、價值、包含的德政思想等問題進行考辨。
一、《元包經傳》的基本情況及真偽問題
《元包經傳》最早見于唐韓愈《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五:“?.,下注《元包經》屵?.。”而《隋書·經籍志》? 《舊唐書·經籍志》等書均未見記載。在宋代有關《元包經傳》的記載漸多,《新唐書·藝文志》易類著錄:“衛元嵩《元包》十卷,蘇源明傳,李江注。”慶歷元年(1041年)編訂的《崇文總目》載:“《元包》十卷,衛元嵩撰,元嵩唐人。武功蘇原明傳,趙郡李江注。”南宋年間編訂的《直齋書錄解題》載:“《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秘書少監武功蘇源明傳,四門助教趙郡李江注。”再如《北溪大全集》《義海》《易裨傳》《易通變》等書亦多有記載。綜上可考知,《元包經傳》撰者當為北周衛元嵩,唐蘇源明作傳,李江作注。《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等書將衛元嵩認為唐人當誤。
衛元嵩在《周書》卷四七有傳:“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將來之事,蓋江左寶志之流。天和中,著詩預論周、隋廢興及皇家受命,并有征驗。性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史失其事,故不為傳。”另《蜀中廣記》卷九一:“先生名元嵩,益州成都人,少不事家產,潛心至道,明陰陽歷算。時人鮮知之。獻策后周,賜爵持節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可概知衛元嵩事跡。
蘇源明在《新唐書》卷二〇二有傳:“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召源明為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偽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李江詳細信息不詳,僅據《直齋書錄解題》《崇文總目》等書可知,其為趙郡人,曾任國子監四門助教,余不詳。可見此書應為安史之亂前完成,因戰亂中蘇源明等人應無暇做此工作,安史之亂后蘇源明就被肅宗任命為考功郎中、知制誥了。
將此書傳播開來發揮重要作用的是楊楫、張昇和楊繪三人。據《蜀中廣記》卷九一載:“知什邡縣事楊楫,序云:大觀庚寅夏六月,余被命來宰茲邑,蒞官之三日,恭謁衛先生祠。顧瞻廟貌,覽古石刻,先生實髙士也。既而,邑之前進士張昇景初,攜《元包》見遺,曰是經先生所作也,自后周歷隋、唐,迄今五百余載,世莫得聞。頃因楊公元素內翰傳秘閣本,俾鏤板以遺諸同志。”《元包》舊序、《元包經傳提要》《雙桂堂稿》續稿卷二《什邡重刻易元包經傳序》與此記相同。據《蜀中廣記》卷九一所引紹興三十一年南陽張洸跋文:“《元包》舊序所稱景初,即洸之先君子也,家藏此書。”可知,楊楫在宋徽宗大觀庚寅四年(1110年)六月知什邡縣事,其余事跡不可考,他在知什邡縣事時,當時的什邡進士張昇向其介紹此書。而此書宋代時藏諸秘府,后為張昇家藏所有,其來源于“楊元素內翰傳秘翰本”。
楊繪,字元素,為北宋人,《宋史》有傳,素有文名。據《宋史》卷三二二:“楊繪,字元素,綿竹人。少而奇警,讀書五行俱下,名聞西州。進士上第,通判荊南。”《文獻通考》卷二三六:“《楊元素集》四十卷。晁氏曰: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幼警敏,讀書一過輒誦,至老不忘。皇祐初,擢進士第二人,累擢翰林學士。沈存中為三司使,暴其所薦王永年事,因貶官。終于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嘗居無為山,號無為子。為文立就。”另據南宋 《厚齋易學》卷一六《易輯傳》十二載:“楊元素曰:六二從初六,五從上,俱失中爻之常。”《經義考》卷三十載:“楊元素侍讀亦謂:圣人設卦,觀象系辭焉,而明吉兇。又曰:系辭焉,所以告也。”可見楊繪曾為翰林學士,且精通易學。所以,他注意搜集此書也在情理之中。
此書內容據《易學象數論》卷四載:“《元包》祖京氏以為書,分純卦為八宮,一世、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遊魂、歸魂為鬼易。但更其次序,先陰而后陽,則《歸藏》之旨也。”《四庫全書總目》卷一〇八子部一八載“體例近《太玄》,序次則用《歸藏》,首坤而繼以乾、兌、艮、離、坎、巽、震卦,凡七變,合本卦共成八八六十四,自系以辭。”《經義考》卷二七〇《衛氏元包》條:“其書以八卦為八篇首,而“一世”至“歸魂”各附其下。先坤,次乾,次兌、艮、離、坎、巽、震。坤曰太陰,乾曰太陽,余六子有孟、仲、少之目,每卦之下,各為數語,用意僻怪,文意險澀,不可深曉也”。今存《元包經傳》五卷附《元包數總義》二卷,已非唐時十卷本,“其或并、或佚,蓋不可考”。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將《元包經傳注》歸入子部術數類,應因為卷五的《運蓍第九》中有大量的術數類的內容。如“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下注“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各有合也。”“陽之策一十有二”下注“象乾,三爻,震、坎、艮各一爻,巽、離、兌各二爻,共一十有二也。”“陰之策二十有四”下注“象坤,七爻,巽、離、兌各二爻,震、坎、艮各四爻,共二十有四也”。該書在《新唐書·藝文志》中則被歸入經易類,《六家詩名物疏》“引用書目”中也歸入“《周易》”。考全書,應歸入經易類為佳。此書現有明刻本《元包經傳》五卷本存世。
此書自宋代流傳后,世人對該書評價褒貶不一。有些易學著作對此書評價不高,如《易學象數論》卷四評價“其書因卦兩體,詁以僻字,義實庸淺,何所用蓍,而好事者為之張皇也。”《四庫全書總目》卷一〇八認為:“以辭文多詰屈,又好用假字,難以猝讀,及?其傳、注、音釋,乃別無奧義,以艱深而文淺,易不過效《太玄》之顰。”只是因“徒以流傳既久”,所以才“姑錄存之”。主要批評此書存在“詁以僻字”和“義實庸淺”兩個方面的問題。當然,有些著作對此書評價較高,如宋人章如愚在《山堂考索》別集卷三《經籍門》中對此書評價:“元包有卦無爻,何義也?……后學崢嶸,亦未可以淺議《元包》云。”再如《蜀中廣記》卷九一引知漢州什邡縣事楊楫語:“包之為書,其學《易》之至者歟!辭簡義奧,殆未可以象數盡也。”對此書評價極高。還有《易像鈔》卷一四:“焦贛《易林》、衛元嵩《元包》,敢于棄置文王彖辭,而自支離,其說不勝杜撰,不勝畫蛇添足,即坐舞文之誅,何過?”也認為此書有一定的研究價值。
針對此書“五百余年世莫得聞”的情況,清人王世貞認為此書很可能是宋人偽作,《經義考》卷二七〇:“王世貞曰:《元包》一書,楊元素由秘翰傳本鏤行,而張昇以授楊楫者也。予疑此即元素撰,或張昇撰,而讬者也。經與傳、注若出一人手。”王世貞在《讀書后》卷五《讀元命苞》中,除了此書“五百余年世莫得聞”的理由外,進一步闡述了另外三條理由,首先,“卦下每作重疊文難字,而考之諸字書,則易曉,其旨甚淺,而于理不甚悖。”其次,“傳、注若出一人手。”再次,“凡唐以前偽書,其理駁,而時有精旨。其文雜而古,其字奇而有不可識者,今皆反之。”針對王世貞的觀點,《四庫全書總目》卷一〇八則以為:“此書唐志、《崇文總目》并著錄,何以云“五百余年世莫得聞”?王世貞疑為依托似非無見。”對于王世貞所提出的“傳、注若出一人手”的問題,筆者認為主要是蘇源明和李江兩人同在國子監,雖是一人作傳,一人作注,但兩人可能合作完成,所以才會“傳、注若出一人手”。對于文字“其旨甚淺,而于理不甚悖”的問題,主要是此書經宋代人韋漢卿釋音的結果。
二、《元包經傳》中的德政思想
唐玄宗時任國子司業的蘇源明為《元包經》作傳的原因,現據李江《元包經傳》序:“秘書少監武功蘇源明,洗心澄思,為之修傳。解紛以釋之,索隱以明之,帝王之道昭然著見,有以見理亂之兆,有以見成敗之端”。另據《元包經傳》卷五說源第十載:“哲人觀象立言,垂范作則,將以究索厥理,匡贊皇極,推吉兇于卦象,陳理亂于邦家,廣論易道,冀裨帝業。”綜上觀之,蘇源明和李江為《元包經》作傳、注是出自“陳理亂于邦家”“冀裨帝業”的目的。
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尋找合適的載體就尤為重要。而在兩人看來,《元包經》就是這樣的作品。正如李江所說:“《包》之為書也,廣大含宏,三才悉備,言乎天道,有日月焉,有雷雨焉;言乎地道,有山澤焉,有水火焉;言乎之人道,有君臣焉,有父子焉。”此書不僅可以筮占吉兇,且“帝王之道,昭然著見”。就如《元包經傳·說源第十》載“蘇公修傳,終以明述作之意,用以論文質之理,又嘆時人不能洗心于精微之道,故云采世人之訂述,作之意訂審也。”蘇源明和李江二人,也有想通過此書來影響社會風氣的考慮。
首先,《元包經傳》的傳文中保存有大量的德政思想。如《復》卦傳:“昔王繇是審造化,察盈虛,以候爾天變,以虞爾人事。”又如《觀》卦傳:“以省爾萬方,以化爾兆民,稗風教大行,率土咸順。”即使是在涉及社會倫理關系時,后面還要補充相應的政治內容。如《革》卦傳:“娣媦欻,少女升也。姊姒勿勿,中女降也。澤之渴,內有火也。炎之戍,上有水也。昔王由是改正朔,易服色,發詔令,行恩惠,文物斯變,景命惟新。”《家人》卦傳:“娣姒侖兩婦,次也姑媦甡,二女聚也。尸而炎,主內灶也。爨爾薪,修中窺也。昔王由是修明德,發嚴令,命將帥,以整爾干戈;進文儒,以熙風化。外罔不從,內罔不鎣。”在《元包經傳》中此類現象不勝枚舉。
其次,《元包經傳》的注文也保存有大量的德政思想。如《頤》卦傳文為“內既勤政,外乃奠居”,注文為“頤之為言,養也。猶手之所執,足之所行。君人之道,豈宜有怠。故詩人綴匪懈之句,周公著無逸之篇,茍能使庶政凝,萬機不怠,何憂乎人之不定者哉。”再如《井》卦傳文為“機聯聯,關之轉也,組牽牽索之引也。深厥皿器入于深,躋厥淵水出于險也。昔王由是建乃刑法,施乃教令,行于中,流于外,罔不順,罔不通,上則之下從之。”注文為“古有言:身正,不令而行。上不正,雖令不從。由斯言,率從上也。何異,機關組索相率耶。亦猶沉器于井,汲水于泉,此先王取象于此。是以建刑法,施教令,行于中,流于外,無不通,故曰上則之下從之。”
為了讓讀者能夠更好地理解德政思想,在有些注文中靈活運用比較生動的例子來闡發自己對問題的看法。如《解》卦傳文為“無俾嚘咿,以傷爾和氣。”注文為“夫政理則人順,人順則氣和;政亂則人怨,人怨則氣逆。昔鄒陽被枉,五月降霜。老婦受誣,三年作旱。夫如是,欲求和氣之不傷,不可得也。君子痛之,故以為深戒。”在注文中用“鄒陽被枉”和“老婦受誣”的例子來進行通俗易懂的解釋。
有時,注文還用比喻或引經據典的方式,試圖讓讀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要表達的主要思想。如《昇》卦傳文為“布爾德教,加于丑類。”注文為“布爾德教,擬夫巽加于丑類,效夫坤也。且升之為言,進也。亦猶股運其腹,婦歸于姑,車之行,足之往,斯非昇者歟。先王法之,所以出制敷外,順人行化,此之謂布爾德教,加于丑類。經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蓋昇之道也。”就使比較艱澀的傳文使人理解起來變得較為通暢。再如《大過》卦傳文為“罔或胥唱,罔或胥和。”注文中為“《書》曰疑謀勿成,《語》曰利口之覆邦家,此所謂言之不正,事之不果也。”就分別引用了《尚書》和《論語》中的句子。
總之,《元包經傳》注、傳的出現,是盛唐學者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理想,有意識地對初唐時期出現的《周易正義》進行理論上的修復。此書完成后不久,由于安史之亂的發生,并沒有引起人們廣泛的關注。因緣巧合之下,《元包經傳》在宋明時期才得以流傳。對此書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將對我國現代文化建設深有助益。
參考文獻:
[1](北周)衛元嵩撰,(唐)蘇源明傳,(唐)李江注.元包經傳[M].北京:中華書局,1985.
[2](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3](宋)王堯臣等編次.崇文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