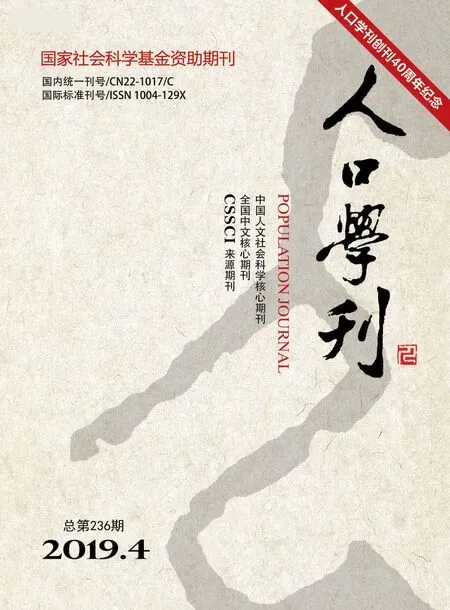農村成年子女外出務工對留守父母健康的影響研究
陳 璐,謝文婷
(南開大學 金融學院,天津 300350)
一、引言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按照聯合國的標準,我國在1999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目前已成為世界上人口老齡化進程最快的國家。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為2.4億,占總人口的17.3%。作為“健康中國”戰略目標的重要一環,如何實現“健康老齡”成為迫在眉睫的問題。與此同時,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農村地區大量勞動力外流。《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7)》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年底我國流動人口數達2.45億,占總人口的17.7%,其中農民工人口數量龐大,接近1.6億人。成年子女離開家鄉外出務工,由此也形成了數量龐大的留守農村的老年人群體。在我國農村地區,由于社區照護機構和專門老年護理機構發展滯后,老年父母的贍養和生活照料依然是由家庭來承擔,主要是由成年子女向父母提供經濟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而一旦子女選擇外出務工,留守在家的父母所獲得的各種照料和支持勢必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與此同時還可能增加留守父母照料孫輩的負擔,從而對其健康狀況產生影響。而留守父母的健康狀況不僅可能影響外出務工子女的社會融入,同時也是實現“健康中國”戰略中必須面對的問題,成為家庭、社會和政府廣泛關注的焦點。因此,本文旨在科學系統地評估成年子女外出務工對留守父母健康的影響,為今后我國相關老齡政策的制定提供經驗研究和決策依據。
本文采用“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1997-2015年的數據,采用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考察農村成年子女的外出務工對留守父母健康的影響。同時考慮在中國農村地區,“孝道”對不同性別的子女而言是不同的,因此我們進一步從性別差異角度檢驗對于留守父親或母親以及不同性別子女外出務工產生影響的異質性。
二、文獻綜述
對于成年子女外出務工對留守父母健康狀況的影響,雖然國內外學者進行了相關研究,但結論并不一致。絕大部分研究發現子女外出務工對留守父母無論是身體健康狀況還是心理健康狀況都有負面影響。Antman使用墨西哥2001年的截面數據,研究發現子女移民增大了父母身體和心理健康惡化的可能性。[1]Falkingham等人使用印度2011年的截面數據,通過二元Logit回歸模型研究發現家庭中有在國內或國際流動的子女,老人罹患高血壓、糖尿病和心臟病的概率更大。[2]Adhikari使用泰國2007年的截面數據,研究發現有在國內流動子女的老人更容易呈現較差的心理健康。[3]連玉君等采用CHNS數據,研究發現子女外出務工使得父母自評健康和生活滿意度雙雙下降。[4]杜鵬等利用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研究所2004年在安徽省壽縣、河北省承德縣和河南省浚縣等地調查的數據,研究發現農村子女外出務工后留守老人孤獨感加重。[5]江克忠、陳友華采用中國老年人健康長壽調查(簡稱CLHLS)2008年數據,發現空巢老人心理健康受到負面影響。[6]但是也有少部分研究發現子女外出務工對父母健康有積極影響。宋月萍采用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2009年的調查數據,研究發現外出務工子女對農村留守老人的精神支持能顯著增進老人的身體健康和精神健康水平。[7]Kuhn使用來自摩爾多瓦2011年的家庭調查數據,研究發現子女流動帶來的收入提高能為留守父母提供更好的飲食和更閑適的時間分配,這些積極作用能補償老年人與子女社會聯系減少造成的負面影響。[8]B?hme使用來自印度尼西亞1997至2000年的家庭生活調查數據,研究發現子女移民后家庭經濟收入的提高給父母健康帶來的積極影響超過了消極影響。[9]
由于子女外出務工的選擇不是隨機發生的,可能會受到可觀測和不可觀測諸多因素的影響,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必須克服這一問題帶來的影響,才能得到無偏的回歸結果。在現有文獻中,有的學者采用截面數據的Logit回歸方法或對數線性模型方法;[10-11]有的學者采用工具變量方法解決可能的內生性問題;[4][12]也有的學者采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和截面數據的傾向值匹配方法解決自選擇問題。[6][13]雖然以上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了外出務工的自主選擇問題,但是如果選擇外出務工的子女在不可觀測因素方面存在顯著差異,而且這種差異隨時間變化的趨勢不同,那么固定效應模型無法解決這種自選擇效應帶來的影響。此外,Gibson在對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以及工具變量方法的比較研究中,發現PSM方法對內生性問題的處理效果優于其他兩種方法。[14]
在以往的研究基礎上,本文的邊際貢獻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本文使用了CHNS七次縱向調查數據,從1997年問卷中第一次調查家庭外出務工人員情況,到2015年最新公布的數據,數據跨度19年,使研究結果更具說服力和代表性;第二,本文使用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來控制自選擇效應可能帶來的影響,由此得到的回歸結果也更加科學可靠;第三,本文進一步基于性別角度,分別對不同性別的留守父母以及不同性別的外出務工子女進行回歸分析,使研究更加深入。
三、數據和變量
1.數據
本文使用CHNS數據,該項調查具有全國性、大規模、多層次和開放性的特點。調查涵蓋全國12個省份(遼寧、黑龍江、江蘇、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西、貴州、北京、上海和重慶)約7 200個家庭,共約3萬人。這些省份遍布全國并且在經濟發展和公共資源等諸多特征上有所不同。因此,作為一項以家庭為基礎的縱向調查,CHNS數據具有全國代表性。[15]本文使用跨度19年的七輪調查數據(1997、2000、2004、2006、2009、2011和2015年),將樣本限定為農村地區,在剔除了未養育子女的個體和缺失值后,有效樣本量為23 830個,其中7 817個樣本為有子女外出務工的父母,占總樣本的33%。
2.變量
本文關注的被解釋變量是個體的健康水平,如何科學地度量健康自然成為關鍵問題。健康是個體的體格、精神與社會適應的整體狀態,是一個包含生理和心理指標的多維度概念(WHO,2015)。因此,本文選擇三個不同維度來測度留守父母的健康狀況。“過去四周是否患病”變量衡量短期身體健康,該變量來自問卷中受訪者對過去四周生理健康狀態的客觀判斷;“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變量(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IADL)”衡量長期身體健康狀況,由于對于IADL的調查僅針對55歲及以上人群,所以對于該變量的研究我們僅針對55歲以上受訪者樣本;“生活滿意度”衡量父母的心理健康狀況,由于CHNS對于生活滿意度的調查從2006年才開始,因此對于該變量的研究我們僅使用2006、2009和2011年的數據①由于2015年公布的CHNS數據中沒有“生活滿意度”指標的數據,所以對于該變量的回歸我們僅用了3年的數據。。
本文重點關注的解釋變量是“是否為留守父母”,CHNS問卷通過“該家庭成員是否住在家中?”詢問了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居住狀況,我們把選擇回答子女“外出打工”定義為至少有一個同戶成年子女外出務工的農村父母,即“留守父母”;而“非留守父母”則定義為沒有同戶子女外出務工的農村父母。在本研究中,留守父母占總樣本的33%。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于CHNS問卷中只對與父母同戶的外出務工子女做出上述提問。因此,我們的研究沒有涉及不與父母同住的子女外出務工對留守父母健康的影響。考慮在一般情況下,同戶成年子女為父母提供實質性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性支持,與父母的互動也最密切,因此在所有成年子女中,同戶成年子女的外出對父母的影響最大。
此外,本文控制了留守父母的個體特征和家庭特征。個體特征主要包括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是否參加勞動、是否擁有醫療保險(社會基本醫療保險和商業醫療保險)等。家庭人口構成包括家庭中是否有多個成年子女以及是否照料6歲及以下的兒童。家庭經濟狀況包括家庭資產指標(是否有摩托車、拖拉機、汽車等)①CHNS問卷中調查了家庭中某些耐用品的擁有情況,我們使用這些數據構建代表家庭財富的綜合指數,該指數基于家庭對普通耐用品的擁有狀況,而擁有這些耐用品代表著相對現代和舒適的生活。。研究變量的具體描述見表1。
四、計量方法
研究外出務工對留守父母健康產生的影響,一定要解決外出務工的自我選擇對于回歸結果可能產生的偏誤。本文采用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基本思想是從沒有子女外出務工的控制組中根據傾向得分選取某些個體,與有子女外出務工的處理組進行匹配,進而可以求得配對個體間的結果變量的差異,以實現對干預效應的無偏估計。[16-17]
以Treatment=1表示有子女外出務工,即處理組;Treatment=0表示沒有子女外出務工,即控制組。則平均處理效應可以表示為:

表1 變量說明與描述性統計

其中,Y1和Y0分別表示處理組和控制組的健康變量。
為了選取與處理組個體在可觀測的基本特征上一致的控制組個體,本文利用Logit模型獲得傾向得分,即Logit模型的預測值,模型如式(2):

其中,Ind表示留守父母的個體特征,包括受訪者年齡、性別、教育程度、是否參加勞動及是否有醫療保險等;HS表示家庭的人口構成,包括家庭內是否有多個成年子女以及是否照料6歲及以下的兒童;HE表示家庭的經濟狀況。

圖1 匹配后核密度函數圖
五、實證分析結果
1.樣本匹配質量
表2呈現了可觀測變量匹配前和匹配后在處理組和控制組之間差異的t檢驗結果①由于篇幅的原因,我們僅呈現四周患病率指標匹配質量的t檢驗結果。沒有呈現生活滿意度、IADL和自評健康指標的匹配質量的t檢驗結果。。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匹配前處理組和控制組在年齡、教育程度、是否參加勞動、家庭人口構成、家庭資產狀況等方面均有比較顯著的差異,而在匹配后,控制組中根據傾向得分選取的樣本組與處理組在可觀測變量方面的差異均有所減小,說明選取的控制組樣本與處理組能夠保持一致性,具有較好的匹配質量。匹配后的核密度函數見圖1,兩組變量的特征在匹配后是相似的。表3是我們進一步呈現了匹配后的數據整體平衡條件的檢驗結果。

表2 匹配質量的t檢驗結果(四周患病率)
2.回歸結果
表4呈現了基于PSM方法的平均處理效應ATT估計結果。我們采用近鄰匹配(Nearest-Neighbor Matching)方法下的1對2匹配作為主要結果進行呈現(見表4第1列),此外將近鄰匹配中1對1匹配、1對4匹配以及半徑匹配(Radius Matching)和核匹配(Kernel Matching)作為穩健性檢驗(見表4第2-5列)。結果顯示,在不同的匹配方法下,估計結果的顯著性和符號與主要結果保持一致。此外表4還呈現了每種匹配方法下不滿足假設的樣本數目,即不滿足共同支撐要求的觀測值,這些觀測值與總體數量相比,數量非常小,可以認為共同支撐要求未對樣本總體產生較大影響。
表4第1列中,匹配之后四周患病率與生活滿意度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不等于0,相對于非留守父母,留守父母會因為子女外出務工導致過去四周患病的概率增加2.7個百分點,顯著降低對于生活滿意度的評價。回歸結果表明成年子女外出務工會對留守父母在短期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我們分析可能的原因是由于與父母共同居住的子女外出務工時,家庭的照料方式會遭到破壞,而缺少子女照料后產生的孤獨、焦慮以及壓力對身體和心理健康產生了負面影響。[3][18]此外子女外出務工顯著減少了留守父母得到的日常生活上的實質性支持,增加了父母在農活和家務上花費的時間。[19-20]與此同時,子女外出后與留守父母的情感交流的減少也會對父母健康狀況產生消極影響。[7]

表3 匹配質量的整體檢驗結果

表4 子女外出務工對留守父母健康的影響
我們的研究結果與國內外文獻是保持一致的。Ao等人使用中國鄉城人口流動調查(the Longitudinal Survey on Rural Urban Migration in China)2009年的截面數據,研究發現子女移民增加了父母健康惡化的可能性。[12]Huang等人使用CHNS 1997至2006年的面板數據研究發現子女外出務工對父母健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13]Antman使用來自墨西哥2001年的問卷調查數據研究發現子女移民增大了父母身體和心理健康惡化的可能性。[1]國內相關研究中,舒玢玢、同鈺瑩使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2012年的截面數據,研究發現成年子女外出務工會對農村老年人健康產生不利的影響,長期兩地分離而導致家庭照顧支持和情感支持的減少是老年人健康狀況變差的主要原因。[21]連玉君等使用CHNS 2006年和2009年的數據研究發現子女外出務工使得父母自評健康和生活滿意度雙雙下降。[4]
從表4中我們發現IADL指標在匹配后的ATT值并不顯著。那么這是否說明子女外出務工對于父母長期健康因素不產生影響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進一步考察不同年齡分組的留守父母數據匹配后的平均處理效應。在表5中,對于65歲及以上的老年父母,匹配后的ATT值均顯著不為0,相比非留守父母,留守父母會因為子女外出務工而不能完成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的概率增加6.1個百分點。這表明子女外出務工對于65歲及以上的老年留守父母的長期身體健康狀況有一定的消極影響。我們分析這可能是因為相比較年輕的留守父母,老年的留守父母對子女照料的依賴程度更高,從而受到子女外出務工這一行為的影響也更顯著。這一結果與國際研究的發現是一致的,Ao等人研究發現子女移民對60歲及以下的留守父母的自評健康狀況沒有顯著的影響,但會增加60歲以上的留守父母有較差自評健康概率17.8個百分點。[12]

表5 區分年齡段考察子女外出務工對于留守父母IADL指標的影響
3.基于自評健康變量的穩健性檢驗
在主要回歸結果的基礎上,我們進一步使用自評健康這一綜合性指標來進行穩健性檢驗。在衛生經濟研究中自評健康被認為是一項較為穩定的度量健康狀況的指標。[22]由于自評健康變量僅在1997年、2000年、2004年和2006年的調查問卷中進行詢問,因此本部分穩健性檢驗采用1997-2006年的數據樣本。表6顯示在以自評健康作為關鍵被解釋變量時,匹配后的平均處理效應顯著不為0,相比非留守父母,留守父母會因為子女外出務工而增加自評健康較差的概率6.4個百分點。表明子女外出務工對留守父母的自評健康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這與我們之前的研究結論保持一致,驗證了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表6 子女外出務工對留守父母自評健康的影響
4.子樣本的回歸結果
為了進一步從性別差異角度檢驗子女外出務工對留守父母健康狀況影響的異質性,我們分別對兩類子樣本進行了匹配回歸。
表7中Panel A是對留守父親和母親進行分組,呈現了匹配后的ATT值。我們發現留守父親會因為子女外出務工增加患病概率3.6個百分點,而留守母親則會增加患病概率2.3個百分點。對生活滿意度指標的回歸結果也顯示對留守父親產生的消極影響要略大于留守母親。表7中Panel B是對外出務工的兒子和女兒進行分組,回歸結果顯示,相比較非留守父母,留守父母會因為兒子外出務工而增加患病概率3.7個百分點,因為女兒外出務工而增加患病概率2.9個百分點。對生活滿意度指標的回歸結果也顯示,兒子外出比女兒外出給留守父母帶來的健康沖擊更大。針對這一結果,我們分析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國農村地區是父權制體系,農村兒女所承擔照護老人的角色不同。[20]兒子在經濟和日常照料上承擔主要責任,[23]而女兒的照料責任通常出于親情而非社會期望。[24]根據2009年西安交通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在安徽省巢湖市進行的“安徽省農村老年人生活福利狀況”調查的數據,研究發現與女兒外出相比,外出兒子為父母提供的生活照料在外出前后的降低效果更明顯。[20]因此,兒子的外出更有可能破壞家庭原有的模式,并對父母健康造成影響。

表7 子樣本的回歸結果
六、主要結論
成年子女的外出務工是由城市化推動的獨特的人口遷移活動。在仍然以家庭養老為主要養老方式的我國農村地區,子女外出對留守父母健康產生的影響受到廣泛的關注。本文研究發現有成年外出務工子女的留守父母的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狀況比沒有外出務工子女的父母要差,而且這種負面影響對父親更大。我們的研究發現與家庭破壞理論模型保持一致,強調了父母與承擔其照料責任的成年子女異地分離的破壞性影響。此外,我們的研究發現成年兒子的外出對父母健康的負面影響更大。基于以上結論,為了彌補以家庭支持為主的傳統養老模式,政府部門應當加強對農村地區社區和機構照料的投入和建設,以期彌補由于子女外出,照料缺失給父母帶來的健康影響。
由于CHNS問卷變量的局限,我們承認本文存在兩點研究不足,這也是今后可以拓展研究的方向。第一,雖然研究發現子女外出務工對留守父母健康產生負面影響,但影響的作用機制還需要進一步深入分析。第二,子女外出務工時間長短對于留守父母的健康產生的負面影響可能在程度上有所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