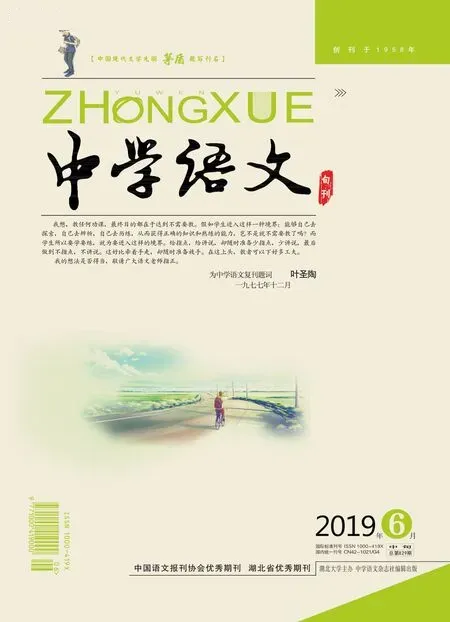木屑覆蓋空曠的中年
——霍俊明《燕山林場》賞析
李漢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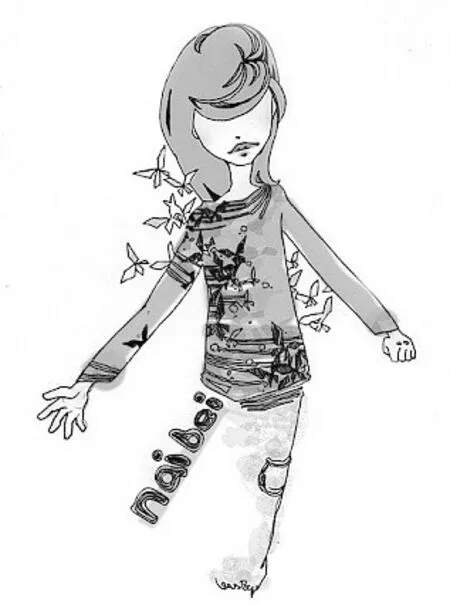
在中國當代詩壇,有一批詩人兼寫詩評,也有一些詩評家兼寫詩歌,兩者相互補充,相得益彰。霍俊明是著名的詩歌評論家,又是自覺成熟的詩人,他把寫詩評和寫詩歌看做是左手和右手的關系,一只更為專業,一只略顯“業余”,二者相互支持,相映生輝。寫詩評是理性的,講究文章的邏輯性和嚴謹性,而寫詩是感性的,依情生發,率性而為。他說:“評論家寫詩,就像真正做一次紅燒肉,了解了從切料、下鍋有多辛苦,吃下去時才會尊重。對文本不尊重,你的理論都是輕率的。”近年來,他的詩評越寫越棒,詩歌也越寫越好,這恐怕得益于他寫詩評和寫詩歌的融合效應。他的詩歌《燕山林場》,以舒緩從容的筆觸敘寫瑣碎、空曠、芬芳、尷尬、冷清的中年氣象,感染著每一個讀者——
當我從積重難返的中年期抬起頭來
燕山的天空,這清脆泠泠的杯盤
空曠的林場,伐木后的大地木屑紛紛
那年冬天,我來到田野深處的樹林
確切說面對的是一個個巨大的樹樁
我和父親坐在冷硬的地上,屁股硌得生疼
生銹的鋸子在嘎吱的聲響中也發出少有的亮光
鋸齒下細碎的木屑越積越多
我露出大腳趾的七十年代有了楊木死去的氣息
芬芳,溫暖
那個鋸木的黃昏,吱呀聲中驚飛的烏鵲翅羽
如雨的風聲在北方林場的上空空曠地響起
當我在矮矮的山頂,試圖調整那多年的鋸琴
動作不準,聲音失調
我想應該休息一會兒,坐在樹樁的身邊
而那年的冬天,父親只是拍拍我的肩膀
那時,罕見的大雪正從天空中斜落下來
(選自《滇池》2014年第3期)
霍俊明,河北豐潤人。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國現代文學館首屆客座研究員。著有《尷尬的一代:中國7 0后先鋒詩歌》《新世紀詩歌精神考察》等多部,編選《百年新詩大典》《中國年度詩歌精選》等多種。曾獲首屆揚子江詩學獎、《星星》年度最佳批評家、《詩選刊》年度詩評家、首屆海子青年詩人獎等多項獎勵。現任職于中國作協創研部。

詩人霍俊明陷入冥想之中
全詩共有17 行,分為五節,多用長句。人到中年,詩人站在空曠的林場,回憶當年與父親伐木的情景,眾多細節構筑的過去歲月歷歷在目,但物是人非,內心涌起無數情感的浪花,不是盡情開放,而是將中年的體驗與感觸內斂在看似平靜的敘述之中。詩人對中年有哪些獨特的體驗與感觸呢?
其一,中年是瑣碎的。中年是人生的成熟期,如同季節進入秋天一樣,但過去的那些往事時不時就會回憶,往事中的那些苦痛和憂悶就會郁積在心中,常常壓得抬不起頭來。所以,“當我從積重難返的中年期抬起頭來”,詩人看到的是“伐木后的大地木屑紛紛”。詩人記憶的“木屑”也開始紛揚起來:“巨大的樹樁”“冷硬的地上”“ 生銹的鋸子”“嘎吱的聲響”……與伐木有關的記憶碎片接踵而來,那么,與其他事情有關的記憶片斷是不是也會接踵而至呢?青年人常思將來,中老年常思過往,那些零散瑣碎的記憶就會覆蓋我們的歲月。
其二,中年是空曠的。中年雖然“積重難返”,但在抬起頭來的那一刻,詩人首先看到的是“燕山的天空”和“空曠的林場”。天空如同“清脆泠泠的杯盤”,空蕩寂寥;林場“如雨的風聲”空曠地響起,沒有阻攔,給人荒涼冷清之感。這是一種什么樣的“空曠”呢?決沒有草原的遼闊,決沒有大海的蒼茫,有的只是歲月的虛空和寥落。
其三,中年是芬芳的。中年是衰老的開始,過去的美好一去不復返,盡管“鋸齒下細碎的木屑越積越多”,盡管“我露出大腳趾的七十年代”已成記憶,盡管“那個鋸木的黃昏,吱呀聲中驚飛的烏鵲翅羽”,但是,當詩人聞到“楊木死去的氣息”,還是感到“芬芳,溫暖”。因為父親就在詩人身邊,給他依靠,給他力量;與父親一起勞動,累了想休息一下,父親沒有訓斥,“只是拍拍我的肩膀”。父愛恩重如山,親情暖徹人心。
其四,中年是尷尬的。風聲如雨,寒冷凄切;“鋸琴”猶在,難彈佳音。青春已隨那美好的樂章永遠地消逝了,“當我在矮矮的山頂”,哪怕“試圖調整”人生,但終因“動作不準,聲音失調”而無濟于事。中年精力漸衰,力不從心,人生出現許多尷尬真的是在所難免。
其五,中年是冷清的。詩中出現過“清脆泠泠”“如雨的風聲”“那年的冬天”等詞語,營造了冷清的詩境。特別是結尾“那時,罕見的大雪正從天空中斜落下來”,更是營造了一種大雪紛飛的寒冷氣象。物境即心境,那時即此時,詩人此時此刻的心境與那時白雪皚皚的物境相互映襯、相互烘托,渲染了氣氛,詩人的體驗也就寓于其中了。
綜上所述,本詩敘寫了詩人進入中年的復雜心情和豐富體驗,善用意象與細節抒寫內心的情感波瀾。燕山南麓,瀕臨京畿要地,是詩人的出生地和成長地。“燕山林場”既是大地上的實有之地,又是詩人的心靈之所,更是詩人進入中年的精神之鄉;“木屑”則成了一種零碎的記憶,是中年狀態的寫照。他將人生無限的感慨都寄寓其中,詩意飽滿而蘊藉。正如霍俊明自己所言:“精神的自我,必須在詩行中現身,因此物質性的世界得以在精神閃電的照徹中變形、過濾和提升。”
霍俊明是中國文壇走紅的詩歌評論家,他的評論站得高,望得遠,看得深,評得準。80 后先鋒詩人董喜陽說:“他的評論總是帶給讀者們一種隱忍而孤絕的感受,攜有沉郁而不事張揚的力量感,直抵當下詩人麻木的秉性,喚醒詩人內心之中警醒的耳朵。”他的詩學專著《尷尬的一代:中國70 后先鋒詩歌》,以其大膽、精辟、尖銳與真誠,曾引起學界與媒體的廣泛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