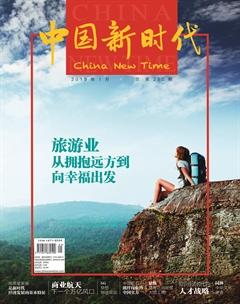知識(shí)經(jīng)濟(jì)時(shí)代的人才戰(zhàn)略
人才,已經(jīng)從被管理的“資源”變成了影響前途的“戰(zhàn)略資本”。
古往今來(lái),人才都是富國(guó)之本、興邦大計(jì)。先有,齊桓公不記追殺之仇,拜管仲為相;后有,劉備三顧茅廬請(qǐng)諸葛亮出山。求賢若渴,古來(lái)有之。
進(jìn)入21世紀(jì),科技日新月異,創(chuàng)新進(jìn)入密集活躍期。聯(lián)合國(guó)教科文組織一項(xiàng)研究發(fā)現(xiàn):信息通信技術(shù)帶來(lái)了人類知識(shí)更新速度的加速。在18世紀(jì)時(shí),知識(shí)更新周期為80年?90年;19世紀(jì)到20世紀(jì)初,縮短為30年;20世紀(jì)六七十年代,一般學(xué)科的知識(shí)更新周期為5年?10年;到了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許多學(xué)科的知識(shí)更新周期縮短為5年;而進(jìn)入21世紀(jì)時(shí),許多學(xué)科的知識(shí)更新周期已縮短至2年?3年。
如今,創(chuàng)新每天都在發(fā)生,正在改變著全球經(jīng)濟(jì)格局。因此在企業(yè)、產(chǎn)業(yè)、地域的競(jìng)爭(zhēng)中,人才被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成為實(shí)現(xiàn)民族振興、贏得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主動(dòng)權(quán)的決定性戰(zhàn)略資源。
人才,已經(jīng)從被管理的“資源”變成了影響前途的“戰(zhàn)略資本”。
黨的十九大報(bào)告提出,人才是實(shí)現(xiàn)民族振興、贏得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主動(dòng)的戰(zhàn)略資源。在知識(shí)經(jīng)濟(jì)時(shí)代,人才不再是被管理的對(duì)象而是企業(yè)、產(chǎn)業(yè)乃至國(guó)家競(jìng)爭(zhēng)力的一部分。
世界銀行公布的2018人力資本指數(shù)(HumanCapitalIndex),比較了157個(gè)國(guó)家和地區(qū)對(duì)年輕人在教育與健康領(lǐng)域的投資。報(bào)告認(rèn)為,一個(gè)經(jīng)濟(jì)體對(duì)教育和健康的投資越大,其勞動(dòng)者的創(chuàng)造力和薪資往往越高,從而使得該經(jīng)濟(jì)體財(cái)富值更高,經(jīng)濟(jì)更強(qiáng)大。
世界經(jīng)濟(jì)論壇(WEF)每年發(fā)布的《年度全球人力資本報(bào)告》,衡量“哪個(gè)國(guó)家的人民有工具(資本)進(jìn)行第四次工業(yè)革命”。
不僅世界組織關(guān)注各國(guó)人力資本的情況,甚至《柳葉刀》雜志也發(fā)表了一篇由健康指標(biāo)和評(píng)估研究所(IHME)撰寫的《人力資本指數(shù)》報(bào)告,根據(jù)教育和健康參數(shù)給國(guó)家打分、排名。
權(quán)威組織對(duì)“人力資本指數(shù)”的關(guān)注,體現(xiàn)出人才在知識(shí)經(jīng)濟(jì)時(shí)代的重要性。英國(guó)廣播公司(BBC)經(jīng)濟(jì)事務(wù)編輯阿赫邁德(KamalAhmed)分析,當(dāng)人力資本指數(shù)影響力足夠大的時(shí)候,它將會(huì)替代GDP成為各國(guó)比較經(jīng)濟(jì)實(shí)力的標(biāo)桿,它的參數(shù)也就會(huì)成為各國(guó)、各地大力投資的新領(lǐng)域。
人才的價(jià)值
人力資本與物質(zhì)資本同樣重要,二者共創(chuàng)、共享企業(yè)的價(jià)值。
華夏基石集團(tuán)董事長(zhǎng)彭劍鋒在其著作《混沌與秩序(下)——變革時(shí)代的管理新思維》中提到了華為怎樣看重人才,“華為的虛擬股權(quán)制(利潤(rùn)分享制)是典型代表,華為公司86%的員工擁有96%的收益權(quán),實(shí)現(xiàn)了共同致富。在華為,任正非持股份1.4%,某種意義上他也是人力資本。所以說是知識(shí)在雇傭資本,勞動(dòng)與資本一樣具有剩余價(jià)值分配權(quán)。”
人才成為資本,人力資源管理的核心目標(biāo)也隨之改變?yōu)樵鯓幼屓瞬派怠H肆Y源管理必須關(guān)注人的價(jià)值創(chuàng)造,使每個(gè)員工成為價(jià)值創(chuàng)造者,使每個(gè)員工有價(jià)值地工作,實(shí)現(xiàn)人力資本價(jià)值的增值。
過去,升職、加薪是最好的動(dòng)力。一旦老板答應(yīng)要給更高的職位或者更高薪水,員工自然就格外賣力地工作。
現(xiàn)在,讓人才創(chuàng)造價(jià)值,讓人力資本升值的辦法必須變一變了。當(dāng)被管理的對(duì)象是不為衣食住行發(fā)愁,而為實(shí)現(xiàn)自我努力的新一代時(shí),單憑多給幾塊錢的工資,已經(jīng)無(wú)法讓他們釋放激情了。
360創(chuàng)始人周鴻在為《驅(qū)動(dòng)力》一書薦言中說:“在互聯(lián)網(wǎng)行業(yè)工作的十多年,我從來(lái)沒有見過哪一個(gè)團(tuán)隊(duì)把金錢作為最重要的激勵(lì)因素。那種源自內(nèi)心的驅(qū)動(dòng)力最為強(qiáng)大,希望作出與眾不同的創(chuàng)意,追求完美,關(guān)注細(xì)節(jié),持續(xù)改善,不斷尋求更高的目標(biāo)。”
喬布斯說他花了半輩子時(shí)間才充分意識(shí)到人才的價(jià)值。他在講話中說:“我過去常常認(rèn)為一位出色的人才能頂兩名平庸的員工,現(xiàn)在我認(rèn)為能頂50名。”對(duì)比亨利·福特當(dāng)年對(duì)流水線工人的理解,他認(rèn)為流水線只需要員工動(dòng)手而不用腦,“每次只需要一雙手,來(lái)的卻是一個(gè)人。”時(shí)代變化帶來(lái)對(duì)人才價(jià)值的認(rèn)識(shí)的變化。
如今,好員工的定義,已經(jīng)從老實(shí)、安分,變成了勇于挑戰(zhàn)。美國(guó)國(guó)際商業(yè)機(jī)器公司(IBM)的開拓者ThomasWatsonJr.把丹麥哲學(xué)家歌爾科加德的一段名言作為自己的管理格言:“野鴨或許能被人馴服,但是一旦被馴服,野鴨就失去了它的野性,再無(wú)法海闊天空地自由飛翔了。”他對(duì)于人才價(jià)值的認(rèn)識(shí)尤為深刻,他甚至說,“對(duì)于那些我并不喜歡、卻有真才的人的提升,我從不猶豫。我所尋找的就是那些個(gè)性強(qiáng)烈、不拘小節(jié)、有點(diǎn)野性,以及直言不諱的人。如果你能在你的周圍發(fā)掘許多這樣的人,并能耐心地聽取他們的意見,那你的工作就會(huì)處處順利。”
阿里巴巴接班人張勇在一次演講中也提到對(duì)于兩種人才更欣賞:體制內(nèi)的不安分者和跨國(guó)公司的叛逆者。“體系內(nèi)的不安分的人,在這里日子過得很好,但老想干點(diǎn)啥,到我們這兒來(lái)吧。第二個(gè)是招跨國(guó)公司的叛逆者,我最關(guān)心這個(gè)人置于這個(gè)體系,是他創(chuàng)造了這個(gè)體系,還是這個(gè)體系成就了這個(gè)人。特別在跨國(guó)公司里,很多人就像螺絲釘一樣,他可能在一個(gè)體系里面轉(zhuǎn)的。但是如果是你把中國(guó)業(yè)務(wù)從零打出來(lái)的,或者你去的時(shí)候,這個(gè)東西本來(lái)沒有,建了這個(gè)體系,這是本質(zhì)的不同,區(qū)別是人造就了事情,還是事情造就了人。”
人的管理的變革
無(wú)論是在大企業(yè)還是小企業(yè)中,都需要一個(gè)部門或者個(gè)人來(lái)管理“人”,這個(gè)部門的名字可能是人事部、人力資源部,現(xiàn)在有的企業(yè)稱為人力資本部。這個(gè)部門的職責(zé)其實(shí)一直在變化,其背后體現(xiàn)出人在企業(yè)中的作用與地位的變化。
在工業(yè)化初期,勞動(dòng)力是工廠成本的一部分,人的勞動(dòng)被算在成本中,管理專家們探討的是怎樣讓人更高效地工作。科學(xué)管理的創(chuàng)始人泰勒認(rèn)為,科學(xué)管理最重要的任務(wù)是追求最高效率,“諸種要素——不是個(gè)別要素的結(jié)合,構(gòu)成了科學(xué)管理,它可以概括如下:科學(xué),不是單憑經(jīng)驗(yàn)的方法。協(xié)調(diào),不是不和別人合作,不是個(gè)人主義。最高的產(chǎn)量,取代有限的產(chǎn)量。發(fā)揮每個(gè)人最高的效率,實(shí)現(xiàn)最大的富裕。”
以這一管理思想為指導(dǎo)的管理時(shí)代,更看重怎樣讓人與機(jī)器、人與人的結(jié)合得到最高的生產(chǎn)率。這時(shí),管理的對(duì)象大部分是工人,因此管理是規(guī)范化、標(biāo)準(zhǔn)化的:用培訓(xùn)來(lái)教給工人完成任務(wù)的技能,用科學(xué)研究來(lái)制定標(biāo)準(zhǔn)和規(guī)章制度并據(jù)此規(guī)定和下達(dá)任務(wù),用獎(jiǎng)懲等激勵(lì)機(jī)制來(lái)保證任務(wù)的完成。同時(shí),對(duì)人才的培訓(xùn)和發(fā)掘,使每個(gè)工人盡之所能,為公司提供最高的價(jià)值。
當(dāng)時(shí),歐美國(guó)家正處于工業(yè)化進(jìn)程中,科學(xué)管理讓工廠的效率大大提高,美國(guó)福特汽車的流水線生產(chǎn)方式就是科學(xué)管理在實(shí)際生產(chǎn)中的應(yīng)用。以勞動(dòng)分工和工廠制度獲取生產(chǎn)效率催生了流水線,而流水線的出現(xiàn)徹底摧毀了作坊式的生產(chǎn)方式,大規(guī)模生產(chǎn)方式誕生,制造的規(guī)模和速度呈幾何式增長(zhǎng)。之后,豐田的精益生產(chǎn)把科學(xué)管理運(yùn)用得更好,成就了日本的經(jīng)濟(jì)崛起。
泰勒科學(xué)管理認(rèn)為最高的工作效率是雇主和雇員達(dá)到共同富裕的基礎(chǔ),在科學(xué)管理體制下,工人們發(fā)揮最大程度的積極性;作為回報(bào),則從他們的雇主那里取得某些特殊的刺激。
當(dāng)企業(yè)管理的對(duì)象不僅僅是工人的時(shí)候,過于嚴(yán)苛的管理方式就無(wú)法帶來(lái)更高的效率了。在現(xiàn)代企業(yè)中,員工不是機(jī)器的一部分,員工的自主意識(shí)更強(qiáng),而員工積極性的提高可以帶來(lái)增值與回報(bào)。因此管理的重點(diǎn)變成發(fā)掘員工的潛力,管理的任務(wù)也更加復(fù)雜,比如把正確的人放在正確的崗位上,培訓(xùn)員工以使其更適應(yīng)崗位,發(fā)放福利薪資以刺激員工的積極性等等。
人力資源的作用是根據(jù)企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的要求,有計(jì)劃地對(duì)人力資源進(jìn)行合理配置,通過對(duì)企業(yè)中員工的招聘、培訓(xùn)、使用、考核、激勵(lì)、調(diào)整等一系列過程,調(diào)動(dòng)員工的積極性,發(fā)揮員工的潛能,為企業(yè)創(chuàng)造價(jià)值,給企業(yè)帶來(lái)效益。
隨著電腦、辦公軟件的普及,人力資源管理逐漸成為一個(gè)系統(tǒng)的管理體系,數(shù)據(jù)庫(kù)將幾乎所有與人力資源相關(guān)的數(shù)據(jù)都進(jìn)行了收集與管理。
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jiǎng)得主埃德蒙·費(fèi)爾普斯在《大繁榮》一書中,闡述為什么經(jīng)濟(jì)繁榮能于19世紀(jì)20年代到20世紀(jì)60年代在某些國(guó)家爆發(fā)。他的觀點(diǎn)是,興盛的源泉是現(xiàn)代價(jià)值觀,例如,參與創(chuàng)造、探索和迎接挑戰(zhàn)的愿望。
這一論點(diǎn),在當(dāng)下也十分契合現(xiàn)實(shí)。在知識(shí)經(jīng)濟(jì)時(shí)代,移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的繁榮,同樣帶動(dòng)了一批有創(chuàng)造性的人才的自我實(shí)現(xiàn),因此,這個(gè)時(shí)代里,人的重要性和作用超過以往任何時(shí)候。企業(yè)最重要的競(jìng)爭(zhēng)力是創(chuàng)新,而人才是創(chuàng)新的動(dòng)力。兩個(gè)年輕人在咖啡廳里聊出的一個(gè)創(chuàng)意,可能被投資者看中,后來(lái)甚至開創(chuàng)一個(gè)產(chǎn)業(yè)。一個(gè)喜歡到各種飯店試吃的自媒體人,他發(fā)布的公眾號(hào)文章可能帶來(lái)上萬(wàn)甚至幾十萬(wàn)的閱讀量,從而為飯店提供了價(jià)值百萬(wàn)的免費(fèi)廣告。
互聯(lián)網(wǎng)已經(jīng)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同時(shí)也對(duì)傳統(tǒng)的人力資源管理提出了挑戰(zhàn)。當(dāng)90后、00后進(jìn)入職場(chǎng),這些伴隨互聯(lián)網(wǎng)、智能手機(jī)、平板電腦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新人才,以新的思維模式、行為方式、價(jià)值理念、職業(yè)訴求,給人力資源管理體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對(duì)于人才的管理方法也在變化。《2018德勤全球人力資本趨勢(shì)報(bào)告——社會(huì)企業(yè)的崛起》的調(diào)查顯示,隨著個(gè)人權(quán)力的增加,組織正在改進(jìn)自己的勞動(dòng)力管理方法、獎(jiǎng)酬制度和職業(yè)模式,以便更好地傾聽和回應(yīng)。尤其是,隨著組織外部的員工和網(wǎng)絡(luò)變得日益重要,公司正在努力與勞動(dòng)力生態(tài)系統(tǒng)的每一部分建立有效的持續(xù)關(guā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