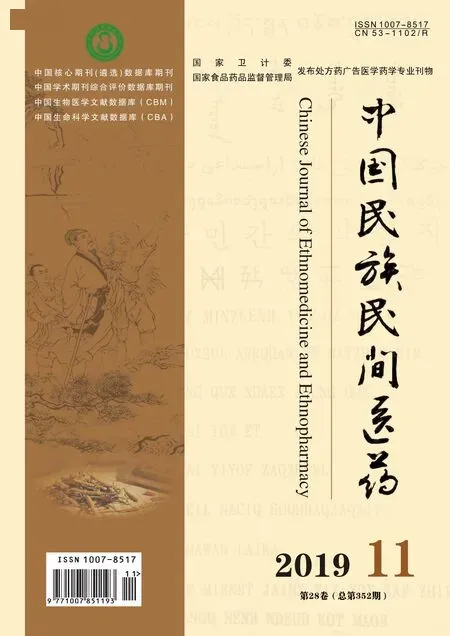張仲景煩躁證治用藥規律淺析
戴希勇 魏開建
福建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人民醫院,福建 福州 350001
煩躁為證名,煩指心中煩悶有熱感,躁指身體躁動不安,煩與躁可有先后之別,先煩后躁者稱煩躁,先躁后煩著稱躁煩。《中醫大辭典》中對煩躁的定義為:煩為心熱,郁煩;躁為躁急,躁動[1]。現代醫學對煩躁患者多使用鎮靜藥物進行干預,但大部分鎮靜藥物具有成癮性及一定副作用,且停藥易復發,長期用藥易出現不良反應[2]。中醫藥在治療煩躁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傷寒論》與《金匱要略》中對煩躁論述頗多,方證兼備,通過對其用藥規律的分析,可為臨床診療提供借鑒。
1 煩躁條文及方劑統計分析
煩躁是《傷寒論》中出現頻率第2的癥狀[3],張仲景雖然無專篇論述煩躁,但據筆者統計,通過對“煩躁”、“煩”、“躁”、“心煩”、“心中煩”、“燥煩”、“煩躁欲死”、“煩亂”、“煩驚”、“煩疼”等詞進行檢索,《傷寒論》、《金匱要略》中有113條原文涉及煩躁的論述。其中治法方劑兼備的條文共64條,涉及方劑46首,用藥63味。
《傷寒論》與《金匱要略》中治療煩躁的方劑共有46首,包括桂枝湯、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桂枝附子湯、去桂加白朮湯、桂枝加黃芪湯、白虎加人參湯、白虎加桂枝湯、麻黃湯、麻黃加朮湯、大青龍湯、小青龍加石膏湯、甘草干姜湯、干姜附子湯、五苓散、茯苓四逆湯、梔子豉湯、梔子甘草豉湯、梔子生姜豉湯、梔子厚樸湯、梔子干姜湯、小柴胡湯、大柴胡湯、柴胡桂枝湯、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柴胡桂枝干姜湯、小建中湯、大陷胸湯、文蛤散、甘草瀉心湯、甘草附子湯、大承氣湯、小承氣湯、調胃承氣湯、黃連阿膠湯、吳茱萸湯、豬膚湯、白通加豬膽汁湯、豬苓湯、烏梅丸、瓜蒂散、赤豆當歸散、侯氏黑散、酸棗仁湯、枳實芍藥散、竹皮大丸、腎氣丸。
由表1可知,太陽經內涉及煩躁的方劑便有24首,乃諸經之魁首,其方大致可分為四類:其一、治外邪入侵,衛氣不宣,陽氣內郁,郁熱內擾心神所致之煩躁,以桂枝湯、麻黃湯、大青龍湯等為代表;其二、治在表之邪未解,內有膀胱蓄水,胃乏津液不和所致之煩躁,以五苓散等為代表;其三、誤治后邪熱留擾胸膈所致之煩躁,有虛實之分,以梔子豉湯類、大陷胸湯等為代表;其四、誤治致陽氣虛損,心神不得收斂溫養,浮越于外所致之煩躁,以甘草干姜湯,干姜附子湯等為代表。陽明經以承氣湯類為代表,治陽明腑實,燥熱上擾心神所致之煩躁。少陽經以小柴胡湯類為代表,治樞機不利,膽火內郁,上擾心神所致之煩躁。少陰經多見本虛標實,或陽虛致寒濁中阻,中焦氣機逆亂而致煩躁(如吳茱萸湯證),或腎陰虧虛不能上濟心火,心火獨亢于上而致煩躁(如黃連阿膠湯證),或陰陽皆虛,陰不系陽,虛陽擾心而致煩躁(如白通加豬膽汁湯證)。厥陰經主論有形之邪阻遏陽氣,陽郁而濁陰不降之煩躁,其代表方為瓜蒂散。《金匱要略》所用方劑雖多,然其與《傷寒論》相通,可參上文。

表1 《傷寒論》《金匱要略》中涉及“煩躁”條文統計
2 《傷寒論》《金匱要略》治療煩躁藥物統計結果
2.1 藥物頻率、配伍分析 筆者將46首方劑中涉及藥物全部列出,共得227味,除去重復的藥物后,統計出46首方劑共運用了63種中藥(表2),其中出現頻數超過3的共有19味,占整體達70.04%。通過分析表2藥物的功效及組方特點,可見張仲景治療煩躁時可謂八法并用。汗法見于麻黃湯類,以麻黃、桂枝發汗驅邪,透熱宣郁;吐法見于瓜蔞散,以瓜蔞涌吐痰實;下法見于承氣湯類,以大黃、芒硝、枳實、厚樸攻逐燥實,通腑泄熱;和法見于柴胡湯類,以柴胡、黃芩樞利肝膽,暢達氣機;溫法見于甘草附子湯等,以附子補火助陽;清法見于梔子豉湯類,以梔子苦寒直折邪熱;消法見于枳實芍藥散等,以枳實行氣散結,芍藥和血止痛;補法見于小建中湯、酸棗仁湯等,以補虛扶正,旨在使正盛而驅邪外出。

表2 張仲景治療煩躁46首方劑中藥物頻數、頻率統計結果
續表2
2.2 藥物四氣、五味分析 筆者將表2出現頻數前19味藥物性味歸經以《中藥學》[4]為準整理為表3。將“大寒”、“微寒”并入“寒”,“大熱”并入“熱”,“微溫”并入“溫”,統計藥物四氣、五味的頻數、頻率。由表4可知,寒性乃諸氣之首,比例高達42.11%,其次則是溫性藥物,占36.84%。若將四氣劃分為溫熱、寒涼、平三大類,性屬溫熱的“微溫”、“溫”、“熱”、“大熱”的藥物占整體將近一半,達47.37%;性屬寒涼的“涼”、“微寒”、“寒”、“大寒”的藥物也占42.11%;性屬“平”的藥物占10.53%。其中“微溫”、“溫”、“熱”與“大熱”藥物頻數為9,“涼”、“微寒”、“寒”與“大寒”藥物頻數為8,可見張仲景治療煩躁不拘于寒涼,而善于寒熱并用,靈活加減。其治三陰病證之煩躁,多以附子、干姜、桂枝辛溫復陽;治三陽病證之煩躁,其寒溫并用,或以辛溫之藥宣閉開竅,發汗透熱,或以苦寒直折里熱,解郁除煩,或寒溫合法,外宣內清,表里雙解。張仲景以寒溫祛邪時亦不忘扶正,其善用生姜、大棗、甘草調和中州,使正氣生化有源,正盛邪自去。

表3 張仲景治療煩躁使用頻數前19味藥物性味、歸經統計結果
2.3 藥物五味分析 由表4可見,張仲景治煩躁用藥的五味屬性,辛、苦(將微苦歸入苦味之中)、甘味之藥居于前列,分別為30.00%、30.00%、26.67%。再結合藥物四氣分析,發現張仲景治療煩躁運用苦辛寒溫之品居多;另外,甘味藥物占26.67%,甘味和中,“人參、甘草、大棗”三藥合用,乃固護脾胃,使陽氣生化有源,溫養心神,斂神于內,不致心神浮越于外而生煩躁之證。諸藥合用,寒溫并舉,陰陽調和,則神有所養,不為外邪所擾,則煩躁自去。
2.4 藥物歸經分析 由表5可見,張仲景治療煩躁的藥物涉及十二正經中的十一條,通過對比頻數與頻率,發現前4為脾經、肺經、心經、胃經,分別為21.31%、19.67%、14.75%、14.75%;脾胃二經皆入前4,其兩者共計頻數為23,頻率達36.07%,體現了張仲景重視脾胃以及扶正祛邪的學術思想,脾胃乃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心主神志,卻離不開血氣的充養。肺主一身之氣,其布輸衛氣,外達皮毛,溫養分肉,充養皮膚,調節腠理,乃一身陰陽氣機之司。心主神志,主司意識情志,其受邪則見煩躁。根據藥物歸經的統計分析,可以說明煩躁病位在心,但與肺、脾、胃等臟腑皆有關聯。
綜上所述,通過對《傷寒論》及《金匱要略》中涉及煩躁的113條原文與46首方劑的統計分析可以看出,整體上張仲景治煩躁并不拘于寒涼,而是寒溫并舉,甘苦辛齊進,從心、脾、胃、肺論治。煩躁之病機乃在陰陽氣機之不和,或因陽郁于內而熱擾心神,或因陽虛心神失養而心神外越,或因實邪躁熱內擾心神,不一而足。然不論病因為何,張仲景皆有應對之法,其治法紛繁,包含了后世所謂的汗、吐、下、和、溫、清、消、補等“醫門八法”。通過對張仲景治療煩躁的條文、方劑、藥物進行統計分析,有助于總結張仲景治療煩躁遣方用藥規律,為提高臨床治療煩躁的療效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