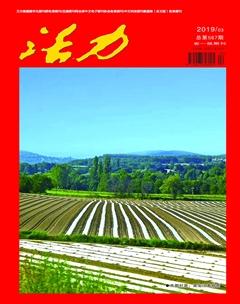列斐伏爾的“異化”概念
南楠
[摘要]列斐伏爾的“異化”概念是面對(duì)新時(shí)期新問題時(shí)對(duì)馬克思“異化”理論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他試圖削弱馬克思“生產(chǎn)決定消費(fèi)”的理論邏輯,強(qiáng)調(diào)消費(fèi)對(duì)社會(huì)的引導(dǎo)作用。他突破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與上層建筑的二分,凸顯日常生活這個(gè)微觀視角。對(duì)于異化的現(xiàn)實(shí),他把馬克思經(jīng)濟(jì)政治的宏觀革命理想轉(zhuǎn)為日常生活和文化革命的微觀革命設(shè)想。其理論過失則在于,過于割裂都市化與工業(yè)化以至于將兩者對(duì)立從而失去雄厚的物質(zhì)基礎(chǔ),使革命成為空中樓閣;忽視經(jīng)濟(jì)政治的批判與變革,單方面?zhèn)戎匚幕校鲃?dòng)將自身邊緣化,是舍本逐末的選擇。
[關(guān)鍵詞]異化;日常生活批判;文化革命;列斐伏爾
自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經(jīng)典論證表達(dá)了對(duì)清楚明白的知識(shí)的尋求、高揚(yáng)了理性至高無上的地位以來,法國(guó)哲學(xué)便一直有思辨的傳統(tǒng)。這容易造成一個(gè)傾向,是重視思維而忽視存在,理論豐富而經(jīng)驗(yàn)匱乏,日常生活便是在這種語境中被貶低、被削弱,成為無足輕重的部分。列斐伏爾對(duì)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史的重要貢獻(xiàn)就在于,通過重新闡釋馬克思的“異化”概念與“總體的人”的理論,將日常生活提升到理論的高度,成為哲學(xué)批判的對(duì)象。這與20世紀(jì)40年代以來法國(guó)哲學(xué)一來要求哲學(xué)走出抽象的理性王國(guó)面向日常生活世界同時(shí)又將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提升到形而上學(xué)層面的趨勢(shì)密不可分。
一、列斐伏爾“異化”概念的理論來源
列斐伏爾的“異化”概念主要來源于馬克思,他在馬克思“異化”理論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了重新創(chuàng)造與再度闡釋,從而使得馬克思的理論在面對(duì)新的歷史情境時(shí)繼續(xù)發(fā)揮著卓越的解釋效用。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用“商品拜物教”的概念來表示在資本主義社會(huì)背景下,用物的關(guān)系來代替和掩蓋人的關(guān)系的本性。馬克思關(guān)于“異化”的思想則是在《1844年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手稿》中集中地進(jìn)行了詳細(xì)闡述和論證。只是《1844年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手稿》在1932年才得以發(fā)表,此時(shí)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思想已形成。雖然盧卡奇等人為深入研究并逐漸豐富拓展馬克思關(guān)于異化的人本主義哲學(xué)思想作出不懈努力,但在當(dāng)時(shí)的歷史背景下“異化”仍然不能成為主流研究對(duì)象。
針對(duì)此現(xiàn)象,列斐伏爾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的再版中增添了關(guān)于異化的理論內(nèi)容,針對(duì)斯大林主義的教條主義和蘇聯(lián)社會(huì)主義思想家對(duì)異化的忽視進(jìn)行尖銳批評(píng)。這兩者作為正統(tǒng)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流派,對(duì)馬克思早期著作以及青年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和以實(shí)踐為核心的人本主義哲學(xué)構(gòu)想的了解不夠,主要繼承了馬克思“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以及“生產(chǎn)力決定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唯物史觀,重視經(jīng)濟(jì)、政治變革,而將人的生存模式和文化模式的變革視作次一級(jí)的、被決定的部分。“異化”概念隨著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手稿》的再發(fā)現(xiàn)而愈發(fā)被重視,在不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家的學(xué)說體系中頻繁出現(xiàn),不斷煥發(fā)活力。“異化”概念在《1844年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手稿》中主要表現(xiàn)為工人同其勞動(dòng)產(chǎn)品、工人同其勞動(dòng)、人同自己的類本質(zhì)以及人同人的異化四個(gè)方面。列斐伏爾雖然繼承馬克思的“異化”概念,但“異化”概念在列斐伏爾處與馬克思有很大不同。
馬克思談“異化”主要是在物質(zhì)生產(chǎn)層面談,“異化”這一事實(shí)在生產(chǎn)過程中就已經(jīng)形成——“勞動(dòng)所生產(chǎn)的對(duì)象,即勞動(dòng)的產(chǎn)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chǎn)者的力量,同勞動(dòng)相對(duì)立”。工人在勞動(dòng)中付出的越多,自己就越被削弱,而他親手創(chuàng)造出來的對(duì)象的力量也就越大。“異化”的四個(gè)環(huán)節(jié)在生產(chǎn)的過程中環(huán)環(huán)相扣,工人在“異化”的壓制中越陷越深。在馬克思處,生產(chǎn)對(duì)消費(fèi)起了決定性作用。列斐伏爾談“異化”主要是在消費(fèi)層面談,強(qiáng)調(diào)消費(fèi)而不是生產(chǎn)的主導(dǎo)作用。他在20世紀(jì)60年代首次提出,現(xiàn)代社會(huì)是一個(gè)“消費(fèi)被控制的科層制社會(huì)”。在這樣的社會(huì)中,日常生活在各種消費(fèi)體制的操縱下碎片化、神秘化。大量流行的次體系對(duì)日常生活無孔不入地進(jìn)行滲透與控制。日常生活在這種滲透與控制下,失去了創(chuàng)造力。凡是能被消費(fèi)的都變成了符號(hào),而符號(hào)則成為了現(xiàn)實(shí)。人們的欲望不斷被制造不斷被引導(dǎo),人們關(guān)心的不是自己真正需要什么,而是在消費(fèi)社會(huì)中被廣告、媒體等文化工業(yè)制造出來的需要。
馬克思談“異化”是從宏觀層面談,以勞動(dòng)為核心,立體地談生產(chǎn)力與生產(chǎn)關(guān)系,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與上層建筑,“生產(chǎn)力決定生產(chǎn)關(guān)系,經(jīng)濟(jì)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在資本主義的生產(chǎn)力條件下,“即使在對(duì)工人最有利的社會(huì)狀態(tài)中,工人的結(jié)局也必然是勞動(dòng)過度和早死,淪為機(jī)器,淪為資本的奴隸(資本的積累危害著工人),發(fā)生新的競(jìng)爭(zhēng)以及一部分工人餓死或行乞”。列斐伏爾談“異化”則是從微觀上談,平面化地談,這種“異化”遍及人們?nèi)粘I畹姆椒矫婷妫粌H僅是馬克思所說的經(jīng)濟(jì)層面而且是政治的、日常的,人們深陷其中而不自知——“異化不僅僅局限于勞動(dòng)領(lǐng)域,而且存在于消費(fèi)與人的各種需要領(lǐng)域,即日常生活領(lǐng)域;異化主要不是馬克思所關(guān)注的貧困問題,而是現(xiàn)代社會(huì)技術(shù)文明進(jìn)步所導(dǎo)致的全方位的社會(huì)問題。”他不再局限于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jì)基礎(chǔ)與上層建筑二分的理論視野,而是認(rèn)為上層建筑要以日常生活為基礎(chǔ)——“上層建筑之所以成為問題,乃是由于上層建筑雖然是上層形成,卻又時(shí)時(shí)刻刻楔入日常生活和社會(huì)實(shí)踐之中。這也是由于日常的實(shí)踐是分散的、零碎的,是個(gè)人的實(shí)踐,是一個(gè)一定的和個(gè)別的社會(huì)活動(dòng)的實(shí)踐,而上層建筑則與整個(gè)社會(huì)與全部社會(huì)實(shí)踐有一種關(guān)系,這就是說:上層建筑反映著部分中的全體,反之,也反映著全體中的部分。”同時(shí),在列斐伏爾看來,生產(chǎn)是符號(hào)的生產(chǎn),不是生產(chǎn)決定需求而是需求決定生產(chǎn),他在精神層面對(duì)此形成批判與非批判,將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轉(zhuǎn)為符號(hào)拜物教。但在東歐新馬克思主義處,赫勒繼承了列斐伏爾、馬爾庫塞的理論,在微觀層面上對(duì)社會(huì)主義異化進(jìn)行的批判卻消解了社會(huì)主義的目標(biāo),這對(duì)我們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也富有啟發(fā)意義。
在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中,國(guó)家是上層建筑中的權(quán)力統(tǒng)治中心,而在列斐伏爾處,取而代之的是日常生活微型權(quán)力的隱性抽象統(tǒng)治的“恐怖主義社會(huì)”,從而將馬克思對(duì)政治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的批判轉(zhuǎn)到日常生活的文化批判上。“恐怖主義的社會(huì)”指的是各種次體系對(duì)人的成功控制,并且這種控制會(huì)變?yōu)閭€(gè)體對(duì)自身的控制,它本身是過分壓抑的社會(huì)的結(jié)果。
二、列斐伏爾“異化”的表現(xiàn)
列斐伏爾認(rèn)為,現(xiàn)代資本主義社會(huì)處于全面異化的狀況中,異化的現(xiàn)實(shí)比馬克思所分析要更加復(fù)雜。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的異化并不直接決定政治的異化,也不直接決定日常生活的異化,這三者處于相互聯(lián)系的總體關(guān)系之中。異化現(xiàn)象遍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異化的諸多表現(xiàn)形式當(dāng)中,列斐伏爾重點(diǎn)分析了人思想意識(shí)的異化、需要的異化和個(gè)人與社會(huì)集體關(guān)系的異化。
思想意識(shí)的異化。異化了的思想意識(shí)也被稱為“被神秘化的意識(shí)”,是由于資本主義價(jià)值規(guī)律的抽象統(tǒng)治,即剩余價(jià)值脫離使用價(jià)值、脫離物本身,才導(dǎo)致了自我意識(shí)這種脫離現(xiàn)實(shí)、脫離生活的幻覺。列斐伏爾指出,首先是拜物教,接著從拜物教的狀態(tài)中派生出了異化,也就是人與自身的疏異性和距離性。此時(shí),當(dāng)社會(huì)停滯不前并且如果不打碎這種停滯不前的狀態(tài)社會(huì)便不能發(fā)生變化時(shí),人們的意識(shí)便被神秘化了。在1936年出版的《黑格爾著作導(dǎo)讀》中,列斐伏爾將這一思想進(jìn)一步表述為異化只有到了意識(shí)超出了它的理解范圍外才會(huì)發(fā)生。在人們?cè)噲D超越自身局限性的過程中,人自身的認(rèn)知欲望會(huì)升華為一種虛幻的形態(tài),一種可以解釋的神秘。人的意識(shí)變得麻木不仁,不再感到痛苦不堪的意識(shí)進(jìn)行了自我欺騙或者神秘化。個(gè)體的人的生存被抽象的社會(huì)關(guān)系所掩蓋。
人的需求的異化。列斐伏爾在其中后期日常生活批判理論中確立了消費(fèi)主導(dǎo)型的現(xiàn)代性批判的理論視野,認(rèn)為消費(fèi)成了異化統(tǒng)治的主要領(lǐng)域。他將受消費(fèi)控制的社會(huì)稱之為“消費(fèi)受控制社會(huì)”。他認(rèn)為現(xiàn)代社會(huì)是大量流行的無形的隱形的次體系對(duì)日常生活無孔不入的滲透和控制。“凡能夠被消費(fèi)的都變成了消費(fèi)的符號(hào),消費(fèi)者靠符號(hào),靠靈巧和財(cái)富的符號(hào)、幸福和愛的符號(hào)為生;符號(hào)和意謂取代了現(xiàn)實(shí)。”在這樣的社會(huì)中,符號(hào)代替了物的存在。凡是能夠被消費(fèi)的都成為了消費(fèi)的符號(hào),人們并不關(guān)心自己真實(shí)的需要,而是在一個(gè)又一個(gè)符號(hào)制造出來的需要中迷失自我,人們不擔(dān)心“貧窮”、“專制”而害怕不夠“時(shí)尚。”時(shí)尚通過排斥日常生活而統(tǒng)治日常生活,因?yàn)槿粘I畈粔驎r(shí)尚所以不能夠存在。
個(gè)體被流行的消費(fèi)心理觀念與大眾傳媒所編織設(shè)計(jì)的時(shí)尚體系所控制。流行的消費(fèi)心理觀念與大眾傳媒不斷制造偽裝和幻覺,滿足的不是人們的真實(shí)需求而是制造了虛假的需求。人們始終在追求被制造出來的虛假需求而忽視了真實(shí)的需求,由于真實(shí)的需求始終沒有被滿足而感到焦慮不安。人們對(duì)自己價(jià)值感的認(rèn)同由從前的生產(chǎn)創(chuàng)造性活動(dòng)轉(zhuǎn)為了消費(fèi)性活動(dòng)。
個(gè)人與社會(huì)集體關(guān)系的異化。人的本質(zhì)是社會(huì)性,人只有在同集體的關(guān)系中才能更好地認(rèn)識(shí)自身。人既不能脫離集體而獨(dú)立存在,也不該在集體中失去個(gè)性。但在現(xiàn)代社會(huì),分工將人們劃分到不同的范圍,社會(huì)共同生活被割裂,人也成為了相對(duì)獨(dú)立的個(gè)體。人和集體的關(guān)系被顛倒,人以為孤立的自身可以更好地認(rèn)識(shí)自己。但事實(shí)上,在這個(gè)過程中人脫離和喪失了認(rèn)識(shí)自身的基礎(chǔ),脫離了自身的社會(huì)根基。人們或者把自身當(dāng)做是一種理論上抽象的東西,諸如心靈、理想等;或者將自身視為一種生物存在,以軀體、欲望為主導(dǎo)。
在列斐伏爾看來異化是全方位的,表現(xiàn)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列斐伏爾認(rèn)為科技、傳媒等也都造成異化并且將異化在自身上體現(xiàn)出來。
三、列斐伏爾對(duì)“異化”的揚(yáng)棄與理論不足
列斐伏爾在《現(xiàn)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中全面總結(jié)和整合了自己60年代的研究成果,概括出總體性文化革命行動(dòng)綱領(lǐng)。其中最著名的口號(hào)在經(jīng)濟(jì)上是“技術(shù)要為日常生活服務(wù)”,政治上是“廢除國(guó)家與實(shí)行自治”,文化上是“讓日常生活成為一種藝術(shù)品”,包括性意識(shí)的革命、城市的改革以及對(duì)節(jié)日的再發(fā)現(xiàn)。
列斐伏爾認(rèn)為,“文化革命”作為一個(gè)概念,指的是藝術(shù)與日常生活創(chuàng)造性地融合。它不能被想象成是美學(xué)的,它的目標(biāo)和方向是創(chuàng)造一種不是制度的而是生活風(fēng)格的文化。文化革命作為藝術(shù)和藝術(shù)價(jià)值的復(fù)興,它主要具有實(shí)踐而不是文化的目標(biāo)。下文將具體敘述文化革命的三大方向。
第一,性意識(shí)的革命。這種變革試圖從意識(shí)形態(tài)的層面而不是制度的層面上改變性別與社會(huì)之間的關(guān)系,用理論和實(shí)踐的全部可行方案來稀釋新資本主義的全面壓抑和性恐怖主義。此時(shí),“性壓抑必然不再是制度所關(guān)心的(實(shí)際上,主要和制度相關(guān));它必須要根除;只要壓抑和恐怖越來越不局限于對(duì)性行為的控制,那么控制變會(huì)愈來愈擴(kuò)展到人類的整個(gè)能力與潛能領(lǐng)域。問題并不是要完全廢除對(duì)性行為的控制;實(shí)際上,徹底的放任自流,讓欲望轉(zhuǎn)化為赤裸的需求,可能會(huì)導(dǎo)致欲望的消失與退化;欲望不能無控制地存在,雖然壓抑確實(shí)建立在控制與扼殺欲望或使之扭曲的基礎(chǔ)上。性控制應(yīng)該由那些關(guān)心的人所掌握,而不是被制度所加強(qiáng),即便是它很少采用倫理和恐怖相結(jié)合的方法”。所謂的性解放和色情藝術(shù)的泛濫是消費(fèi)社會(huì)對(duì)人的欲望和身體的深層次控制,由此觀之性意識(shí)的革命不僅是意識(shí)形態(tài)的革命,更是對(duì)控制現(xiàn)代日常生活的抽象權(quán)力空間的革命。
第二,城市的改革。所謂城市的改革就是把傳統(tǒng)的節(jié)日?qǐng)雒嬷匦戮唧w化為發(fā)自欲望深處的詩性實(shí)踐所創(chuàng)造出的嶄新的生活情境。列斐伏爾希望用都市化的日常生活代替工業(yè)化社會(huì),從而去除科層制社會(huì)的種種弊病。人們?cè)谶@種都市化的日常生活中,將重新找回農(nóng)業(yè)社會(huì)或古代社會(huì)的快樂。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隨時(shí)進(jìn)行著詩性的創(chuàng)造與實(shí)踐——日常生活將變成為其中的每個(gè)公民與共同體各顯其能的創(chuàng)造(詩性的而不是實(shí)踐的)活動(dòng)。
第三,節(jié)日的再發(fā)現(xiàn)。在資本主義社會(huì),由于分層和制度化,節(jié)日成為例行公事,甚至是消費(fèi)社會(huì)中商家刺激消費(fèi)的契機(jī)。列斐伏爾希望被現(xiàn)代性所遮蔽的節(jié)日能重新煥發(fā)出光彩,調(diào)動(dòng)每個(gè)人感覺、身體、精神的全部投入,以及所有人不分貧富貴賤的平等參與。他希望節(jié)日不再屈從于商品化與情感的升華,而是與日常生活完全融為一體,用節(jié)日狂歡打破美好理想與枯燥現(xiàn)實(shí)的界限。
列斐伏爾的理論將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轉(zhuǎn)移到日常生活,試圖從微觀領(lǐng)域發(fā)起革命,別具一格。但卻在實(shí)踐中受挫。一方面,由于過于割裂都市化與工業(yè)化以至于將兩者對(duì)立,從而失去了雄厚的物質(zhì)基礎(chǔ),使革命成為空中樓閣;另一方面,由于忽視經(jīng)濟(jì)政治的批判與變革,單方面?zhèn)戎匚幕校鲃?dòng)將自身邊緣化,是舍本逐末的選擇。
參考文獻(xiàn):
[1]馬克思.1844年經(jīng)濟(jì)學(xué)哲學(xué)手稿[M].北京:中央編譯局,譯.2000.
[2]劉懷玉.現(xiàn)代性的平庸與神奇——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哲學(xué)的文本解讀》[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
[3]Henri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vlife,volume I[M],trans by Moore,Verso,London,New York.1991
[4]Henri Lefebvre,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rn World[M],Transaction Publishers,1994
[5]吳寧.列斐伏爾論現(xiàn)代社會(huì)的異化.[J].湖南文理學(xué)院學(xué)報(bào)(社科版).2007.
[6]范海武,劉懷玉.“讓日常生活成為藝術(shù)”:一種后馬克思主義的都市化烏托邦構(gòu)想[J].求是學(xué)刊,2004.
[7]仰海峰.列斐伏爾與現(xiàn)代世界的日常生活批判》[J].現(xiàn)代哲學(xué),2003.
[8]潘禹非.列斐伏爾的日常生活異化理論研究[J].知與行,2016.
[9]張一兵.當(dāng)代國(guó)外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思潮[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
[10]仰海峰.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
[11]何萍.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史教程(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劉懷玉.列斐伏爾:日常生活的恐怖主義批判[J].求是學(xué)刊,2007.
[13]劉懷玉.日常生活批判的瞬間、差異空間與節(jié)奏視角——以列斐伏爾為例[J].哲學(xué)分析,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