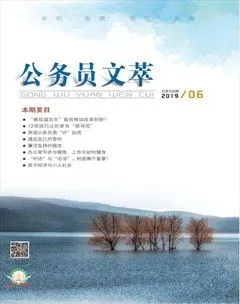機構改革:克了哪些難,還要闖幾關
劉江林
“物理整合已經完成,但化學反應還沒有真正揮發。”對于過去一年機構改革的進展,55歲的自然資源部調控和監測司原巡視員董祚繼如是評價,“改革的重點不在整合歸并、加減計算,而在打破各部門自身利益傾向,轉變政府職能。”
一、編制未定先“走”人
“編隨事走、人隨編走”,這是本次機構改革遵循的原則之一。在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研究員任永安的印象中,該部是本輪改革中最早進行人員重組的部委之一,2018年4月初,國務院原法制辦的180名機關人員就搬到了司法部辦公,由于時間倉促,很多搬遷工作甚至在夜間進行。生態環境部一位人士表示,由于搬進的人員眾多,辦公場地變得很擁擠,近期該部內部已經有是否需要重新選址辦公的聲音。
2018年4月初,原國家質檢總局開始做思想動員工作。彼時,7名原局領導的去向均已基本明確。而對于很多干部而言,其時并不知曉接下來可能的去處,“直接領導在與干部面對面談的時候,先問,你是想去海關總署還是市場監管總局,然后說尊重個人的意愿,但最后還是要服從組織決定。”海關總署一位處級干部表示,該人士之前任職于質檢總局。
一般來說,都會選擇去“發展前途更好”的地方,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市場監管總局新聞司是正局級單位,而海關總署新聞辦只是正處級單位,對原質檢總局從事宣傳崗位的干部來說,在傾向性上更愿意去規格更高的市場監管總局新聞司。
二、過渡期“加長板凳”
“過往的機構改革,突出困難是富余人員和領導職位的安排。”清華大學政治研究所所長于安覺得本輪改革基本解決了人員調配和思想認同工作。較典型的是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和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這兩個原副部級單位的職責劃入市場監管總局后,改由4個局級單位承擔他們的原有職能,對外僅保留牌子。
其中原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整個系統有800多人,委機關大概是100余人,屬參公管理單位。據了解,改革后原來的委機關只有10余人進入對應的司局,對超出編制的人員,市場監管總局實行自然過渡,以保證人員的妥當安置和分流。
其中一種方式是分流到新設的一些臨時機構,其二是分流到相關事業單位,其三是到達58歲以上的干部一律退居二線,最后一條路是自主擇業。
多個新機構組建后,帶來的突出問題是,中層及以下工作人員的發展空間在一定程度上被壓縮,晉升的機會減少、晉升時間拉長,對干部職工心理造成一定影響,容易引起思想波動。
在觀察人士看來,受影響最大的是40~50歲的第二梯隊干部,對三四十歲的第三梯隊干部影響還不明顯。
但一個反常的現象是,過去一年,第三梯隊中青年干部下海的勢頭有所抬升。前述海關總署處級干部說:“在海關和原質檢系統,受機構改革影響,從事跨境貿易監管業務的中青年干部,被高薪挖到互聯網公司,從事跨境貿易政務工作的比例在提升,尤其是在擁有大型電商平臺的江浙地區。”
在基層,“被改革者”受到的心理影響會更甚。東部省份某市農林局一位人士表示:“差不多近半年時間,一些處室的干部們都在觀望、等待,會和什么單位的處室合并,是否要職變成閑職,這意味著最后在哪里退休的問題。”
為了平穩推進機構改革,一些部委和地方采取“加長板凳”的方式,將改革前的部門負責人悉數納入新單位的班子,爭取以“時間換空間”。
某中央黨校副局級干部介紹,新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目前有一正五副共6名領導,而正常的配備應該是一正兩副。與以往“機構一合并,人就開始分流”的做法不同,這次中央黨校設立了三年左右的過渡期。按照常務副校長何毅亭的說法,在三年過渡期內不搞一刀切,要科學配置,加長板凳,逐步消化。
三、杜絕“圈子”,肅清“流毒”
人雖沒有立即分流,但是否能迅速融入新的機構,也是檢驗改革成果的一把尺子。據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研究員任永安介紹,國務院法制辦和司法部合并后,一些原法制辦干部到司法部上班,心理上會有些不好受,“但融入進去后,發現司法系統有警銜,還有具體司法行動的補貼,福利待遇比過去有提高,心態上就好了很多”。
本輪改革中,由多部門整合而成的新機構,都面臨多支干部隊伍如何融合的問題,尤其是中層干部。據了解到,大部分重組的部委均采取重新洗牌的方式任免中層干部,讓原來分屬不同機構的人員交叉任職,力圖打破舊有的隔閡,通過人員融合加快推動業務融合和文化融合。
據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許耀桐觀察,“干部任用會避免因以某一機構為主而導致的一家獨大現象,杜絕小圈子”。2018年9月,自然資源部在內部明確提出,要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堅決杜絕國土圈、海洋圈、測繪圈、地質圈等圈子文化。董祚繼說:“部管局在過去被戲稱為‘不管局,就是說部委很難真正對下屬局發揮領導作用。本輪機構改革后,部委對其管理的國家局的宏觀指導和政策協同在增強。”
四、“隱層面”未盡之事
長期以來,中國的改革掣肘于壟斷利益、部門利益糾葛,未來任務依然艱巨。此輪機構改革后,一些突出問題仍然存在,有些部委承擔關鍵性輔助和技術支持職能的事業單位,并沒有隨內設機構劃轉到新機構。
過去規劃的編制環節均是按不成文的管理進行,無明文規定,帶來的問題是規劃的隨意性較大,政出多門。通過本輪機構改革,規劃與建設分離,落實多規合一后,減少了規劃數量,但全國統一的空間管制性規劃如何制定,在自然資源部內部仍存有分歧。
“原發改委、住建、國土等不同部門對具體規劃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新部門組建后,從熟悉業務到真正管好,會有一個較長的過程。”董祚繼說。
改革后,市場監管總局同樣面臨新的融合問題,名義上是大部,但內設業務機構仍保持相對獨立運行,以市場監管總局新聞宣傳業務為例,原質檢總局和原工商總局新聞辦的干部,現在仍各自負責原來業務的宣傳工作。
融合難題之外,一些新領域還存在多頭管理的問題。2018年12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了外商投資法草案,對于外商投資管理,規定了多個部門和多個層次。在商務部研究院外資研究所所長馬宇看來,外商投資管理的核心是市場準入,從國際通行做法來看,都由一個機構來管理外商投資,但目前我國的商務主管部門和投資主管部門均參與其中。
“現在對機構改革成效得失的討論還不夠。”有受訪專家表示,“成效得失應該公開討論,聽取各界不同聲音,吸收具體行業和地方執行層面的改革經驗,真正的改革應該兼有各種視角。”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