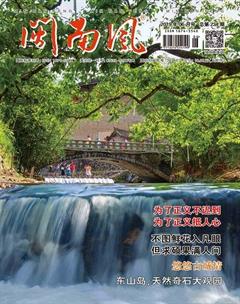回憶父親
郭勝堅

又是一年清明節,給父親上完墳回來,我的心里帶著一種酸楚,父親離開我們已經八個年頭了,可我一直覺得他還在身旁。
獨自一人在書房的窗臺上沖了一壺武夷雙韻,擺了兩個杯子,一個給自己,一個放對面,這是給父親沏的上好的武夷巖茶,猶如他就坐在對面,像往年那樣父子倆對坐。午后的陽光斜灑在窗臺上,溫暖靜謐,茶香氤氳。父親一生勤儉,生前沒喝過這么好的茶。
有一種幸福,就是每個孩子都管自己的父親叫“爸爸”,可我不能。從我懂事到父親離世,我從沒叫過他一聲“爸”,我得叫他“叔”,為了區別于其他叔叔,我叫父親“阿叔”的“阿”的發音又不同于一般的“阿”,而是類似于普通話里面的輕聲。小時候我經常因為這個與眾不同的叫法跟母親鬧,長大后母親才告訴我,因為算命的說我們父子緣淺,怕養不活我,所以我只能偏叫。
我家祖輩算是出了幾個讀書人,太爺爺是清末的秀才,據說當年中秀才時才13歲,報子來報喜的時候,他還光著屁股在家門口的池塘里和小伙伴們戲水呢!太爺爺是一位醫德高尚,醫術精湛的醫生,聽奶奶說,以前村里人要進我家大門還得換上長衫,以示尊重。叔公是民國時鄉國立小學的第一任校長,伯父當過民國時的保長,建國后全國上下掀起一場轟轟烈烈的“土改”運動,奶奶擔心我們家被劃成地主富農,便讓十七歲的父親虛報了一歲,報名參軍去了。
父親年輕的時候長得眉清目秀,穿上軍裝,一副英姿颯爽的模樣,部隊首長很是喜歡他,把父親安排在文工團,可是父親性格內向,木訥寡言,識字又不多,還操著一口典型的閩南地瓜腔,根本不適合當演員,讓他去樂隊,可是不管是弦樂器樂還是管樂,他都搗鼓不來。后來部隊首長無奈只好把他送去汽車連,不曾想父親卻是一個開車的好把式,沒幾天就輕車熟路了,直至從部隊復員,父親成了當時海澄縣第一汽車運輸隊的司機,運輸隊的第一輛汽車“福建牌”便是父親從福州開回來的,此后,父親在四十多年的駕駛生涯中創下了安全行駛一百多萬公里的記錄。
父親是當年村子里第一個在縣城“吃頭路”的人,一個月工資只有5元,家里的生活主要還是靠母親做裁縫和養豬維持。但是,比起周圍的人,我們的生活還是比別人優越,父母也常常會省吃儉用接濟左鄰右舍。海澄縣離家有十幾公里,父親是個嚴守規矩的人,絕不肯私用公車,上班基本靠走路,很不方便。父親通常一個月左右才回來一次,每次回來都會帶回很多好吃的東西,餅干、罐頭,還有鯊魚、黃花魚、白帶魚等各種海產品,最難忘的是過年時買回來的“石馬”牌臘腸,用油一炸,那個香氣把堂兄弟姐妹全都吸引了過來,見者有份,母親便會每人分一小段,大家都攥在手里,饞了就聞一聞,誰都舍不得先吃掉,這在當時都是極其罕見的東西,在那個物質缺乏的年代,盼望父親回來便是我們一家最期待的事了。
等待的日子總是漫長的,那時候沒通電,有月的夜晚,我們便會湊在長輩堆里,聚在家門前的大埕上搓草繩。搓一條草繩可以賣2分錢,織一條草袋1毛1,大概是裝化肥或者裝砂石筑河堤用的,這是父親接回來的活,讓村里人農忙之余可以掙點錢貼補家用。
兒時記憶中父親高大魁梧,不茍言笑,有一種軍人的威嚴。當月亮高高升起的時候,便會看到一個高大的身影從清冷的月光下走過來,那就是父親回來了。我們都會屏住呼吸,連話都不敢說,連原本有說有笑地搓草繩的嬸婆叔伯也都安靜了下來,大家都依據自己的輩分跟父親打招呼,而父親通常只是“嗯”一聲。
父親是個大孝子,一回來便把帶回來一大堆東西提到奶奶的房間,讓奶奶檢視后,挑下她喜歡的東西,剩下的才帶回我們的房間。
每次父親回家我們仨兄妹既興奮又緊張,既期待又害怕,尤其是哥哥,那時哥哥已經上小學了,父親便要檢查他的功課,而偏偏哥哥又不大會讀書,遇到不會讀的字,他就有邊讀邊,沒邊讀上下,或者干脆直接跳過去,起初父親還會幫他糾正,要是錯得太多了抓起來直接就是一頓臭打,氣得實在不行,父親就把哥哥的課本撕了,然后第二天再重新買一本,如此周而復始,一直延續到哥哥上完初中。每次母親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勸,父親就轉而把氣發在母親身上,怪她寵孩子,不會教孩子,母親就哭,有時也發狠話,孩子不會讀就是不會讀,你打死他也沒用,你每次回來都打孩子,你干脆就不要回來了,于是父親就氣沖沖的又上班去了。
我略會讀書,父親不曾因為功課打我。可我淘氣,這是父親的大忌,他常說一句話:一粒粟要做種也要曬干。他認為“男憂女笑”,男孩子應該安靜沉穩方能成大事,可我偏偏不是個成大事的料,我生性好玩,愛打架,天不怕地不怕,除了怕父親。
有月的夜晚,我們一大群野孩子就在曬谷場上玩各種游戲,“救國”、“過五關”、老鷹捉小雞、跳格子、跳皮筋,最考驗人膽量的游戲是“匿啌找”(閩南話,即捉迷藏)。幾個孩子,通過翻手掌(抦黑抦白)確定一個要找人的孩子當瞽雞(瞽:瞎眼),領頭的孩子用雙手捂住他的眼睛,其余的孩子充當白蛋就各自找黑暗的角落躲起來,然后頭兒就念:掩瞽雞,走白蛋,一句嗄,一句問,放瞽雞兒去找蛋。那個當瞽雞的孩子就往黑暗的角落里逐個尋找,膽大的孩子什么地方都敢藏,有一回有個同伴竟然藏到我奶奶陪嫁的那副棺材里,那可是對奶奶的大不敬,后來不知道是誰說出來,那個傻蛋被他娘臭打了一頓。但是父親回來時我就不敢出去玩了,父親打人太兇了,這個我領教過。
小時候,經常有“做鳳陽”的來村子里打拳賣膏藥,那是走江湖的人討生活的一種方式,鳳陽師到各個村子里巡回,或變魔術,或表演武術、氣功,或唱些類似東北二人轉的段子,也有耍猴或者耍眼鏡蛇的。小孩子最高興的不僅是可以看熱鬧,還可以跟父母要一點零錢買零食吃。有一回鄰村做鳳陽,我征得母親同意后跟同村四個小伙伴一起去看,不料父親突然回來了,碰巧被他看到,正在跟其他小伙伴有說有笑的我,突然被一雙大手從后腰提起來,我起初還以為是哪個小伙伴捉弄我,我還說了一句:“怪小”,別開玩笑。可憐我被父親直接舉過頭頂,就像戲臺上要抓陳世美去斬頭的那幕一樣,我被父親拎回家,直接摔到地上,劈頭蓋臉就是一頓狠揍,那個晚上,母親自己一個人哭到天亮。
在父親威嚴的注視下我漸漸長大了,父親不會再打我了,可我心里仍然怕,還不僅僅是怕,有什么話我也不會找他說,甚至見面都不會跟他打招呼。后來我考上了師范,離開家的我就像一只出籠的小鳥,覺得自己從此可以過上無拘無束的生活了。可我還是沒能離開父親的視線,每個月父親都會騎著腳踏車趕十幾公里路到學校給我送生活費,每次見面,父親都會交代我要認真學習,不要亂花錢,每次我都是“嗯”幾聲就走,只有沒生活費了我才會回家,回家我也只跟母親要。
畢業后我回到家鄉工作,離家不遠卻經常住在學校,偶爾回家也極少跟父親說話,父親每次見我回來,不是高興,而是一番盤問,好像我逃學翹課似的。
2002年,我調到縣城工作。依母親心意,每年除夕我都攜家帶口回老家圍爐。這一年除夕,圍爐時感覺平時吃東西很快的父親沒怎么吃,我瞄了他一眼,發現父親清瘦了很多。過了正月初五,母親才跟我說,父親最近總吃不下東西,還老是噯氣,叫我帶他去醫院瞧瞧。到縣第二醫院做了胃鏡檢查,醫生懷疑父親可能得了胃癌,建議到市立醫院做進一步檢查,我一聽就懵了,我不相信父親會得這種病,一向高大健朗,像永遠使不完勁的父親怎么會得病呢?他不是還隔三岔五地從村里的那口老井打水,帶上母親自己種的菜,騎著那輛騎了三十多年的老爺車趕四五公里路送到鎮上給我;我跟生產隊承包了一百多畝山地,準備開荒種果的時候,他不是二話不說就扛起鋤頭挑上水桶,跟我上山干活了,甚至一天最多能挑76擔水,也從不喊累;他不是為了省車費還能騎著他的老爺車石碼浮宮來回跑,每當楊梅、蓮霧收獲的季節他還能載著一筐筐的水果親朋好友一家一家的送,就算熱得滿頭大汗,也樂此不疲。父親怎么突然就得了這么嚴重的病呢?我一時感覺父親就要離我而去,可他還沒享受過一天清福啊,難道就這樣任由疾病奪去他的生命?此時,我才感覺到,其實父親并非離我那么遠,雖然我從沒叫過他一聲“爸”。
我不敢讓父親知道,也不敢跟母親說。我找了個借口把父親送到市醫院辦了住院,最后父親被確診為胃癌晚期,并已浸潤到食管中下段,醫生建議必須馬上做手術,我還是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卻必須面對這么殘酷的現實。醫生說如果不手術,父親的食管馬上就堵住了,到時滴水不進,只能靠輸液和止痛藥維持,最多活不過半年,快則一兩個月;但是如果手術要花一大筆錢,手術費及后續的各種治療費用得一二十萬,且手術不能保證一定成功,有的甚至是上了手術臺,就回不來了。
我只能回家跟母親商量,母親也不敢決斷,請來了舅舅、大哥和幾個堂哥開了個會,大家一致反對給父親做手術,都說父親已經68歲了,手術又不一定成功,沒必要冒這個風險;另外,手術費用太大,父親又沒什么積蓄,我一個月四百多塊的工資是承擔不起的,父親的幾位好友也不贊成手術。
母親聽了傷心欲絕,她說我們不能這樣眼睜睜看著你父親痛苦地走了吧,他可還沒享過一天福啊!
是啊,父親雖然嚴厲得幾乎不近人情,可他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安分守己,認真讀書。父親一輩子勤勤儉儉,唯一的裝備那輛老爺車還是自己省吃儉用買零件組裝的,他身上穿的除了部隊的軍裝和單位發的勞動服,就是母親過年給他做的中山裝,他從沒趕過時髦,一提起給他買新衣服,他就不高興。他不僅培養我們仨兄妹讀書,還蓋了兩座平房改善我們的居住環境,這期間付出的辛苦,做兒女的怎能忽視。我理解母親的心意,我跟母親說,錢我來想辦法,不管結局如何,只要有一線希望,我們也要爭取。
父親手術很成功,又和我們一起度過了8年的幸福時光,很多人都認為是奇跡,雖然這8年我帶著父親四處求醫問藥,每年都要做各種檢查,吃很多藥,但我們的付出是值得的。父親還是時常騎著那輛被我戲稱為“羅馬牌”的腳踏車,載著時令蔬果,自家養的雞鴨鵝蛋,興沖沖地來縣城看我們,有一回我們加班,剛10歲的兒子放了學,知道爺爺胃不好,不能吃干飯,竟然懂得請他爺爺去吃“真粥道”,父親樂壞了,回到村子里逢人就夸,說那是他吃過的最好吃的一餐。一有時間我就帶父親四處逛逛,走走親戚,父親性格變了很多,變得不再急躁,也喜歡笑了。
2011年的春天,父親還是離開了我們,他走的時候很安詳。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父親走了,這世上從此少了那個我應該叫他“爸”的人了,縱然有再多的美食和歡樂也無法與他分享了。有時,我也常想,如果我小時候,他們不那么相信算命的,不讓我偏叫,不這樣暗示我們父子緣淺,我和父親興許就沒有了之前的那么多隔閡,那應該是另一種生活場景吧。
閩南老話說:爸死路遠,母死路斷。如今母親已85歲高齡,我常伴母親左右,帶她求醫問藥,噓寒問暖,寬心解悶,共享天倫,所幸兒子也懂事,對他奶奶十分孝順,二十多歲了還會和奶奶同睡一鋪床照顧她,這種血脈相承的親情必定緣深,哪會緣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