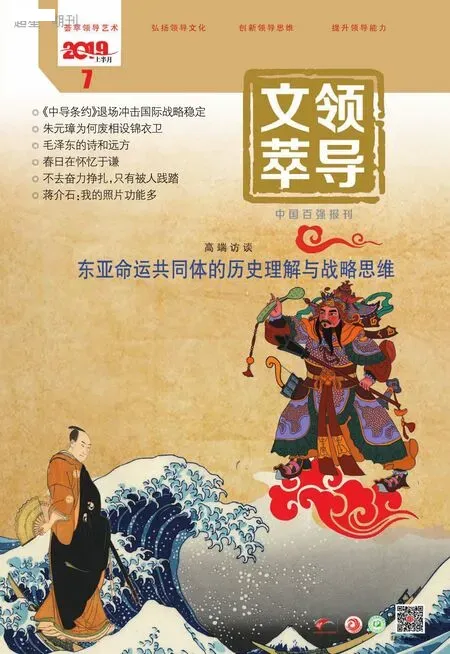春日在懷憶于謙
張亞萌

何謂英雄?挽狂瀾于既倒,摧敵鋒于正銳,敢為人之所不敢為,敢當人之所不敢當,可以算英雄。北京保衛戰,是于謙一生中的華彩篇章。
誰言書生百無用,鐵骨丹心鑄昆侖——書生上陣,亦有“烈火焚燒若等閑”的瀟灑氣度。有人說,若非你以文弱書生之肩扛起一國存亡,有明一代的歷史恐要重新寫下,而北京或許早已“淚盡胡塵”,成為又一個北宋開封。歷史上,漢族王朝君主被外族俘去不是個例,但無條件被釋放僅有此次。一如當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中所寫的,在北京保衛戰中,你,完成的是一個在絕境下始終堅持信念的奇跡。
粉身碎骨全不怕
于謙能夠戰勝入侵的外敵,卻不能戰勝內部的對手——土木堡之變使他成為舉國擁戴的英雄,奪門之變又會使他因“謀逆之罪”而喪命。
“將軍不解避鋒芒”,你在詩作《過韓信冢》中這樣寫淮陰侯,而你自己又何嘗懂得“避鋒芒”?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友人曾勸于謙“安逸”,答曰“嘗疏請骸骨,奈不放何?只是一腔血報朝廷耳。”《明史》有言,“謙性故剛,遇事不如意,輒拊膺嘆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視諸選耎大臣、勛舊貴戚意頗輕之,憤者益眾。”你的處事方式直來直去,不加掩飾,同僚的“不樂謙”“齒謙”遍布史書,這如同阮小七一般的暴烈、熱血與婉轉不足,是你引來殺身之禍的重要誘因,過于剛直的風光霽月對政治家而言是一種“致命傷”,是足以斷送政治前途的“人格缺陷”,故而《明實錄》載:于謙“恃才自用,矜己傲物,視勛舊國戚若嬰稚,士類無當其意者,是以事機陰發,卒得奇禍。”
同時,你與朱祁鎮及太子見深、朱祁鈺及太子見濟這“一仆四主”的復雜關系,讓你左右不是、前后為難,易主易儲,不暇兩全,再次陷入了明代最麻煩也最危險的皇室權力斗爭中。
因此你必須死。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五,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兵部尚書于謙會同群臣商議,一起上奏病重的朱祁鈺復立沂王見深為太子。眾人推舉商輅主草奏疏,疏成后已日暮西山,來不及上奏,遂決定次日清晨再遞。
遲了幾個時辰,就改變了明代歷史,也改變了許多人的一生。正月十六日凌晨,夜四鼓,武清侯石亨、副都御使徐有貞、太監曹吉祥等潛入位于今南池子大街緞庫胡同內、現已不存的南宮,擁立被軟禁七年之久的太上皇朱祁鎮復辟。
朱祁鎮完成了由皇帝到俘虜、從俘虜到囚徒又變成皇帝的傳奇轉變——改年號為天順,并在復位當天以“更立東宮、迎立外藩”為名傳旨逮捕于謙;十九日令三法司會同九卿從速審清。二十日,大理寺會審,逼供未遂,于謙身遭酷刑,被扣上“意欲迎立外藩、圖危社稷”之罪名。
其實,奪門之變的詭異之處在于,兵權在握的你蕩平此亂本是輕而易舉,而你為何按兵不動?后人猜測,面對新舊兩位皇帝,事變中表現得近乎遲鈍的你,早已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但我更相信談遷在《國榷》中記述屠隆所言:“奪門之役,徐石密謀,左右悉知,而報以謙。時重兵在握,滅徐石如摧枯拉朽耳……謙顧念身一舉事,家門可保,而兩主勢不俱全;身死則禍止一身,而兩主亡恙。……以一死保全社稷者也”:一旦作為兵部尚書的自己有所行動,朱祁鎮必獲謀逆之罪,他的子孫將都是罪人之子,宣宗朱瞻基一脈將永失皇權。朱祁鈺已然不久于人世,迎立其他藩王又必致國勢動蕩,所以你才選擇在西裱褙胡同舊居“屹不為動,聽英宗復辟”,一如你曾選擇的“立鈺為帝,朱見深為太子”,對社稷而言都是最佳選擇。
“粉身碎骨全不怕”,你猶如一條魚,撲向那張早已可見的漁網。天順元年正月二十二(1457年2月16日),你的人生以極其悲壯的方式謝幕——成功保全社稷后遭枉殺。
有人說,于謙之冤死,主于英宗之心,出于佞臣之謀,行于群小之誣,裁于污吏之手,真乃“此一腔血,竟灑何地”!
《明史》載:“死之日,陰霾四合,天下冤之。”
要留清白在人間
“勇猛圖敵,敵必仇;振刷立功,眾必忌。況任勞之心任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勞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謗書盈篋,毀言日至,從古已然”,于謙死后又169年,袁崇煥寫下這照映他們二人相似命運的血淚文字。《菜根譚》亦言:“淡泊之士,必為濃艷者所疑;檢飾之人,多為放肆者所忌。君子處此,固不可少變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鋒芒。”
以《菜根譚》的標準而言,你似乎并非“君子”,而只是一個有勇氣亦書生氣十足的“人”。景泰元年始,你多次請辭總督軍務,亦想辭掉兵部尚書之職,徹底辭官回鄉,這種無可奈何的苦悶心態展現在《自嘆》詩中:“逢人只說還家好,垂老方知濟世難。戀戀西湖舊風月,六橋三塔夢中看。”讀來令人心痛——你殺伐決斷于疆場,卻折戟沉沙于廟堂,成為“明代皇位之爭最無意義者”的鬧劇犧牲品。學者左東嶺認為,這一切源于“奪門”,“奪門”源于土木堡之變,土木堡之變源于王振專權,而王振專權則源于仁宣時期之士風疲軟——彼時“三楊”等閣臣與皇帝的關系中師生情感占有相當比重,隨著仁宣二帝逝去,此種情感已不復存在;士人在失去了與皇帝的情感紐帶之后,逐漸也失去了駕馭朝政的能力。明朝政治成為一種無序的專制政治,強者即權力中心的特性既成就了你拯救國家于危亡的偉業,亦會導致殺身成仁的結局。
“英宗復辟以后,被殺者不止于一于少保,而于少保之因忠被讒,尤為可痛。”作家蔡東藩嘗言。盡管起決定作用的也許是“性格缺陷”,但于少保的死,有冤而無憾——作為傳統儒家人臣,能死為社稷是人生的圓滿。
你的入世、進取與擔當,讓我想到脂硯齋對賈探春的脂批:“看得透,拿得定,說得出,辦得來,是有才干者。”——有“志”,是能夠構成推動世界向前的力量。而你又何嘗不是如此?哪怕你有你的“性格缺陷”,你仍是一個擔當得起有守有為而“不識時務”的“人”。做社稷之忠臣,結社稷之正局,此非豪杰之勇,實乃大賢之仁。重名節,輕名利;重成仁,輕殺身;重社稷,輕君王,正是這身居高位而“不識時務”,成就了中國歷史上的一次次絕地反擊,這是中國士人千年以降的傳統——雖千萬人,吾往矣。
你曾寫過一首懷念岳飛的詩《岳忠武王祠》:“中興諸將誰降敵,負國奸臣主議和。黃葉古祠寒雨積,青山荒冢白云多。”這幾乎成為你自己的讖語:岳飛死于“莫須有”,而你死于徐有貞“不殺于謙,此舉(奪門)為無名”的“意欲”。意欲豈殊三字獄,英雄遺恨總相同。死后你與岳飛同棲魂于西湖的春水晴云之間,一如袁枚所說,“賴有岳于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
《帝京景物略》說,于謙“被刑西市也,為天順二年。九年復官,為成化二年。又二十二年,賜謚肅愍,為弘治三年。又一百一年,改謚忠肅,為萬歷十八年。凡百有三十三年而論定。”成化二年(1466年)充軍戍邊的兒子于冕與女婿朱驥被放還鄉,發還家產——于冕充軍龍門,則成為《龍門客棧》故事的原型,不過,那是后話了。
你曾作詩《北風吹》,中有“樹堅不怕風吹動,節操棱棱還自持。冰霜歷盡心不移,況復陽和景漸宜”之句,昭示了哪怕身處無序的世界,也始終做一個擔當有為之人的“志”,“要留清白在人間”。那陽和之景,就像作家林太乙所說的:“光陰荏苒,奪不去在懷的春日。”——春日在懷,而我只想說:你是人生的模板。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