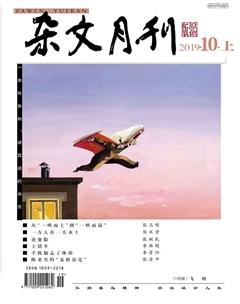“三問他人”與“三省吾身”
李崇和
與“三省吾身”指每日多次反省自己意思相似,本文所說“三問他人”,也是取每天喜問他人(仕途、財運等)的意思。
經常遇到“三問他人”之事,近日就遇到一起。暑期一個周末,朋友為慶祝孩子高考金榜題名,置辦便宴數桌,請朋友同事老師同賀。我被安排與師者同桌。入座不久,一位老師便急不可耐,詢問同桌一個官場朋友:“現在當多大官了?”據我所知,同桌幾位由教師改行當官的主兒,均官運不通仕途平平。尤其是被問之人,曾經仕途一度看好,后多年原地踏步,所問顯然讓對方尷尬,羞于回答,其他人也不便應聲。一番酒酣耳熱后,這位師者仍然不肯罷休,又數次詢問朋友官至何方何位。出于對老師尊重,其問均被席友虛與委蛇岔開話題。類似哪壺不開提哪壺,莫名其妙的“三問他人”,往輕處說,是自討沒趣;往重處說,則有辱師道。
世上沒有人不要求進步,也沒有人不追求成功;然而,每個人“進步”和“成功”標準相異。師者何以三番五次問朋友官至何方何位?顯然,在他觀念中,官級便是衡量“進步”“成功”的首要標準,甚或唯一標準。殊不知,人各有志,“三觀”有別。僅拿佳途“官念”說事,有人信“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為圭臬;有人以“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為愿景;有人定“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為座右銘……退一萬步說,就算將官位大小當成度量“進步”“成功”的標準,也不可藉此計量人生價值意義的大小。因為,尷尬現實是,官位大小與個人才能努力并不必然成正比;相反,人們所見不少官運亨通者,并非靠個人才能努力,而是靠投機鉆營的歪門邪道,抑或“朝中有人”的旁門左道。

其實,“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人生本應適時轉型。無論你從事何種職業,對年近知天命的吾輩而言,職場“出息”的時空概率已然不多。仍舊舉仕途說事,雖不說“船到碼頭車到站”,但吾輩面臨“退休嫌早,提拔嫌老”尷尬年齡,卻是不爭事實。可見,以平常心對待仕途,不僅是職場規則使然,更是人生定律使然。上述那位師者慕戀官場,老師關心學生前途,多年未見問幾句以示關心未嘗不可;然而,反復詢問則讓人難堪,雖不至于讓人揶揄討嫌,但也顯得其官本位思想太重,官念太舊。換言之,其既在認知上有失偏頗,又在定位上不合時宜。當然,平常心不是說“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而是指以理性平和心態,走好走穩走完職場余途。
自然,平常心還包含,到了歸于平靜的年齡,老友見面問問健康狀況,每天跑步多少,有何興趣愛好,父母身體怎樣,叮囑常回家看看,問問孩子學業工作。因為,除了職場發展,個人身體,孩子未來,家庭幸福,都是人生“進步”“成功”的題內之義。假如師者非要“三問他人”的話,不妨問健康不問官職,問父母子女不問張三李四,問心情興趣不問做官發財。如此這般,理性平和,皆大歡喜,何樂而不為?
曾任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的北大才女盧新寧,在一次北大中文系畢業典禮致辭中說:“我唯一的害怕,是你們已經不相信了———不相信規則能戰勝潛規則,不相信學場有別于官場,不相信學術不等于權術,不相信風骨遠勝于媚骨。你們或許不相信了,因為追求級別的越來越多,追求真理的越來越少;講待遇的越來越多,講理想的越來越少;大官越來越多,大師越來越少。”何以至此?顯然,亟待國人“三省吾身”,而非“三問他人”。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意思是說,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別人做事有沒有盡心竭力?和朋友交往有沒有誠信?老師傳授的知識有沒有按時溫習?每天多次反省自己,這是圣人做的事,容易引發失眠,常人也許做不到。但每隔一段時間,沉靜下來反省一下自己,過濾沉淀一下自己,尋回迷失的本真,是可以做做的。假若“三省吾身”一時半會尚有點困難的話,別“三問他人”討人嫌,還是必要和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