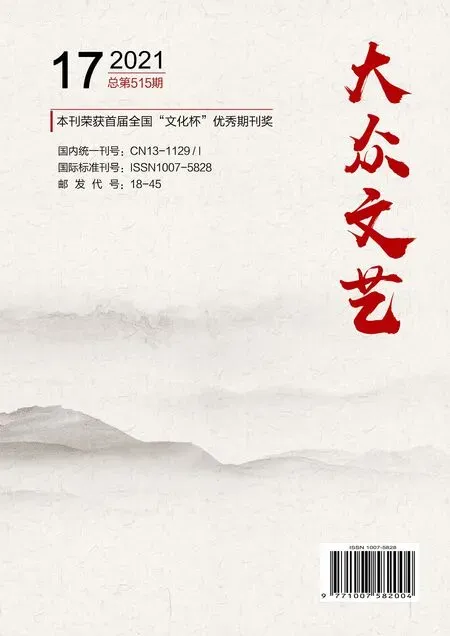“花”之隱喻,“歌”之表達
——評《怒江中游地區傈僳族民歌傳承研究》
(廣西藝術學院藝術研究院民族藝術研究所 530000)
隨著近年來我國“非遺”保護工作的開展,傳統音樂受到來自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在眾多的傳統音樂品類中,民歌不僅地位重要,所占比重也相當之大。最近筆者閱讀到一本書——《怒江中游地區傈僳族民歌傳承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9月版,下文簡稱“羅著”),此書闡釋民歌這一活態民俗文化在傈僳族日常生活中的具體運演模式與功能,探討民歌傳承運作模式及其傳承變化特征,剖析在一種集體民歌音樂文化的傳承模式中集體觀念和個體歌者表達對變遷的影響,及就個體選擇對于群體性民俗之重要價值進行反思。
倘若將民歌這一音樂事象比喻為音樂百花園中一株鮮花。花香是傈僳族民歌中傳承主體的象征,只有花香不斷飄散,民歌才得以延續傳承;花枝是傈僳族民歌中生態語境與文化傳統現狀的表征,只有保護好傳統語境,才能讓花枝根深蒂固;花簇象征著傈僳族民歌中歌者的生存面貌,只有歌者受到關注并得以保護,花簇才能更為繁榮茂盛。縱觀羅著全書,結合“花”之隱喻,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對其進行評述:
一、花香縈繞:以怒江傈僳族民歌傳承為研究主線
全書內容結構為總—分—總形式,設計的內容范圍是以民歌傳承為主線,逐步從不同傳承形式等方面解讀這一主線,每一章節又以清晰的脈絡呈現出來,從而引領讀者有一個明確的邏輯結構去閱讀。例如第六章“全球化地方性文化中民歌傳承”,分為“全球化對民歌傳承的影響”“地方性構建與民歌傳承”“傳統民歌之現代傳承”三個部分,其目的是為了用來闡明“民歌傳承”這一主題。
縱觀學術界,民歌研究成果主要側重在民歌音樂本體研究和文學研究,盡管民族音樂學、民俗學等學科對民歌的研究有豐碩成果,但將民歌傳承放置于文化整體中考察其活態延續的歷程以及對傳承主體的關注目前涉及較少。值得肯定的是,羅著中正是以“民歌傳承”為研究中心,將怒江傈僳族民歌傳承方式、模式及現狀貫穿于書中每一篇幅。例如書中第三章“怒江傈僳族的歌唱傳統與歌唱”之“傈僳族村落實錄”中,作者敘述怒江族自治州瀘水縣與福貢縣三個村落不同民歌的存在狀態,解讀其歌唱傳統與歌唱生活之密切關系的同時又詮釋當地傳承主體與傳承現狀存在問題。綜上可知,傳承主體在民歌承續中雖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若作者再論述傳承主體在傈僳族的社會構成、族群認同等方面如何推動和體現其社會功能與價值問題,則更具現實意義。
二、花枝根植:以賴斯三角體系對傈僳族民歌的立體闡釋
著名民族音樂學家蒂莫西?賴斯(Timothy Rice)所創建的“歷史構成—社會維護—個人創造和經驗”研究模式,標志著民族音樂學在方法論上的一次“質”的飛躍。在我國民族音樂學界,賴斯的三維立體研究方法已經成為田野調查與案頭工作的經典模式。賴斯認為,在音樂形成過程中,社會、歷史、個人三個部分的作用是雙向與互為建構的,即歷史構成能夠被社會維持的格局和個人創造的決策所解釋。
羅著以怒江傈僳族民歌作為民俗案例進行探究,是一本以民俗學視角描述怒江傈僳族民歌的學術專著。羅著除以民俗學理論為全書理論基礎外,還引用民族音樂學領域中賴斯有關音樂研究“社會—歷史—個人”的立體三角理論作為研究視角,對傈僳族民歌傳承主體與民俗生活的相互建構進行呈現。通過賴斯的三角體系理論,我們可以較為清晰地捕捉作者的思考邏輯:在歷史構成角度,從完成對傈僳族民歌傳統的歷史重構的同時,也關注建構中的民歌傳承變遷與發展;在個人體驗和創造的角度,主要關注傳承中由于個體間觀察問題和把握問題能力方面的差異,以及個體在民歌傳承中的角色建構;在社會維持角度,基督教文化的浸入、多元文化理念下國家力量的介入等變量構筑成不同歷史時期特定的社會和信仰體系,并與民歌傳承相互作用。
三、花簇綻放:從民歌歌者角度展開傈僳族民歌話語體系表達
話語體系實質上是思想的外溢形式,正如馬克思指出,語言是“思維本身的要素,是思想生命表現的要素”,是“思想的直接現實”。因此,話語體系的吸引力直接決定其所承載和闡述思想的吸引力。在傈僳族民歌傳統話語體系表達中,歌者在維系自身與集體的良好傳承氛圍同時,也在努力訴求和表達自身個體話語。羅著里提及的傈僳族民歌傳統語境中“個人體驗和創造”即為群體中的個體對民歌傳統的感悟和民歌實踐,個體一直與其所處的生活互為建構,努力實現著表達自我和慰藉自我的愿景。
以往的民歌研究中,在考慮人與民歌之間關系時主要關注以族群為對象的群體考察,甚少涉及民歌傳承中歌者的個人生活經歷和內心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研究具有宏觀話語特征,往往從大的范域著手,卻缺少對傳承人的關注與保護。盡管對傳承人個體給予越來越多的關注,絕大多數對傳承人的研究也僅停留在對這一社會身份的強化和認定上,缺少對其生活身份的關照。在民歌發展歷史至傳承傳播過程中,以往普遍認為民歌是集體智慧,由集體創作而成,由此便忽視個體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缺少“人文關懷”“以人為本”的傳承觀念。羅著將傈僳族民歌傳承主體放置于傈僳族民歌傳承語境之中,結合其在現代化趨勢和地方性文化建構中如何實現群體互動與個體話語表達這一關鍵問題,在側重于個體深描的同時,也突出群體與個體的之間的聯結關系。
四、小結
回想該書對筆者的啟發,除對傈僳族民歌有更深入的理解外,最寶貴的莫過于在當代語境下,如何解讀少數民族民歌文化的發展樣態并就其傳承研究展開思辨性學理剖析。讀罷全書,既有收獲也有思考,以下就不足之處展開探討:
(一)譜例與形態分析有待增添
民歌的本體形態是其音樂身份的標識,對其音樂形態展開描述分析即是解讀其音樂獨特性和地域性的津梁。羅著主要以民俗藝術學為研究視角,借鑒民族音樂學家賴斯的三角體系理論方法,體現學科間的相互借鑒。筆者認為,羅著既然引用民族音樂學理論方法,亦可增加音樂形態分析的內容。倘若能在對傈僳族民歌曲調、唱詞等進行記譜后,再進行音樂形態層面的分析,解讀其音樂本體概貌,并拓展分析不同歌者或同一歌者在不同時期的歌唱行為,則不僅更好呈現傈僳族傳統民歌的地域性特點,也呼應了民歌音樂與區域文化相結合的重要性,使研究更具立體感和全面性。
(二)章節內容不夠平衡
翻閱羅著目錄,不難發現,各章篇幅存在內容不平衡的問題。如正文部分第二、三、六章分三節,而第四、五章僅設兩節而已。筆者認為,每一章在篇幅安排上應保持平衡,這不僅是為全書結構的完整美觀,也為通過充實的篇幅盡可能解決和論述每一章待討論的內容。就書中第四、五章篇幅設計上的缺陷,筆者在此提出以下不成熟建議。如第四章為“民歌歌唱傳統與傳承”之“怒江中游地區的傈僳族民歌傳承”與“民歌傳承與歌唱系統生成”。既然作者談到民歌傳統與民歌傳承方式各自在傈僳族群生態中呈現的樣貌和變遷,筆者建議,可再增設一節,進一步解釋民歌傳統與民歌傳承方式間是如何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的關系。
(三)尚未提出可操作性的傳承保護措施
不可否認羅著對傈僳族民歌傳承現狀問題進行較為系統的描述與分析,但值得思考的是,作者雖對民歌傳承進行了現狀分析,但未就這些現狀背后顯現的問題提出可持續發展的保護建議。筆者認為,作者應在現代社會語境下,就怒江傈僳族民歌傳承發展中的現狀和問題,提出可操作性的措施。例如建立怒江傈僳族民歌數據庫,對傳承人信息、民歌音響、影像資料等進行整理收集;自2015年以來,我國網絡直播平臺興起,利用網絡直播推廣并通過解說民歌傳統,可與觀眾拉近距離,也能更好地適應當代年輕人的生活方式與審美趣味,促進傈僳族民歌在當代全球化時空語境中的傳承與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