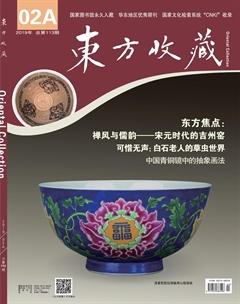貴貴琳瑯游牧人



蒙古、回部與西藏位于亞洲內陸,多為高原和盆地的地形,緯度高、地勢高,氣候寒冷,雨量不穩定,除了河谷、綠洲之外,以游牧經濟為主,其住民多元,蒙古族、維吾爾族及藏族占多數,在地理、宗教與歷史上,均與以農業經濟為生的漢族有很大的差異,形成特有的游牧文化與藝術。
十七世紀起于中國東北的滿人逐步向西及向南擴張,建立大清王朝。作為統治者,滿族從未改變成為北方草原民族共同盟主的企圖,并積極掌控西南方青藏高原的藏族。除了軍隊戍守和行政治理之外,清朝并透過婚姻、宗教和年班等手法,深入統治,維系人心,鞏固政權。
臺北故宮博物院舉辦的“貴貴琳瑯游牧人”特展,以清朝宮廷與蒙古、回部、西藏諸藩部之間往來互動的相關文物為中心,從人類學與物質文化的角度出發,一方面闡釋蒙回藏游牧文化的特質,同時解析文物本身的藝術特色及其所傳達的文化內涵。
尊貴的飲食器用
游牧人因應自然環境條件下的抉擇,同時將自然資源發揮到極致,形成特有的游牧文化。他們依循前人的經驗,隨著季節變化,驅趕著馬、牛、羊等動物,規律地移動。動物是他們衣、食、交通所賴,植物的每一個部分都被善加利用,制成各式用品。居住的是易于拆搭的帳篷,隨身攜帶著飲食器用,無一長物。當其以木碗、刀叉等基本生活用品作為贈禮時,不僅反映其樸質簡實的價值觀,同時木碗等做工的講究,足以說明其工藝技術的純熟。
圖1為金鑲樺皮鳳冠頂飾件。樺樹是北方溫帶常見的樹種,自古以來樺樹皮就被游牧民族充分運用,制成各式用品,用以覆蓋屋舍甚至作為書寫用的紙張。元代貴族婦女頭上戴的罟罟冠也是利用樺樹皮柔韌輕薄的特性,外覆織品,蒙古國家博物館藏元代墓葬出土的稀有樺皮冠頂,配合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元代后妃畫像,可想象樺皮使用的情形。這件樺皮鳳內部以木支架支撐,外覆樺樹皮,再貼飾金箔,鳥冠、翼尾、鳳足與云形底座作金構件,鳳身、鳳尾嵌飾大小珍珠,風格造型均和金累絲鳳鳥相同,是清代宮廷后妃冠頂常見裝飾,非常具有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色。
圖2為木碗附嵌綠松石鐵鋄金盒。木碗是最能反映蒙藏各族飲食習慣的用具,可用來喝茶、抓糣粑、存放食品等,輕便耐用,易于隨身攜帶,盛裝食物不燙手、不變味。木碗一般以樺木、杜鵑樹根或雜木根制成,最貴重的材料則是以寄生植物制作,尤其是寄生在蒿根部的一種瘤(藏語稱為“咱”)。自康熙年間每年初春藏地往往進貢木碗賀年,宮廷中常用以喝奶茶,稱為“奶子碗”,雍正年間仍沿襲此習。《活計文件》記載,噶倫貝子康濟鼐進札布札牙木碗,達賴喇嘛進札固里木碗大小五個。這件木碗附嵌綠松石鐵鋄金盒,材質細致輕巧,絲狀紋理對比分明,用材珍貴,并以鐵鋄金嵌綠松石鏤空圓盒盛裝,為藏地貴族進獻宮廷的珍品。
圖3為鎏金刀叉匙附皮盒、木盒。土爾扈特部是漠西蒙古的一支,十六世紀末逐漸西遷至伏爾加河下游流域一帶游牧,十八世紀后期因俄國沙皇的威脅,長途跋涉東返舊地,得到清朝的安撫與接納,進入伊犂河一帶安居。乾隆三十六年(1771)其首領可汗渥巴錫(1742—1775)等,至熱河避暑山莊見謁清高宗,并曾進獻哈薩克良馬、白鷹等。展出的是渥巴錫轉呈敬獻清高宗的叉匙匕首組,置于一皮匣內,匣蓋四周環繞幾何花卉紋飾,表現俄羅斯洛可可華麗流暢的風格,中央書蒙文二行,清朝宮廷又特制木盒盛裝,并于盒面題銘記錄,說明這組文物的特殊意義。
藏傳佛教的浸潤
由印度佛教與西藏本土宗教“苯教”交融而成的藏傳佛教,十五世紀后逐漸興盛,成為蒙、藏族思想與生活中的一部分,并進而影響滿族的信仰。西藏的寺院不僅是信仰中心,亦為地方經濟與行政重心所在,因此喇嘛或王公等的進呈,無一不是一時之選,而以佛教法器作為獻禮,正與西藏丹書克每每敬稱皇帝為“文殊師利”的關系相應;換個角度來看,清代皇帝對藏傳佛教的禮敬,則清楚表明其對藏傳佛教影響力的高度重視與尊重。
圖4為嘎布拉數珠。念珠又稱為數珠,不論佛教、伊斯蘭教或是天主教都會使用念珠,作為經文誦念、咒語或稱號時輔助修行的用具。這串念珠是六世班禪乾隆四十五年(1780)所呈進,時值乾隆皇帝七十歲壽辰,六世班禪于7月到達熱河避暑山莊,清朝特別依照其駐錫的札什倫布寺修建須彌福壽寺,乾隆皇帝并于8月6日和24日至該寺拈香。1751年清朝冊封七世達賴喇嘛政治權力之后,喇嘛除應定期朝覲,遇皇帝壽辰等亦可不定期進京。六世班禪是清代三位親自進京的大喇嘛之一,這在當時是一件大事。這件念珠以人骨制成,間以蜜蠟、珊瑚佛頭珠,青金石佛頭塔,附以綠松石、水晶、金銀金剛杵記捻,展現十八世紀西藏念珠的莊嚴與殊勝。
圖5為青金石佛缽附皮盒。這件青金石缽色澤鮮艷,造型圓潤,十分莊嚴。盛裝石缽的皮盒蓋內記錄,這是乾隆乙亥年(乾隆二十年,1755)打敗準噶爾部時所得,應該是先前準噶爾部在西藏時得到的用器,己卯(乾隆二十四年,1759)高宗在缽上刻滿、漢、蒙、藏四體文字。蒙古族的準噶爾部在十七世紀興起,以伊犂為首都,亦信奉藏傳佛教。該部曾進入西藏,占有拉薩,統治西藏三年(1717—1720)。乾隆六年(1741)高宗曾賜予蒙古的哲布尊丹巴一件鐵缽(蒙古博克多汗冬宮博物館藏),其樣式和本次展出的“炕老鸛翎鐵缽”相同,“炕老鸛翎”是在鐵上燒烤出藍紫色氧化層的作法,《雍正朝活計文件》多次記載制作炕老鸛翎色匙箸。因此這件青金石缽很可能是著眼于青金石特有的顏色,仿炕老鸛翎鐵缽的造型制作而成。
圖6為銀壇城附五色哈達。這件銀壇城,環系紅藍黃白綠五色絲質哈達,為青海佑寧寺駐京喇嘛六世土觀呼圖克圖(1839-1894)在慈禧太后大壽時所呈進。壇城是佛教世界的象征,壇面滿刻海浪文樣,中央為四層方臺,代表宇宙中心的須彌山,壇城最外圍的圓周上環峙鐵圍山,群山之間的四方位各置一城門代表四大洲。城門上的圓形、三角、月形、方形,分別代表東勝身洲、南贍部洲、西牛貨洲、北俱盧洲,海面上環繞一圈八寶以及四方位的月、聚寶盆、日、滿意牛,藉以供養佛陀。壇城側面外圈上下嵌珊瑚與松石的連珠紋,并飾金剛杵與蓮瓣紋,中央為卷葉紋與八寶間隔為飾,卷葉紋中心亦以珊瑚與松石珠組成十字形飾。紋飾、做工均甚工整,摻雜漢地的風格,表現十九世紀藏地工藝的風貌。
珊瑚與松石的對話
珊瑚和綠松石深受蒙古與藏族的喜愛,常鑲嵌在金、銀器上,或搭配珍珠、蜜蠟,組成色彩鮮艷、碩大豪邁的飾物,每逢盛會佳期,則層層披掛,形成游牧文化獨特的美感。珊瑚來自地中海,松石來自伊朗,價值不菲,足以展現佩戴者的身份與財力。珊瑚、水晶、硨磲等各色寶石,一方面是佛法殊勝的具象化表征;另一方面,苯教自然崇拜的信仰中,稀有寶石往往具有護身符的功能。因此,寶石飾物兼具吉祥、幸運與社會地位的象征,成為蒙藏人美麗的特色。
圖7 為清銀嵌珊瑚松石冠頂。西藏不分性別皆喜以寶石為飾,珊瑚、松石和蜜蠟是最常見的類別。西藏的珊瑚來自地中海,大多經由印度、克什米爾等地進入,至于松石,西藏也有生產,惟色澤偏綠,并有褐色紋理,這件冠頂的松石顏色就較偏綠,可能是西藏本地礦石。冠頂的裝飾往往與身份等級有關。這件冠頂為銀質局部鍍金,最上方的寶石已失,在綠松石和蜜蠟之間,間隔著珊瑚珠。最下層綠松石呈花瓣形,外圍環繞一圈珊瑚珠,中間銀座托上一蜜蠟瓜棱式珠,上下又各以大小珊瑚珠襯托,銀胎為錘打成型,打造痕跡依稀可辨,鍍金的顏色淺而淡,下器底附一螺紋栓,原應固定在冠帽上,做工樸實,為西藏地方性工藝的作品。
圖8為嵌松石珍珠帽。西藏的貴族在清代統治時期被封為公爵、札薩和臺吉,納入行政體系之中。貴族的冠飾和身份等級有關,也有地域性差別。節慶盛會時拉薩一帶貴族婦女依身份高低頭戴珍珠巴珠或珊瑚巴珠,“巴珠”為藏語,指“頭冠”,作三角形支架,包覆氆氌,外層滿飾珠石,地位更高者則在巴珠之上再加上珍珠帽。珍珠帽以木為胎,滿覆一層層圈迭串結的小珍珠和不時穿插點綴的綠松石,帽頂為金嵌綠松石圖形飾,帽內上朱漆,十分厚重華麗。除了戴珍珠冠飾,通常在兩耳前側垂掛著以發辮穿系的大型綠松石耳飾,胸前戴著“嘎烏”佛鍋,裝飾著成串的珍珠串飾等,展現藏族尊貴氣派卻又不失優雅的美感。
圖9為嵌珊瑚珠石黑絨發辮套。這件辮子套清宮稱其為“黑絨練垂套”,作長筒形,發辮可置于其間,管內頭尾兩端內部以皮革加固撐起,外以珊瑚珠排列成環狀飾帶,蒙古國家博物館研究人員辨識其應為土爾扈特部婦女使用的樣式,該部以黑色為吉祥象征,故以黑絨制成。蒙古族的辮飾和帽式非常具有特色,最為人熟知的是喀爾喀部婦女頭上高高聳起兩只彎曲如羊角造型的發辮,辮子上裝飾著各式卡子,肩上的辮子也套著裝飾各色寶石的辮子套。目前辮子套的外層在修護的過程中都加了一層保護用的疏薄絹(crepeline),這是一種極細的絲綢,常被使用于織品的保存與修復。臺北故宮博物院修護部門的費心處理,配合黑色絲絨特別選擇黑色的疏薄絹,縫制成套子,套覆于絲絨上,作為保護與支撐。
超越國界的珍寶
回部位于歐洲和亞洲的交會地帶,多民族多語言:哈薩克、塔吉克、烏茲別克、維吾爾等,同時并存;這里是絲綢之路必經之地,地中海文化、伊斯蘭文化和印度文化透過商旅貿易,川流不息,無論是人們活動的范圍或是工藝技術的流傳,都超越國家界線的概念,形成多元文化混融的特質。元朝帝國曾經相連一氣的東、西兩大文明,在清朝統治內陸亞洲時再一次打通,游牧民族精湛的金工、伊斯蘭文化的玉石審美觀,出現在遙遠的紫禁城,為清代的藝術注入新生命力。
圖10為蕾絲椿伯爾提面紗。這件蕾絲面紗是塔吉克婦女的結婚用品,蕾絲的紋樣是在鏤空方形格內加上絲線,拼出幾何形的圖案,織法特殊,是十八世紀留存的少數例子。“椿伯爾提”“春伯特”是維吾爾語的漢字譯音,為面紗或面罩之意。面紗上緣鑲繡花帶,一面為金絲線繡卷草紋紅絨帶,另一面是絲線繡花卉藍布帶,二者均為中亞常見的刺繡手法與紋樣。面紗附四組系帶,兩組為紅棉線飾銀絲線結子,另兩組為金絲線飾珍珠結子、金嵌寶石線墜子,后者的金飾件以金珠組合出幾何紋,上嵌紅、綠寶石,非常具有伊斯蘭風格。這件面紗來自英吉沙爾,這是附屬于喀什噶爾的城市,喀什噶爾是古代絲綢之路北中南三線在中國西端的匯集地,中亞各地往來貿易十分發達,這件面紗正忠實地反映了絲綢之路上同時并現的多元混搭風貌。
圖11為金嵌珠石帽花。清代宮廷的木盒上寫著“金玉吉爾哈”,“吉爾哈”很可能是波斯語 jigha 的音譯,指印度和伊斯蘭王室或貴族頭巾上佩戴的羽毛狀頭飾。據清室善后委員會編印的《故宮物品點查報告》記載,其為乾隆三十五年喀什噶爾所呈進。這件頭飾羽軸的根部以玉作管狀,中心部分為一圓形花卉,羽片部位兩側并排著一顆顆由大漸小的圓形寶石,末端以偏向一側垂掛而下的單顆寶石收尾,和伊斯蘭頭巾上的飾件造型相同,嵌飾寶石的底部貼以金箔,金箔貼附并不緊密,器側各附一金煉鉤,可與帽飾等固定。最特別的是在這片羽毛的背后,加上兩只長長的金冠羽,原本屬于貴族使用的羽狀頭飾在十八、十九世紀以后發展出更多的變化,樣式繁復或變形的設計,使頭飾純以追求華麗為目的,脫離了原來作為身份象征的意義體系。就做工及樣式推測,極可能為仿伊斯蘭風格的回部作品。
圖12為包金嵌珠石帽花。這件清代記錄為“包金嵌珠石帽花”的美麗飾件,具有明顯伊斯蘭文化的色彩。一片片細長的金枝自中心柱向外伸展,柱頂一粉紅碧璽,其造型令人聯想起十八世紀以后伊斯蘭文化帝王頭巾上一叢叢向上挺立的寶石羽狀穗。同時,帽花中心柱上鑲嵌的紅、綠寶石與珠飾,不論寶石的色澤或是鑲嵌、串飾的手法或美感,都和蒙兀兒風格如出一轍。清代宮廷收藏伊斯蘭風格的頭飾很可能是由回部輾轉傳入,清代的回部是指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一帶,并包含今阿富汗、吉爾吉斯坦的一部分地區,十九世紀初浩罕商人掌握天山南、北路與中亞的進出口貿易,由于地緣與文化的相近,伊斯蘭文化相關文物在回部十分普遍,其中的精品得以進入宮廷,展出的三件帽花就是最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