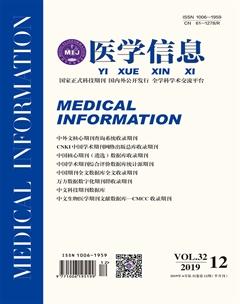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抗體及肝外疾病研究
和重祥
摘要: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PBC)是一種以膽汁淤積為特點的慢性自身免疫性肝病,可發展至肝硬化甚至肝衰竭,早期診斷PBC十分重要。PBC患者多數合并自身免疫性相關肝外疾病,包括干燥綜合征、系統性硬化癥、甲狀腺疾病等。本文總結了PBC相關抗體及相關肝外疾病的研究,幫助臨床醫生對PBC的診斷及治療。
關鍵詞: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抗體;肝外疾病
中圖分類號:R575.7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 ? ? ? ? ? DOI:10.3969/j.issn.1006-1959.2019.12.016
文章編號:1006-1959(2019)12-0050-03
Abstract: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 (PBC) is a chronic autoimmune liver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cholestasis, which can progress to cirrhosis and even liver failure. It is important to diagnose PBC early. Most patients with PBC have autoimmune-related extrahepatic diseases, including Sjogren's syndrome, systemic sclerosis, and thyroid disease.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study of PBC-related antibodies and related extrahepatic diseases to help clinicians diagnose and treat PBC.
Key words: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Antibody;Extrahepatic disease
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PBC),舊稱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是一種病理表現為免疫介導的膽道上皮細胞損傷、膽汁淤積和進行性纖維化的自身免疫性肝病,最終發展為膽汁性肝硬化[1]。PBC被認為是一種多因素疾病,是由遺傳因素和環境因素相互作用引起[2],發病以中年女性多見,通常根據患者膽汁淤積的表現、血清抗線粒體抗體(AMA)陽性做出診斷。近年來自身免疫性肝病的發生率呈明顯上升趨勢,雖然高達50%的患者在診斷時無癥狀,但當出現癥狀時往往會對生活質量和功能狀態產生重大影響,特征性癥狀包括瘙癢、疲勞和日益認識到的輕度認知障礙[3],因此早期通過抗體檢測明確診斷極其重要。現如今關于PBC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問題越來越引起關注。PBC患者至少有60%的機率出現自身免疫性肝外疾病,包括風濕性、內分泌性、皮膚性疾病等[4]。本文總結了PBC相關抗體及相關肝外疾病的研究,現綜述如下。
1 PBC相關抗體
1.1抗線粒體抗體(AMA) ?1987年,抗線粒體抗體識別線粒體自身抗原這一發現,標志著PBC研究新時代的到來,對PBC的理解取得了實質性進展[2]。高滴度血清AMA是PBC的敏感指標,其識別的抗原主要是位于線粒體內膜上的丙酮酸脫氫酶復合體E2亞單位(PDC-E2),PBC肝組織中也可見CD4+CD8+ PDC-E2特異性T淋巴細胞浸潤[5]。超過90%的PBC患者AMA陽性,AMA可分為M1~M9共9個亞型,其中AMA-M2對PBC特異性最高。當AMA陽性同時存在血清肝功能異常時,才能夠診斷PBC,有研究發現6例AMA陽性但堿性磷酸酶正常的患者中,僅有1例會在5年內出現PBC,應對AMA陽性但血清肝功能正常的患者進行隨訪,每年對肝臟進行生化等相關評估[6]。劉紅虹等[7]發現AMA-M2陽性率在肝硬化期及非肝硬化期無統計學意義,提示AMA-M2可作為篩選指標,但與病情進展可能無直接相關性。曹季軍等[8]也提出,PBC患者中AMA-M2抗體與肝功能的變化無相關性。盡管在PBC患者機體中,AMA-M2是PBC的特異性抗體,但有10%的PBC患者AMA-M2陰性[9],因此完善更多血清抗體和標記物(如抗核抗體等)檢測,一方面可使患者避免肝穿刺有創檢查,另一方面能增加AMA陰性患者診斷PBC的敏感性。研究發現[10],唾液中AMA-M2水平與血清AMA-M2水平呈正相關,血清學檢測有許多局限性,包括帶來不便、侵襲性和感染風險,唾液AMA-M2測試可能是一種更具成本效益且方便的診斷PBC的方法。
1.2抗核抗體(ANA) ?ANA是以細胞的核成分為靶抗原的自身抗體的總稱,它對多種自身免疫性疾病都具有診斷價值,其與風濕性疾病的關聯尤為密切,在慢性活動性肝炎中ANA也有一定的檢出率。董玉琳[11]研究發現,ANA在自身免疫性肝炎(AIH)和PBC的陽性率分別為61.11%和64.28%。有研究[12]對322例PBC患者進行抗體檢測,發現抗核抗體陽性率為87.0%。李沛然等[13]研究結果顯示,ANA陽性的PBC患者多表現為中滴度(≥1∶320)的核膜型或者核點型,這兩種核型的ANA都可以被純化提取為相應的特異性抗原:GP210(核膜型)、SP100(核點型)、PML(核點型)。黃程勇等[14]也發現PBC患者中ANA滴度以中高滴度為主,但核型以胞漿顆粒型和核顆型為主。有學者認為[15],ANA核膜型和核漿點型是PBC較特異核型,對PBC篩選起到輔助診斷作用,由此可見,ANA核型分析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篩查的重要指標。
目前國內PBC發病率呈上升趨勢,在無相關癥狀的隱匿期達到早期診斷尤為重要[16]。抗GP210、抗SP100是抗核抗體的亞組,其在PBC患者中的診斷價值已在許多研究中得到驗證[17]。吳婷婷等[9]發現GP210的檢測可能會有助于AMA-M2陰性的患者的診斷,因為GP210陽性主要出現在AMA/AMA-M2陰性的PBC患者中。另有報道顯示,雖然GP210、SP100這些抗體的總體陽性率在PBC患者中不高,但在AMA陰性的PBC患者中可達85%[18]。目前多個研究報道稱GP210陽性的PBC患者有更嚴重的膽汁淤積表現和肝功能損害,預后不佳。李鳳惠等[19]報道抗GP210抗體陽性患者預后較差,其研究提示抗GP210陽性組Mayo評分高于陰性組,同時還發現抗GP210陽性組肝衰竭發生率高,在隨訪期間死于肝臟相關疾病的概率也較高。有研究報道稱抗SP100與反復泌尿系統感染高度相關[18]。
1.3其他抗體 ?王美云等[20]研究發現,109例抗著絲點抗體(ACA)陽性患者中PBC占7例(6.42%)。王妙嬋等[21]研究報道,在AMA-M2陰性的PBC患者中ACA陽性率高達80%,而ACA在所有PBC患者中的陽性率為56.4%,表明ACA可作為AMA-M2陰性PBC患者的一個重要標志。田輝[22]則認為目前PBC患者ACA陽性的臨床意義不明確,因為ACA是限制型系統性硬化癥最特異的抗體(90%以上患者均可出現),尚不清楚ACA陽性是表示限制型系統性硬化癥臨床前期的標志物還是代表一種獨特的PBC亞型,亦或只是表明免疫失調的偶然現象。祁雙等[23]研究發現抗表達類泛素化修飾物(SUMO)抗體在PBC的診斷特異度高達99%,其靈敏度保持在86%,高特異度的抗SUMO抗體有望成為PBC診斷的一種新型抗體,這也提示SUMO在疾病中的表達研究初見成效。研究[24]認為抗PML抗體與中國人群PBC疾病進程的關系需進一步研究,目前認為抗PML抗體檢測對中國人群PBC早期診斷意義不大。相關研究發現[5],抗kelch樣12和抗己糖激酶1在AMA陰性PBC中的陽性率分別為35%和22%,但該檢測尚未廣泛開展。
2 PBC相關肝外疾病
2.1干燥綜合征(SS) ?SS是以侵犯唾液腺和淚腺等外分泌腺的一種慢性系統性疾病[25]。PBC與SS都有以上皮細胞為炎癥靶點的特點。有研究對322例PBC患者進行結締組織病檢查,發現150例患者患有一個或多個結締組織病,最常見為SS(121例)[12]。PBC患者中有26%~93%唾液腺活檢組織學特征符合SS,有47%~73%存在眼干、口干癥狀[26]。對于存在口干、眼干的患者需注意改變生活習慣和環境,使用唾液替代品、人工淚液等對癥處理。白曉莉等[27]研究發現,130例PBC合并SS的患者中,熊去氧膽酸(UDCA)聯合潑尼松龍治療的效果優于單獨使用UDCA治療,聯合治療可改善患者的部分肝功能和免疫球蛋白指標。
2.2系統性硬化癥(SSc) ?SSc是一種引起皮膚增厚和內臟器官纖維化的慢性自身免疫性結締組織病[25]。近幾年國內外關于PBC合并SSc的報道陸續出現。王曉東[28]研究發現9例PBC合并SSc患者,7例SSc的臨床癥狀或體征早于PBC的臨床表現,1例PBC診斷早于SSc,1例PBC和SSc幾乎同時發病,表明SSc的發病通常早于PBC。有研究報道80例PBC患者中,10例PBC患者滿足早期SSc診斷標準,5例患者確診SSc,同時發現PBC合并和不合并SSc的患者中,在轉氨酶、堿性磷酸酶方面無差異[29]。
2.3其他風濕性疾病 ?PBC患者中類風濕關節炎(RA)的患病率在1.8%~5.6%[4]。若PBC患者出現關節癥狀,需結合患者關節病變特點及輔助檢查,以明確是PBC引起的關節病變還是RA,避免誤診[30]。PBC與系統性紅斑狼瘡(SLE)的關系很少報道,在英國和日本文獻中僅發表了34例[4]。王立等[31]報道在322例PBC中,PBC合并SLE共12例,占全部PBC患者3.7%,均為女性患者。當PBC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時,患者應配合使用免疫抑制劑和腫瘤壞死因子拮抗劑進行治療,例如甲氨蝶呤是RA治療的一線用藥。
2.4甲狀腺疾病 ?Floreani A等[32]對921例PBC患者隨訪觀察,共有150例(16.3%)患有甲狀腺疾病,其中94例(10.2%)為橋本氏甲狀腺炎,15例(1.6%)為Graves病,22例(2.4%)為多結節性甲狀腺腫,7例(0.8%)為甲狀腺癌,此外還發現甲狀腺疾病的存在并不影響肝臟并發癥的發生率或PBC的自然病程。相關文獻也提出,自身免疫性甲狀腺疾病本身似乎并不顯著影響PBC的自然史[33]。2015年PBC診治共識中指出,約15%~25%的PBC患者合并有甲狀腺疾病,且通常在PBC起病前即可存在,建議在診斷PBC時均應檢測甲狀腺功能并定期監測[34]。
2.5皮膚病 ?結合現有相關文獻報道,雖然仍有部分學者堅持PBC可能與白癜風、銀屑病、扁平苔蘚、甚至罕見的褶皺處無菌性膿皰病相關,但目前缺乏任何皮膚病與PBC之間的明確關系[4,22]。
3總結
PBC是一種慢性自身免疫性肝病,最終將發展為肝硬化,隨著診斷技術及研究水平的提高,更多自身抗體譜的檢測應用于臨床工作中,對于PBC診斷及預后有重要意義。目前本病在臨床上并不少見,且常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臨床醫師應進行詳細的病史詢問及體格檢查達到早期診斷及早期治療。
參考文獻:
[1]李謙謙,周新苗.《2018年英國胃腸病學會/英國PBC協作組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治療及管理指南》推薦意見[J].臨床肝膽病雜志,2018,34(6):1191-1192.
[2]Tanaka A,Leung PSC,Gershwin ME.Evolution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PBC[J].Best Pract Res Clin Gastroenterol,2018,34-35(5):3-9.
[3]Khanna A,Leighton J,Lee WL,et al.Symptoms of PBC-Pathophysiology and management[J].Best Pract Res Clin Gastroenterol,2018,34-35(6):41-47.
[4]Floreani A,Cazzagon N.PBC and related extrahepatic diseases[J].Best Pract Res Clin Gastroenterol,2018,34-35(5):49-54.
[5]王璐,韓英.《2018年美國肝病學會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實踐指導》摘譯[J].臨床肝膽病雜志,2018,34(11):2300-2304.
[6]孫春燕,馬雄.《2017年歐洲肝病學會臨床實踐指南: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的診斷和管理》摘譯[J].臨床肝膽病雜志,2017,33(10):1888-1894.
[7]劉紅虹,福軍亮,徐軍,等.123例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臨床表現與自身抗體譜[J].北京大學學報(醫學版),2013,45(2):233-237.
[8]曹季軍,李勇,王金湖,等.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自身抗體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比較及其臨床意義[J].臨床檢驗雜志,2018,36(10):738-742.
[9]吳婷婷,王興亮,劉興祥,等.AMA-M2抗體、gp210抗體和sp100抗體對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的診斷的價值探討[J].中國中西醫結合消化雜志,2018,26(12):1046-1048.
[10]Lu C,Hou X,Li M,et al.Detection of AMA-M2 in human saliva:Potentials in diagnosis and monitoring of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p[J].Sci Rep,2017,7(1):796.
[11]董玉琳.六種肝抗原自身抗體檢測在自身免疫性肝病診斷中的應用研究[J].現代診斷與治療,2015,26(20):4740-4742.
[12]Wang L,Zhang FC,Chen H,et al.Connective tissue diseases in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a population-based cohort study[J].World J Gastroenterol,2013,19(31):5131-5137.
[13]李沛然,陳霖,劉愛霞,等.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的實驗室指標分析[J].肝臟,2018,23(3):221-223.
[14]黃程勇,陳雯.自身免疫性抗體檢測在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診斷中的臨床意義[J].中外醫學研究,2018,16(32):43-44.
[15]葛紹鋒,張忠源,楊香洪.抗核抗體和自身免疫抗體譜檢測在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診斷中的應用價值[J].醫療裝備,2018,31(10):55-56.
[16]薛偉,朱燁.AMA-m2運用于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早期篩查的效果研究[J].河北醫學,2016,22(1):15-17.
[17]Yang F,Yang Y,Wang Q,et al.The risk predictive values of UK-PBC and GLOBE scoring system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the additional effect of anti-gp210[J].Aliment Pharmacol Ther,2017,45(5):733-743.
[18]閆琪.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44例臨床分析[D].蘇州大學,2016.
[19]李鳳惠,呂洪敏,向慧玲,等.血清抗GP210抗體對PBC患者的診斷價值[J].天津醫科大學學報,2011,17(4):549-552.
[20]王美云,張宏,陶金輝,等.抗著絲點抗體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的臨床意義[J].實用醫學雜志,2012,28(4):586-588.
[21]王妙嬋,徐愛芳,湯曉飛.抗著絲點抗體陽性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患者血清學及影像學特征分析[J].中國衛生檢驗雜志,2018,28(7):827-829.
[22]田輝.自身免疫性肝病相關性風濕病樣及皮膚表現[J].臨床肝膽病雜志,2018,34(9):2021-2026.
[23]祁雙,舒李鑫,韓崇旭.抗SUMO抗體在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臨床診療中的價值[J].國際檢驗醫學雜志,2019,40(3):298-303,307.
[24]張海萍,閆惠平,陳小三,等.不同免疫方法檢測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特異性自身抗體的對比研究[J].中華檢驗醫學雜志,2018,41(3):203-207.
[25]羅秀霞,尹志華,曹智君,等.抗核抗體譜十八項檢測在系統性紅斑狼瘡中的臨床應用[J].現代生物醫學進展,2014,14(34):6676-6679.
[26]陳歡雪,王曉非.干燥綜合征肝損害[J].中國實用內科雜志,2017,37(6):496-498.
[27]白曉莉,管斌,朱建榮.熊去氧膽酸聯合潑尼松龍治療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合并干燥綜合征[J].貴州醫科大學學報,2017,42(2):226-229.
[28]王曉東.系統性硬化癥合并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的臨床和免疫學特征分析[J].現代實用醫學,2015,27(8):992-993.
[29]Tovoli F,Granito A,Giampaolo L,et al.Nailfold capillaroscopy in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a useful tool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of scleroderma[J].J Gastrointestin Liver Dis,2014,23(1):39-43.
[30]胡文露,劉升云,張磊,等.類風濕關節炎合并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3例[J].中華臨床免疫和變態反應雜志,2015,9(3):231-234.
[31]王立,楊云嬌,張烜,等.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合并系統性紅斑狼瘡的臨床特點[J].中華臨床免疫和變態反應雜志,2013,7(1):36-40.
[32]Floreani A,Mangini C,Reig A,et al.Thyroid Dysfunction in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A Comparative Study at Two European Centers[J].Am J Gastroenterol,2017,112(1):114-119.
[33]Kus A,Arlukowicz-Grabowska M,Szymański K,et al.Genetic Risk Factors for Autoimmune Thyroid Disease might Affect the Susceptibility to and Modulate the Progression of 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J].J Gastrointestin Liver Dis,2017,26(3):245-252.
[34]賈繼東.原發性膽汁性肝硬化(又名原發性膽汁性膽管炎)診斷和治療共識(2015)[J].肝臟,2015,20(12):960-968.
收稿日期:2019-3-9;修回日期:2019-3-22
編輯/楊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