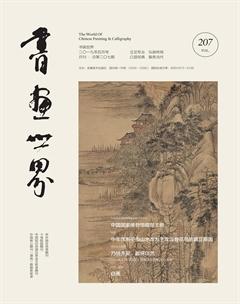“鐵”與“畫”
李品 郭兵要

內容提要:“山水人物皆空嵌,巧奪萬代所未有”,蕪湖鐵畫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中一個獨具特色的藝術品種而馳名中外。鐵畫從字面上理解是“鐵”與“畫”,是藝術家與鐵匠緊密合作產生的結果,兩者形影不離,缺一不可。但縱觀當下,蕪湖鐵畫前行之路艱難,出現后繼乏人的窘境。究其緣由,就是有“鐵”無“畫”,有“藝”無“鐵”。
關鍵詞:“鐵”與“畫”;蕪湖鐵畫;畫稿
鐵畫源于宋代,盛行于北宋。清代康熙年間,蕪湖鐵畫自成一體,享譽四海,距今已有340多年的歷史。蕪湖鐵畫以錘為筆,以鐵為墨,以砧為紙,鍛鐵為畫,鬼斧神工,氣韻天成。據清代《蕪湖縣志》所錄《鐵畫歌·序》載,蕪湖人湯鵬“少為鐵工,與畫室為鄰,日窺其潑黑勢,畫師叱之。鵬發憤,因鍛鐵為山水嶂,寒汀孤嶼,生趣宛然”。由此不難看出湯鵬創造鐵畫是受蕭云從繪畫的影響。湯鵬與蕭云從的合作,猶如戲曲創作,明代戲曲家湯顯祖為了推出一臺好戲,會主動參與戲班生活和排練,體會“案頭”和“場上”微妙的關系,由此才能創作出佳戲。
一、鐵畫的現狀
(一)人、畫兩缺
蕪湖鐵畫是一種民間的自發的審美運動,因鍛打技藝之精湛、與國畫碰撞結合的巧妙為百姓喜聞樂見。它以低碳鋼做原料,在制作過程中遵循中國傳統國畫的構圖法則及金銀首飾、剪紙、雕塑等工藝技法,經出稿、鍛打、焊接、銼、鑿、除銹、著漆、上框等工序制成,既有國畫之神韻又具雕塑立體美,還能將鋼鐵的柔韌性和延展性發揮得淋漓盡致。按說這種純以審美原因而輝煌、不曾加入宗教信仰的力量捆綁銷售的作品,本不該受到民間信仰缺失的影響,技藝類似的如景泰藍、漆藝等,不管意識形態如何變化,它們始終以技藝來滿足著人們的審美需求,仍然廣為人知,仍然不曾降低其在民眾心中貴重物品的定位。然而據調研得知,目前蕪湖鐵畫從業人員不足80人,30歲以下傳承人更是屈指可數。蕪湖本地的年輕人,生于斯、長于斯二三十年,生活中都不曾接觸鐵畫,更有甚者竟不知鐵畫為何物,如此窘境,不禁令人痛心。長此以往,這造成惡性循環之局面,最終導致鐵畫傳承人鏈條“斷裂”,出現后繼無人的尷尬局面。
通過對蕪湖鐵畫藝人群體的深入調研,我們發現他們普遍文化水平較低,且多數為中學或小學畢業,僅一人上過藝校。這就導致他們審美素質較為低下,無法創作畫稿及準確判別一幅畫稿究其妙在何處。既不懂畫稿,必定會盲從畫稿,如有不妥之處,也必定不知避讓或刪減,長此以往,必然導致有技無藝,產出的優質鐵畫寥寥無幾。目前市場上可見的蕪湖鐵畫作品,迎客松居多(多因北京人民大會堂有巨幅鐵畫迎客松),其次是八駿圖、梅蘭竹菊、四條屏等,表現方式多年不變,罕見出新。近些年蕪湖鐵畫市場混亂,又因版權保護意識弱,抄襲現象屢見不鮮,同質化嚴重。一些不良商家為了生存,打價格戰,惡意競爭,以次充好,將鐵畫本質美拋之腦后,可拿得出手的鐵畫少之又少。
(二)過度依賴政府
蕪湖鐵畫的衰落引起眾多專家、學者的關注,他們試圖挽救這一寶貴的民族財富,但是在挽救方法上不應該只是國家政策、財力的傾斜這么簡單。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儲金霞曾言:“不能讓非遺變成遺產,最后成為遺憾。”只有它發了新的芽,抽了新的枝,重新獲得了生命力,才算是真的活了起來。鐵畫鍛制技藝傳承340余年,至今經歷了幾次大起大落,鐵畫藝術在歷史上出現的每一次輝煌都與政府有關,政府的力量介入對于幾乎所有產業的影響自然是不可小覷的。若一個產業一味地強調政府扶持,而不去重視其在民間土壤中的生命力,我們是否可以將其理解為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是對政府的捆綁?《蕪湖鐵畫保護和發展條例》已于2016年9月30日在蕪湖市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通過,2016年11月10日安徽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四次會議批準。自立法以來,《蕪湖鐵畫保護和發展條例》實施已有兩年有余,效果如何,客觀來講見效甚微,治標不治本。作為首個非遺保護例法,政府出發點很好,但令部分鐵畫藝人反噬,覺得已有立法,政府必須大力扶持,無論是財力還是物力,處處想獲得政府資助,出現對政府的捆綁現象,而個人則不思進取,技和藝停滯不前。
二、“鐵”與“畫”
(一)有“鐵”無“藝”、有“藝”無“鐵”
眾所周知,蕪湖鐵畫的輝煌是以與國畫的結合為肇始的,直到今天,它多以國畫為范本(鐵畫目前還未出現脫稿直接鍛打之人),如鄭板橋的竹、徐悲鴻的馬、王石岑的迎客松等。隨著社會的發展,國畫變化日新月異,新文人畫、當代水墨等詞不斷涌現。任何新事物的出現,必定需要時間的檢驗。安徽工程大學藝術學院院長黃凱教授于2017年6月在安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給2016年度國家藝術基金“蕪湖鐵畫藝術人才培養項目”學員授課時,曾言:“蕪湖鐵畫應該分為三類,其一是高端藝術品;其二是中層可接受的工藝品;其三是大眾消耗品。”按如此分類法,鐵畫的畫稿也須分為三種,與之對應。鐵畫藝人因其文化水平較低,缺乏美術基礎,無法獨立創作畫稿,而目前多數創作畫稿之人又不懂鐵畫,兩者存在一定的隔閡。能作為鐵畫底稿的作品要多以寫意線形造型(寫意為主),潑墨或者工筆勾線并不適合轉換為鐵畫。蕪湖鐵畫藝人們一方面苦于好畫稿的匱乏,另一方面又因生活壓力所迫,他們不敢隨意嘗試新的畫稿。因為新作是否有市場,能否在短時間帶來經濟效益,還須經過市場的檢驗。新畫稿隨之而來的是新技藝的產生,有部分藝人不愿意花時間研發新的技藝,與其嘗試新技藝,不如多做幾件“產品”,這樣才有基本的收入。如此一來,必定會出現有“鐵”無“藝”、有“藝”無“鐵”的現象,更不易適應新的消費群體的審美與需求。
(二)停滯不前、虛無市場
蕪湖市工藝美術廠于1956年成立,曾被評為國家旅游工藝品定點生產企業、安徽省旅游先進窗口單位。該廠主要生產蕪湖鐵畫與金飾工藝畫,效益最鼎盛時期年產值可多達人民幣2億元。然而在2012年12月,由安徽德潤文化置業有限公司以歷時56年的蕪湖市工藝美術廠資不抵債為由,向鏡湖區法院申請對蕪湖市工藝美術廠進行破產清算,原來屬于國營的工藝美術廠就這樣被迫解散。該廠破產后,鐵畫藝人自謀生路,有的轉行,有的則在家里鍛制鐵畫,有的成立鐵畫公司。目前幾個規模較大的鐵畫公司有蕪湖市儲氏鐵畫工藝品有限公司、蕪湖市飛龍鐵畫工藝品有限公司、蕪湖文典鐵畫工藝品有限公司、徽藝坊等。從調研結果來看,個人單獨銷售除儲金霞、張家康較易外,其他均難度較大。多數鐵畫藝人的作品只能低價出售給大的鐵畫公司來維持基本的生活需求。如此一來,鐵畫藝人就很被動,他們不敢輕易改變或者也不會修改畫稿,只能按照畫稿鍛打;另外,創新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鐵畫經營者作為商人,利字當頭,他們也不敢輕易嘗試拿新類型的作品去接受市場的檢驗。可是,購買者看厭了傳統的圖式,形成視覺疲勞,久而久之,無人愿意為這些老套的作品買單,最終就會導致無人愿意承擔研發新產品的風險。據不完全統計,目前蕪湖市整個鐵畫市場年產值不足2000萬元,足可以說明市場蕭條程度。
三、新畫稿、新面貌
隨著文化自信的不斷提出,部分藝術家將目光轉向民族傳統藝術上,以求得新突破。如天津美術學院譚勛教授所創作的《草》系列作品(圖1),他用蕪湖鐵藝技術對小草進行了巧妙的轉化,不但將非遺工藝帶入當代文化語境之中,探索并激活了傳統文化的可能性,而且在觀念上對這些“弱者”進行了語義的重塑—堅硬的鐵消解了草的柔弱,增強了對現實的觀照,以此反思當代人的生存現實。又如安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郭兵要老師親自畫稿、親自鍛制的作品《眾生相》(圖2),該作品借用蕪湖鐵畫獨特的鍛制技藝,表現出蕓蕓眾生行走過急而迷失自我的一種生活狀態,并作為蕪湖鐵畫新秀成功入選由中國美術家協會舉辦的首屆全國工藝美術大展。再如2017年6月在安徽師范大學開班的2016年度國家藝術基金“蕪湖鐵畫藝術人才培養項目”,面向全國招生30名學員,這些學員多數為本科以上學歷,且其中一人為博士學歷,經過短短65天培訓,以驚人的速度和水平創作出90余件鐵畫(30幅太平山水圖,60余件自由創作),最終5名學員共7件作品獲得2018年度國家藝術基金滾動資助。這些“新興的鐵畫藝人”的出現為鐵畫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引起鐵畫界陣陣波動。由此可見,只有“鐵”與“畫”、“鐵”與“藝”合二為一,才能更好地促進蕪湖鐵畫發展。
結語
綜上所述,“鐵”和“畫”,一個為技,一個為藝,兩者相互交織,缺一不可。為了鐵畫更好地發展,鐵畫藝人們需要提高自身的審美能力,從而提升創作能力,更好地滿足市場的需求,使蕪湖鐵畫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新時代產生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