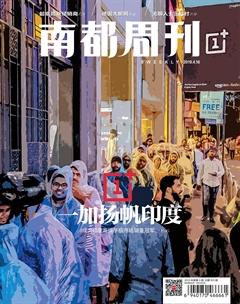原生家庭:都挺不好?
尼德羅 壹哥
正方觀點 什么都要怒懟“原生家庭”?那是你自已不爭氣
正如“原生家庭”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心理學術語,如果不那么嚴格地進行推斷,80后、90后大抵是人類歷史上生活水準最高的一代人。然而,恰恰是享受了最好物質和精神陪伴的這一代人,卻喊出了“父母皆禍害”的口號。近年來,包括《歡樂頌》、《狗十三》、《都挺好》等熱播的影視作品,都能激起觀眾對“原生家庭”的討論,乃至掀起對原生家庭的集體聲討。
作為生活水準更高的一代人,何以對原生家庭產生了如此多的怨恨?答案也許可以套用一個句式:原生家庭就像一個錘子,一旦拿起來,看見什么都像釘子。畢竟,任何人都成長于某個具體的家庭,與父母多年的相處經歷,也總能發掘出一些負面影響。所以,當聲討原生家庭變成一種成本低廉行動,就更容易引發人群的共鳴,并大有成為一股潮流,一種政治正確的趨勢。
對于一些人來說,原生家庭的影響的確非常深遠。就像一張正態分布圖,特別糟糕的原生家庭和特別完美的原生家庭,對孩子的影響都會更大。但是,需要說明的是,這樣的判斷很難進行測量,也無法預判某個糟糕家庭或某個幸福家庭成長的孩子一定會如何發展。也因為這樣,當聲討原生家庭成為潮流時,很多人都會隨波逐流,試圖將自己的某些人格缺陷與原生家庭進行對應。
依照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公布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嚴重的軀體虐待或者是嚴重的性暴力,才會帶給孩子明顯的童年陰影。然而,對于絕大多數80后與90后來說,成長經歷中也許存在一定的情感忽視或冷暴力,但不可能大量經歷嚴重的軀體暴力或持續性的性暴力。對此,有兩份研究可以提供更直接的證據,來證明原生家庭其實并沒能決定一切,甚至其影響是微不足道的。
首先是《科學》雜志曾刊發過一份研究報告,報告歷經10年時間,調查了56對分開養育的同卵雙生子和30對一起養育的同卵雙生子,結果顯示分開養育和一起養育的雙胞胎們,他們的人格測試結果基本上是一致的。第二份研究則是針對經歷過納粹集中營孩子的,研究發現那些能夠最終戰勝貧窮和社會隔離的孩子,他們具有更強的韌性。顯然,今天很少有什么人的成長境遇能夠跟納粹集中營中的環境相提并論。
所以,原生家庭并非不重要,但看待原生家庭更需要明白的一點是:對于一個人的人格發展,首要的因素其實是遺傳基因,這個占比接近一半;其次是環境因素,而家庭環境是其中之一,學校環境、社會環境也非常重要。實際上,面對不同的環境,我們會戴上不同的面具,乃至表現出不同的人格。
因此,只要不是生活在小概率的極端家庭,一般而言,家庭養育模式對孩子人格的影響并不大,家庭環境的影響很多時候還趕不上學校、工作環境。之所以這一代年輕人傾向于將自己的某些性格問題,歸咎于父母的養育方式問題,根本原因還在于這一代人太過“自戀”。他們成長至今,內心并不清楚父母的精神狀態和行為方式其實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受父母的父母、所處的時代、身邊的朋友影響而形成的。

從這一點出發,在聲討原生家庭之前,他/她本人應該想辦法進入父母所經歷的家庭、社會和時代構成的特殊語境。一旦進入了這一語境,他/她的同理心會更強,對生命的理解會更深,與父母和解的能力也會更強。由此可見,人格也好,性格也罷,改變的力量終究來自自己的內心,一味歸咎于原生家庭,其實是一種自我放棄的狀態。
反方觀點 原生家庭的戰爭,要么生,要么生不如死
一個老朋友突然在微信上問我:“你看沒看《都挺好》?”問這話的人,已經3年沒有回過一次老家,談起老家,永遠是支支吾吾,顧左右而言他。
就在上個月底,一個剛剛13歲的男孩在深圳跳樓自殺。在他留的四封遺書里,有一句話特別刺眼:“爸爸媽媽,我知道你們討厭我,我走了,請不要傷,心難過。”
看見朋友的微信,我突然想起了這條新聞。然后只回了他兩個字:“看了”。
如果用兩個詞來形容看完《都挺好》的感受,我會選擇這兩個詞:擊節叫好,慘然一笑。
擊節叫好,是因為終于有了一部電視劇,告訴我們原生家庭會給孩子帶來多大傷害。而慘然一笑,是因為它來得太晚了,晚到很多的傷害已經造成,很多人的半輩子已經過去。如果它早來20年、30年,很多人,也許會比現在幸福太多。
劇一開篇,就是蘇家老母親去世,明哲、明成、明玉兄妹三個回來奔喪。但奇怪的是,姚晨演的蘇明玉對母親的喪事從始至終都是一副“公事公辦”的態度,似乎去世的不是她自己的媽。
看到這我有點納悶:一家人,何以至此?后面的劇情很快就給出了答案。

畫面轉回10年前,明玉正在高考復習的沖刺期,此時大哥明哲剛從清華畢業,準備去美國念書,二哥明成也剛被家里人安排了工作。明成休息回家—上來就干了兩件事:1.圍著媽媽撒嬌。2.把一包臟衣服丟給妹妹,命令她去洗。
正在備戰高考的人,怎么可能有時間給別人洗衣服?但媽媽可不這么想,她的態度很明顯地偏向哥哥。一個詞瞬間出現在眼前:重男輕女。《都挺好》里簡直就為我們演示了教科書式的重男輕女,看得我這個男人都忍不了了。比如吃個飯,媽媽給兩兒子夾了雞腿,就是不給明玉夾。
這部劇不光展示原生家庭之罪,更是在展示家庭的傷害,到底會怎樣影響子女的一生。小時候受的那些傷,往往在成年后,才會顯露出它真正的疤痕。
最明顯的要數明玉,自小不受待見讓她形成了邊緣化的人格。她極度自律刻苦,拼了命地往上爬,只想讓別人能看得起,在上大學的時候把自己成功推銷給了后來的老板。但同時,她卻像是一個極度理性的工作機器,理性到不近人情。除了對老板的忠誠,幾乎不會對任何人產生依賴和感情。她身居高位,住著高檔公寓,但每天晚上都是獨自面對冰冷的衣柜,夜夜失眠。
中國有多少家庭是被這種循環毀掉的呢?告訴你,比你想象的多得多。開頭提到的那個朋友,每次問他為什么過年不回家,他只會說一句:“跟家里的感情已經很淡了,不想回去。”
我的一個女同學,跟男朋友談了十年的戀愛,就是不敢結婚,更不敢要孩子。問起原因,她總說:“我怕我的孩子來到這世上,和我小時候一樣痛苦。”
這樣的例子,我可以給你舉一車出來。他們大多甚至都不涉及重男輕女問題,因為都是獨生子女,但是他們都對父母有著同樣綿延半生的仇恨。每個中國家庭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問題。把《都挺好》上升到全民層面,每個中國家庭,其實都挺不好的。
但《都挺好》也給了一點暖心的希望:明玉碰到了一個可以讓她托付愛的男人,也許這個人是她與自己和解的開始。(本文原載“一條電影”公號,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