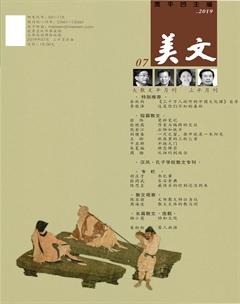文體散文特征芻議

陳亞麗
之所以要特別明確是“文體散文”,是因為時下文體(文學)散文與中國古代“散文”(散行文章),常常被混為一談,在此以示區別。
文體散文作品多、精品也不少,散文愛好者更是多如牛毛;但細究起來,它自身似乎有很多“說不清”的問題;而現存所謂“文學理論”,其實往往與散文無關。僅就散文文體特征而言,就亟待理順。
五四以來的敘事抒情散文及隨筆,就創作素材而言,都是以客觀真實為前提的,非虛構性突顯。散文“第一人稱”的抒寫形式,也即內容;散文的“核心人物”是敘述者即作者自身,所敘之事是圍繞敘述者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件。林語堂曾經強調“小品文”讀來應“如至友對談,推誠相與,易見衷曲”;梁實秋也坦言:“平常人的語言文字只求其能達,藝術的散文要求其能真實,——對于作者心中的意念的真實。”散文是作者人生體驗的真實記錄。
散文以“我”為中心,這在眾多文學體式中是“獨一無二”的。不管是中規中矩的敘事抒情散文,還是“碎片化”“陌生化”的后現代主義散文,都是“我”眼中的社會現實,哪怕是有點不可思議的本雅明的隨筆,都不能逃脫“我”心靈的洗滌與升華。
散文中的“敘事”,常常是“片段性”的,或是“階段性” 的。可以是“僅僅”關乎個我的生活經歷,還可以是對一段生活的總結與了悟,包括作者的閱讀體驗。散文,無論長短,都只是人生歷程中的一個“橫斷面”而已。以敘述“生活片段”為主的就是敘事抒情散文,以“歸納總結”人生感悟為主的就是隨筆。
中國現代白話散文自誕生之日起,就顯示出記憶的再現性特征。魯迅在《朝花夕拾》“小引”里說,兒時所曾吃過的菱角、羅漢豆等,“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后來,我在久別之后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由此可見,記憶是對過去日常點滴感受的積累,必然攜帶一種主觀情感,是作者寶貴的人生體驗。
本雅明曾說過:“生命的真正尺度是記憶,它在瞬間跨越了人的一生,隨后將目光轉向后面。”散文是一種再現性記憶的復制。記憶首先是一個心理學范疇,記憶因子儲存于人類的大腦之中,而“重現”(再現)作為記憶的核心問題“是語言和實在之間的邏輯聯系和審美聯系。而這一切,只有通過符號才能發生”。記憶需要一種話語進行表達,而散文則是呈現記憶的最佳話語模式,換句話說,記憶在散文那里得到了最適宜的表達。既然“重現”(再現)記憶的“核心問題”是“語言和實在”之間的邏輯聯系,所以這注定了“實在”成為記憶呈現的重要內核。散文是“從記憶當中抄出來的”,也就注定了散文表現“實在”、表現客觀真實的“宿命”。所謂“語言和實在之間的邏輯聯系和審美聯系”,換句話說,在表現記憶的時候,只需要考慮語言是否能夠準確、和諧、優美的表達“實在”,這種表達是否符合邏輯,是否具有美感。
嚴格來說散文的寫作心理主要是聯想。聯想的心理活動的基本規律就是由此及彼。聯想包括感性聯想和理性聯想。感性聯想多半由具體事物或情景引起。比如魯迅的《阿長與<山海經>》,由對于阿長的稱謂,到阿長的睡姿,直至阿長所教的“吉祥話兒”,每一件事、每一個細節,都源于作者的聯想,因為所有內容均為已經發生,而且所聯想的事情均為日常瑣事,且都是具體的事物或情景。這屬于感性聯想。魯迅的另一篇作品《女吊》,是被放置在雜文集里,但文章主要介紹了家鄉的民俗,實際是一篇隨筆,作家在寫作過程中同樣主要運用了感性聯想的思維方式。所謂“理性”聯想,就是對已經存在的客觀事物要有所概括、抽象和提煉,比如荀子《勸學》,“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性非異也,善假于物也。”這里由前兩句推導出第三句的結論,從心理活動來說就屬于理性的聯想。
從散文的寫作心理和小說的創作心理的差異看,散文作者的“自主性”明顯要弱于小說作者的“自主性”。 散文寫作需要“按部就班”、“以文運事”,必須按照基本的客觀事實去組織篇章;而小說創作則給作者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空間,可以“因文生事”。可以說,散文反映主客觀世界的方式,是在已有的現實材料中去“選擇”,所以主要是聯想;而小說反映主客觀世界的方式主要是,模仿現實生活去創造一個全新的與現實生活毫無現實關聯的虛擬世界,虛構性想象、創造性想象是必備的心理基礎。
可以說,散文是以真實發生過的事實為基礎,是對現實生活的再現,絕大多數內容是紀實性的,是再現性的記憶的復制;小說、戲劇創作是以作者的想象空間為基礎,充滿了“無中生有”的創造性想象,離不開“綴合”與“虛構”。
散文還可以直接袒露作者的襟懷與抱負,可以集中表現作者的精神追求與境界。因為散文屬于“向內”的文學,即散文常常是對作者內心世界的裸現。散文所表現的都是經過作家內心世界過濾之后的作家眼中的現實,是對作家自身情感和心靈的審視與裸露。散文作者,首先是文化人,其次可能還是某一領域的專家、學者,或者是小說家、戲劇家、詩人以及生活閱歷豐富者等等,作者本身的文化積淀都會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散文作品之中;更因為散文沒有任何人格面具,所以作者的思想深度、歷史哲學以及審美風格等等通通會在散文中“和盤托出”。而在小說創作中,作家“個我”是完全隱蔽的,不是也不可能直接呈現作者個人的真實觀點,所以才會有西方敘事學中所謂作者、“隱含作者”、“敘述者”之區別。
散文表現的是作者真實的現實生活以及他們的內心世界,而小說作者可以完全游離于作品之外。有學者說:“散文是整個文學大廈的基座,是詩以外別的文學門類的母體,它還每每是一個民族、一個時代文學成就潮漲潮落的標尺,是作家們文學能力的試煉場,測試其思想、文化、審美涵養的全部綜合能力的一枚指針。”?這段話一方面表明散文在整個文學門類中無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另一方面也強調了散文直接反映作家的思想、文化、審美涵養等全部綜合能力的特征。作家在創作散文時,作家的心理活動、內心世界展露無遺,作家的文化人格全部投射在散文的字里行間。可以肯定,散文就是作家本人文化積淀的集中展示,也可以說散文就是文化的直接載體,是作家文化人格與智慧的藝術體現。
羅蘭·巴特關于“作者已死”的論斷在散文這里是斷然行不通的,因為散文的作者不僅沒有死,而且始終活在散文作品之中。散文一方面直截了當地展示著作者的“愛恨情仇”,另一方面作者的文化修養與審美嗜好、思想深度甚至多年累積而成的“語氣”都“一覽無余”地裸現在散文作品里。
散文在創作方式上充分體現出“散漫自由、以小見大”的特征。“散漫自由”是“根本” ,“以小見大” 則是具體表征。一方面指在行文過程中沒有固定的結構模式,另一方面指素材“大小隨意”,同時還包括篇幅“長短由人”。所謂“小”,既指散文的素材,又指散文的篇幅。“散漫自由”與“以小見大”互為表里,是散文特征之一的“一體兩面”;也互為“因果”,因為“散漫自由”,所以才有可能導致“以小見大”,“小”是“自由”的直接結果;而由“小”至“大”,則是一種自然的選擇。如果不能通達“大”的效果,散文就失去了存在的生命力。“散漫自由、以小見大”集中反映了散文與其他文學文體的本質差異。
所謂“散漫自由”,意味著表達的自然、樸素,不飾雕琢。在《蒙田隨筆集》“致讀者”中蒙田坦言:“若是為了嘩眾取寵,我就會更好地裝飾自己,就會斟字酌句,矯揉造作。我寧愿以一種樸實,自然和平平常常的姿態出現在讀者面前,而不做任何人為的努力,因為我描繪的是我自己”,可見,蒙田在此書中所要展示的是真實、自然、平常的“自己”,堅決摒棄“偽飾”與“做作”,哪怕是“字斟句酌”,都是他所不齒的。
五四時期在“小品文”的大討論中,許多作家、學者都主動闡明了自己對于“小品文”的認知,比如李素伯曾這樣描述:“把我們日常生活的情形、思想的變遷、情緒的起伏,以及所見所聞的斷片,隨時隨地抓取,隨意地安排,而用詩似的美的散文,不規則地真實簡明地寫下來的,便是好的小品文。”“散漫自由”之謂也!
林語堂曾提出“小品文的筆調”,即娓語式或閑談筆調。林語堂發現了“談話”與“小品文”的共通之處,他指出,無論是在格調抑或內容方面,談話和小品文都類似,且均需一種不經意的、悠閑的、親切自然的態度:“或剖析至理,參透妙諦,或評論人世,談言微中,三句半話,把一人個性形容得惟妙惟肖,或把一時政局形容得恰到好處,大家相視莫逆,意會神游……”所謂的“娓語式”,其實就明確闡述了散文行文過程中的任意而談,任心而為。
散文,無論中外,其開頭、中段、結尾的寫法都沒有一定之規,完全規避了小說的章回結構、戲劇的場幕格局以及詩歌的韻律要求等等形式束縛,如何開頭、又如何收尾,任憑作者的心性,完全跟著作者的感覺走;“散漫自由”同時還表現在篇幅的大小及素材的選擇上。散文的“篇幅短小”、“素材雖小”,但是格局常常闊達、氣韻不凡。
在與其他文學形式的比較之中可以得出,散文是以作者真實的生活經歷及生活感悟為主要素材的,與虛構無緣;是作者記憶的再現,主要以聯想為心理基礎;是作者情感、思想、情趣乃至整個心靈世界的裸現,是作者文化人格與智慧的集中體現;散文是作者表現“自我”最為酣暢淋漓、行文無拘無束的藝術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