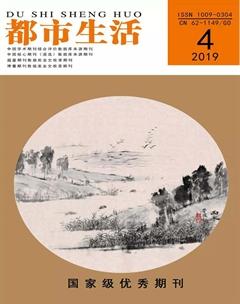人才集聚動力因素分析
摘 要:人才對國家或區域發展的重要作用得到廣泛的認可,而人才集聚作為人才流動的一種特殊現象也引發了國內外學者的關注。本文從人才定義入手,通過國內外文獻分析與整理,對人才集聚內涵進行界定;以此為基礎,搜集并整理了人才集聚的相關文獻,基于文獻綜述視角對人才集聚的動力因素進行梳理。
關鍵詞:人才集聚 動力因素 文獻綜述
一、引言
1912年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將創新定義為“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引人生產體系”,并指出:科技和科技創新催生了新產業,促進了新增長。技術對經濟增長驅動作用得到眾多學者認可,然而,技術的產生、重組和傳播關鍵在于人才,其既有知識、能力與經驗會決定其應用新技術水平。人才是區域發展的重要因素,其在國家和區域發展研究中得到重視(Simon,1998;Glaeser,2012)。
二、人才集聚的內涵
1998年,麥肯錫咨詢人員提出“人才大戰”,并認為人才是組織獲得成功的重要因素(Michaels等,2001)。然而, “人才”一詞被理所當然的廣泛使用,卻尚未得到明確解釋。在梳理“Talent”一詞語言進化史基礎上,Gallardo-Gallardo(2013)提出了人才的兩種解釋:組織中的精英群體;組織中的所有雇員。鑒于精英群體判斷具有主觀性,本文選擇“組織中的所有雇員”作為人才的定義。
隨著人才在城市發展中作用的凸顯,人才集聚作為人才流動的的一種特殊現象得到學者們重視。國內學者蔡永蓮(1999)提出“人才集聚”概念,指出人才集聚可通過類聚效應、綜合效應和聯動效應產生聚合效果。隨后,朱杏珍(2002)、牛沖槐(2006)、孫健(2007)等對人才集聚內涵進行界定,綜合來看,人才集聚指人才由于某些因素影響,從不同區域流向某一特定區域過程(朱杏珍,2002)。
國外對人才集聚研究更多采用“勞動力流動”“人力資本集聚”等表述(王勇,2011),但與國內人才集聚研究殊途同歸。在西方國家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初期,工業企業權衡運輸成本和生產成本,自然資源的鄰近性成為區位選擇重要因素,企業集聚應運而生。在此階段,勞動力較多作為成本最小化因素被納入考慮范圍,人才集聚尚未得到足夠重視。隨著社會的進步, “知識經濟”、“創新型經濟”等時代的興起,科技、知識、創造力、創新成為促進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人才集聚開始得到重視(Mellander和Florida,2014)。
三、人才集聚的動力因素
人口遷移由“推動人離開一個地方的推力”和“促使人進入另一個地方的拉力”共同決定(于斌斌,2012),而人才集聚具有明顯方向性,國家或城市需增強拉力促使人才進入。已有研究也較多從該角度出發,探討人才集聚的動力因素。
國內學者孫健等(2007)在分析中國不同地區人才集聚模式時,將收入、人才環境、教育科研作為相關因素。牛沖槐和江海洋(2008)、徐茜和張體勤(2010)均從環境角度進行了人才集聚分析。前者在進行硅谷與中關村人才集聚效應分析時,著重比較了地理、文化、制度、科技、人才市場五類外部環境;后者基于Lewin的動力場理論,提出影響人才集聚的城市環境因素:人口、經濟、自然地理、生活、制度。與上述學者角度不同,朱杏珍(2010)在早期人才集聚的利益、精神、環境三因素的基礎上,進一步將人才集聚的動力因素分為:宏觀環境因素、中觀組織因素、微觀個體因素,并認為個體因素是人才集聚主要因素。
面對人才競爭愈發激烈態勢,世界經濟論壇(2011)提出采取“國家品牌”戰略吸引人才,具體包括品牌定義、創造友好型移民環境、培育國際公共意識。為構建融合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品牌重塑戰略,Silvanto和Ryan(2014)回顧國家品牌領域文獻后,從驅動人才流動視角出發,分析人才在流動前考慮的問題,據此提出驅動視角下的國家品牌重塑戰略,具體包括:文化的多樣性和包容性,就業、經濟和機會,明確的移民政策和有效的政府管理,人才地理集中,生活質量和生活方式。此外,Johnson(2003)、Solimano(2008)等學者選取全球化、升職潛力、文化的包容性等因素進行對人才集聚現象進行了深入分析。
參考文獻:
[1] Simon C J. Human Capital and Metropolitan Employment Growth[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1998, 43(2):223-243.
[2] 愛德華·格萊澤著,劉潤泉譯.城市的勝利[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2:223-248.
[3] Michaels E. The War for Talent[J]. Jones, 2001, 49(2):37--44.
[4] Gallardo-Gallardo E, Dries N, González-Cruz T F.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alent in the world of work?[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13, 23(4):290-300.
[5] 蔡永蓮.實施優秀人才集聚戰略[J].教育發展研究,1999(1):28-32.
[6] 朱杏珍.人才集聚過程中的羊群行為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2(7):53-56.
[7] 牛沖槐,接民,張敏,段治平,李剛.人才集聚效應及其研判[J].中國軟科學,2006(4):118-123.
[8] 孫健,孫啟文,孫嘉琦.中國不同地區人才集聚模式研究[J].人口與經濟,2007(3):13-18.
[9] 王勇.人才集聚研究綜述[J].生產力研究,2011(9):205-208.
[10] Mellander C, Florida R. The Rise of Skills: Human Capital, the Creative Clas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M].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2014:317-329.
[11] 于斌斌.區域一體化、集群效應與高端人才集聚——基于推拉理論擴展的視角[J].經濟體制改革,2012(6):16-20.
[12] 牛沖槐,江海洋.硅谷與中關村人才聚集效應及環境比較研究[J].管理學報,2008,5(3):396-400.
[13] 徐茜,張體勤.基于城市環境的人才集聚研究[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0,20(9):171-174.
[14] 朱杏珍.人才集聚的動力因素分析——以浙江省為例[J].社會科學戰線,2010(1):280-282.
[15] 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talent risk-seven responses [EB/OL]. http://www3.weforum.org/docs/PS_WEF_GlobalTalentRisk_Report_2011.pdf
[16] Silvanto S, Ryan J. Relocation branding: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ttracting talent from abroad[J]. Journal of Global Mobility, 2014, 2(1): 102-120.
作者簡介:范耀元,女,山西人,1991年,西藏大學,助教,研究方向:風險管理與城市不動產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