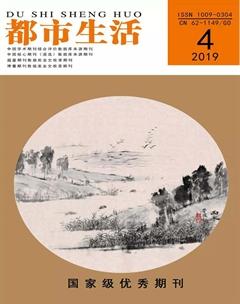逃不出的“時間之獄”
邱正儀
摘 要:“時間之獄”和“純粹時間”是俄裔美國作家納博科夫提出的一種獨特的時間觀,在他看來,時間是一座環形的監獄,并且沒有出路。這種時間觀在他的多部小說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微暗的火》也不例外。本文結合作家對時間獨特的理解,尋覓作品中時間的痕跡,探究身陷牢不可破的"時間之獄"中的人的生存和生活。
關鍵詞:《微暗的火》 時間之獄 純粹時間
一
作為20世紀重要的后現代作家之一,納博科夫獨辟蹊徑,大膽嘗試寫作技巧創新實驗,而《微暗的火》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面貌出現在讀者眼前,使評論家措手不及。譯評普希金的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的經歷給了納博科夫全新的創作靈感,將前言、一首四個篇章的長詩、評注和索引編織在一起,直觀地沖擊著人們對“小說”一詞的傳統認識。
《微暗的火》被公認為是納博科夫所有作品中結構最新奇,設計最精巧的一部。眾多學者針對該小說各式各樣別出心裁的技巧運用做了豐富而深入的研究和總結,并通過解剖式的挖掘,正如納博科夫希望讀者“把它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細細咀嚼”那樣,品嘗到其稀有的香味。對于普通讀者來說,閱讀《微暗的火》絕非易事,這主要是由于納博科夫以其驚人的語言天賦天馬行空地玩轉筆下的文字,對細節精心安排,融合影視效果諸如蒙太奇、長鏡頭等,加之對各時期文學作品的諳熟于心使得他運用戲仿手法時得心應手,活靈活現。這一系列高難度藝術手法使得讀者在初讀作品時深感力不從心,跟不上作家的步伐。如果說《洛麗塔》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表面的戀童內容和曲折的出版道路引起了人們的好奇心,《微暗的火》則充分證明了納博科夫作為一名嚴肅的文學大師天賦異稟的藝術才華。寄托在光怪陸離的形式外殼上的,是厚重而深刻的文學價值以及納博科夫對世界、人生獨特的感悟和見解;如同一塊高檔機械表,隱藏其內部的,除了精密精準的結構,同樣重要的是它所呈現的永恒主題:時間。
著名的納博科夫傳記作家布萊恩·博伊德在《納博科夫:俄羅斯歲月》中認為“時間,而不是空間,是納博科夫的真正主題。”(博伊德 248)納博科夫在作品中鮮有關于時間的系統論述,而主要是借助小說自身對時間的顯現來呈現其獨特的時間觀。
二
納博科夫的“純粹時間”是比一切空間化的時間更為本源的時間,它不能被表象為某物,也不能再被還原成別的什么。在《微暗的火》中,納博科夫運用“湖”這一意象來隱喻時間的本源狀態。麥卡錫曾指出:“湖——原始人最先使用的鏡子,在整個故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Routledge 83)在謝德住所附近,有三個連體湖:Omega,Ozero,Zero。這三個單詞的所指都是“終結”或“虛無”,表明此文本正是處于時間的終點(或開端)。正是這種終結或者說對線性時間觀的超越使得過去、現在和未來能夠以共時性的姿態出現在同一文本境域之中。站在時間本源之處,所有一切都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樣子。納博科夫的文本世界進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之域,我們在其中也感受到了自由的召喚:“我覺得全身通過時空在分向四面八方:一只腳在山頂上,一只手在水流湍急的海灘卵石下,一只耳朵在意大利,一只眼睛在西班牙,洞穴中,我的鮮血;群星里,我的腦漿,我那三迭紀里悶聲悸動不已;綠色光點閃現在那上更新世,一陣冰涼的顫抖貫穿我那石器時代,而所有的明天皆在我的肘部尺骨端。”(26)此時,人仿佛成了深藏在宇宙深處的一只眼睛,曾經我們困于其中的人世間滄海桑田的變幻此時被我們盡收眼底。在這一瞬間的變幻中,我們突然掙脫了線性時間與空間的束縛,視線可以自由地停留在歷史的各個時期、世界的各個角落。過去、現在、未來不再是一股抽象的時間之流沖卷過我們的身體,而是成為我們斑駁陸離的生存之域,我們這空虛的、永遠未完成性的存在就在這以過去、現在、未來構成的境域中展開我們的生存。小說文本那看似支離破碎的片段正是過去、現在、未來投射在我們存在背景上的斑斑點點的影子,我們需要在這背景上動態地建構我們自己的世界。跳出了線性時間觀的納博科夫不會用有連續關系的時間序列,如同撰寫生平傳記一般描繪詩人謝德以及自稱為贊巴拉國王的金波特的生活,按照某種順序排列他們的活動,因而使得文本呈現出碎片性、不完整性的特征。
三
在《說吧,記憶》中,納博科夫寫道:“我曾在思想中返回……到遙遠的地方,在那里摸索某個秘密的出口,但僅僅發現時間之獄是環形的而且沒有出路。”(11)沒有出口的“時間之獄”將人們禁錮在每一個特定的“現在”,使他既無法抵達“過去”,也不能擁抱“未來”。《微暗的火》中的金波特面臨的正是這樣的境域,作為一名在現實工作生活中遭受排擠的同性戀學者,眼下的生活苦澀難耐,他極度需要一樣東西來幫助他逃避現實,那就是謝德的詩。通過描繪虛構贊巴拉國度以及同性戀國王,金波特企圖將自己的性傾向合理化。在謝德的詩篇未被揭曉以前,金波特已經在頭腦中一遍又一遍地建構詩篇的面貌了,因此未完成的《微暗的火》可以被看作是“未來”,它充滿無限希望和想象力。可惜的是,正如納博科夫所說的“未來不存在”,因為未來只是不可被實現的可能性,毋寧說是“絕對的虛無”。完成的詩篇——即“現在”注定達不到金波特的期望,預示著金波特不可能擁有想象中的“未來”,于是他轉而投入“過去”的懷抱,通過對詩篇編注,將想象中的美好過去融進現實的詩篇來超越時間,戰勝時間。然而,正如絕大多數其他納氏小說的主人公一樣,金波特因置身于危險的本源時間中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種精神病狀態,從一封由華茲史密斯學院英文系主任執筆的公開信中可確認金波特患有神經錯亂癥的事實,這種病癥使得主人公時常體驗到出離自身的感受,而這也是他獲得同一性的方式,正是這種感受讓他意識到了自己存在的事實,既本源時間性的表現。
如果說謝德是莎劇典故中的那個太陽,金波特則是月亮,如今太陽不見了,月亮只有暗淡無光。現實生活分崩離析,精神世界坍塌瓦解,金波特只能借助記憶和藝術形式來短暫重現支離破碎的過去。如果我們對作家的生平稍作了解,不難看出,納博科夫本人也同樣在依靠他的小說重溫他的過去。出身貴族的他在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中飽經風霜,快樂的早年生活與他30多年的漂泊生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是這種長期的煎熬使他逐漸形成了獨特而又帶著一絲悲觀色彩的時間觀。無論是《洛麗塔》中的亨伯特,《瑪麗》中的加寧,再到本文論述的《微暗的火》中的金波特,他們無一例外地對時間持有一種執念,即渴望回到過去,而這種執念實際上也是作家納博科夫本人對時間的一個情結,試圖使“時間”在他的文學作品中得到“永生”。
參考文獻:
[1] 納博科夫. 《微暗的火》. 梅紹武譯. 長春: 時代文藝出版社, 1999.
[2] 納博科夫. 《獨抒己見》. 潘小松譯. 長春: 時代文藝出版社, 1998.
[3] 納博科夫. 《文學講稿》. 申慧輝等譯. 上海: 三聯書店, 2005.
[4] 海德格爾. 《存在與時間》. 陳嘉映、王慶節譯. 上海: 三聯書店, 1989.
[5] 納博科夫. 《說吧,記憶》. 陳東飚譯. 長春: 時代文藝出版社, 1998.
[6] 譚少茹. 《納博科夫文學思想研究》. 武漢: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
[7] Routledge & Kegan Paul. Nabokov: The Critical Heritage. Norman Page, 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