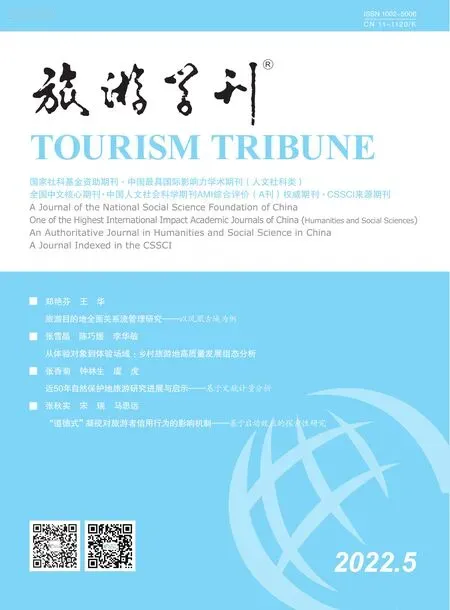經濟換擋期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旅游利用與產業的高深演化
金準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19.05.001
當前,我國經濟正進入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過渡的階段,年增長率從8%左右逐步調換到6%左右,這一變化是經濟發展的自然過程。1960年以來,全球100多個追趕經濟體中,只有12個國家和地區完成了追趕任務,邁過高收入經濟門檻,而這些國家普遍經歷了增速換擋期。中國在2008年前后越過劉易斯拐點,2016年中國經濟增速為6.7%,接近底部,逐步進入中速增長平臺①。十九大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經濟換擋期將是一個相對較長的時期,從國際經驗看,平均為14年,在這一時期,旅游業一般發生結構性的轉變,在這其中,要高度關注非物質文化遺產對產業的深化作用。
一、經濟換擋期是旅游產業質量提升的關鍵時期,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利用的深化期
從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等成功邁過高收入經濟門檻的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經驗來看,經濟換擋期是旅游產業質量提升的關鍵時期,也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旅游產業中逐步深化的關鍵時期,以日本在這一階段(1974-1991年)的發展經驗為例,這一時期具有明顯的“三期合一”的特征。
第一,是旅游產業的穩速增效期,旅游消費質量指標大幅提升。日本在這一階段的旅游業絕對增長速度并沒有隨著經濟增速的換檔而換檔,其總體增長速度基本呈現穩中略降的趨勢,國內過夜游人次年均增長率從高速增長期的6.9%調整到4.9%,入境游人次從11.7%調整到9.8%,基本穩定在上一時期的增長擋位上。而從反映產業效率的國內過夜游的人均消費指標看,從1.66萬日元攀升到3.94萬日元,增長了2.34倍,旅游總消費上漲了5.89倍,旅游人次小幅下降的同時,旅游總消費得到了大幅的提升,經濟的換擋期是旅游業的穩速增效期。
第二,是旅游消費的必要化期,非物質化消費深入發展。1963-1973年,包含旅游的文化與休閑消費已經成為日本家庭的第三大消費,僅次于食物、被服與衣服兩項生存型消費,占比8.5%;1974年-1991年,文化與休閑消費超過了被服與衣服的消費,在家庭消費中位列第二,占比接近10%,成為僅次于食物的第二大消費。總體而言,從高速增長期到換擋期,是非物質化的消費日趨剛性的時期,并且,文化與休閑消費本身的非物質化性也在大幅提升。
第三,是旅游業的創新集聚期,非物質文化遺產會對供給側產生活化作用。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的回落和經濟發展重點的調整,旅游業的地位隨之凸顯,清理旅游業的發展障礙,放松市場機制,改革旅游業的運行機制因而成為發展的重點,市場也因之回以大量的創新,1974-1991年,是日本旅游業的改革突破期和創新集聚期,日本在這一時期出臺了《關于為確保中小企業開展事業活動的機會、對大企業的事業活動進行調整之法》《90年代旅游振興行動計劃》《海外旅游倍增計劃》和《旅游交流擴大計劃》等法律和規劃,松開了管制之手。以市場化和國際化為基礎,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旅游業的利用得到深化,大大活化了旅游業的供給側,成為日本旅游產業轉型的重要推手。20世紀70年代,日本首次提到“文化立國”,提出日本已經從“經濟中心的時代過渡到了重視文化的時代”;1975年,日本深感運行25年的《文化財保護法》已難以適應中速發展期的發展需要,對其進行大幅修改,豐富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體系;1979年日本開啟“一村一品”運動,緊接著1991-1992年,日本制定了《關于靈活運用地方傳統藝術和技能等開展活動以振興旅游和特定地區工商業之法律》。更重要的是,這一時期,日本迪士尼樂園開始興建,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美國迪士尼總部不參與運營的度假區,日本經營方將外來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本土經營文化深入結合,成為全球主題公園本土創新的范本,這充分體現了日本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和旅游產業結合的能力。
二、中國旅游業的增長紅利面臨歷史性轉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深化利用將助力其轉變增長方式
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總體上看,中國旅游業高速增長的特點仍在延續,但新的結構性變化已經產生,中國旅游業面臨增長要素的歷史性轉換,前一階段支撐中國旅游業快速發展的關鍵要素正在相繼發生變化,亟待轉換增長方式,而這有賴于非物質文化在旅游業的深度利用。
第一,宏觀增長紅利消散,有賴于尋找新的增長動能。長期以來,中國旅游業的增長依托于整體宏觀經濟增長的紅利,進入換擋期,政府主導產業的能力、居民收入增長支撐旅游需求的能力、產業綜合風控的能力都有下滑的可能。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國旅游業亟待尋找新的增長動能,這種動能必須是市場性的,能降低旅游業對政策驅動的單極依賴;是深度型的,更多地依托消費升級而非市場規模的增長;是內源型的,能帶來乘數性的增長,基于文化,通過對非物質文化的深度挖掘帶來的效率增長是重要的增長來源。
第二,土地和資源、人力成本快速上升,需要建立知識密集型的旅游經濟。快速增長期,中國旅游業享受了低成本地獲取和使用土地、資源、勞動力的紅利,這一情況已發生改變,相對而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使用價格依然處于低位,開發潛力巨大,對其進行深度開發,有助于建立高附加值、知識密集型的新型旅游業,對沖傳統要素價格的上升。
第三,投資性質發生轉變,旅游投資有待“軟轉型”。隨著中速時代金融環境的變化,高投資、高標桿、低收益的旅游投資將大為減少,旅游投資將進入實質和理性增長時代,這其中,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深度活化利用,將推動旅游投資由硬而軟,由淺而深,由規模型向效益型轉變。
從轉變旅游業的增長方式的角度,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深度利用,將帶來旅游業的幾個重要變化:第一,以規模增長為主,轉向效率提升;第二,從硬資源投入為主,轉向軟資源深挖;第三,以勞動力依賴為主,轉向知識依托;第四,以物質資源的直接轉化為主,轉為文化資源的深度開發。
三、依托改革和創新,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深化利用
我國旅游業一直具有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結合的傳統,但這種結合,與高速期的旅游業發展模式緊密捆綁在一起,其發展依賴宏觀增長紅利,依賴政策主導,依賴土地、資源和勞動力的低成本,依賴大投資的持續導入,導致市場發育不完全,良性的增長格局和收益格局遲遲沒有形成,要依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深度利用,突破高速期的旅游業發展模式,推進新的增長模式的形成,需要實現多層次的結構性破題,其核心在于三個方面:
第一,依托改革,提高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轉化效率。這必須要求產業的增長轉向基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效率模式。據宋瑞的測算①,2006-2015年,我國旅游業全要素生產率平均增速為5.6%,但其中,創新積累深度嚴重不足,對應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旅游利用方面,面臨淺層次(以直接轉化為主,文化深化程度和科技結合程度都比較低,復合性、體驗性和延伸性都較差),高負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利用一方面享受很低的直接使用成本,另一方面在其轉化過程中又面臨著資源、用地、能源、融資等多方面的高成本問題,保護和開發都難以維系),非充分(政府主導型戰略一方面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旅游業的廣泛利用,另一方面也在產生低效率的問題),低替代(業態升級緩慢,產品替代頻次低)等多方面問題,亟待改革破題。未來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旅游業利用,應該重視三個“注重”,即注重改革對于生產力的松綁,注重市場對綜合創新力的激活,注重知識與科技對產業的結構性進化。
第二,圍繞市場,推進旅游文化消費的深化。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旅游業結合,已經成為中國旅游消費的重要形態,但消費的深化仍然不足,文化附加值依然較低。旅游文化消費的深化,核心是如何建立適應需求的供給。當前,旅游需求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正在走向新的人口世代的主導,走向消費者更具主權的社會,走向越來越難以滿足的市場需求,面向趨勢性的升級和結構性的降級并存的局面,快速增長期相對剛性的供給體系,難以應對新的市場變化,供給要適應彈性化、柔性化、快速化的變革需求。
第三,拓展發展邊界,建立前沿拓展型的創新模式。現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旅游利用,以從旅游先發展國家習得的跟隨式模仿居多,隨著中國旅游業逐漸步入世界旅游業的發展前沿,可借鑒的他國發展經驗越來越少,下一步要自主開拓新的前沿,需要商業模式、創新模式和人才模式的大轉換。
總之,經濟換擋期對旅游業的定位,應該是從高速環境中的規模產業,轉變為中速環境中的高深產業,這體現在“6個高”和“4個深”上:第一是經濟效益高;第二是效率高;第三是附加值高;第四是正外部性高;第五是滿足人民群眾需求的程度高;第六是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占據上游;第七是深入,深入支撐經濟;第八是深透,通過改革全面盤活要素、激活生產力;第九是深度,深度與生態契合,深度與文化融合,深度與科技結合;第十是深刻,深刻影響社會民生外交文化。而這其中,非物質文化遺產能通過在旅游業的深度轉化和利用,推動中國旅游業新的增長方式的形成,推動產業向高深轉化,是下一階段旅游業發展的重要一面,其改革和創新,特別值得我們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