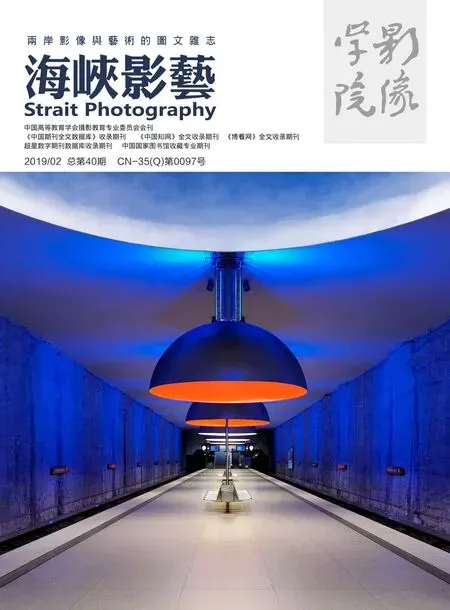柔軟的理性
——讀羅蘭·巴特《明室》

很早以前就曾經(jīng)聽說過羅蘭·巴特的《明室》一書。但一直對于理論界特別是受當代西方哲學界語言論轉向影響后,理論文章普遍由現(xiàn)象分析到現(xiàn)象呈現(xiàn),懸置本質;同時導致語言艱澀冷峻的做法持異議,因而不愿過多的接近。最近因為一個偶然的機遇拾起了這本小書,不僅為其深刻的理性洞察力和情感充沛的敘理方式感到深深折服。原來理性不一定都是咄咄逼人,或者冷冰冰據(jù)人于千里之外的,它完全可以是微笑著接納來者,象一張柔軟的床墊。
最深刻的道理往往蘊籍于最深沉的情感之中。
最冷靜銳利的理性分析之前必然經(jīng)過最深徹透骨的情感體驗。
1839年攝影術出現(xiàn)了,人類眼睛的命運從此發(fā)生了變化。生活在這個世界里的人們,無論他們愿意與否,更多的是在還未作好準備的情況下,突然地與一個小孔里的世界不期而遇了。人類的感官從來都不僅僅只是機械的接收裝置而是直接關乎心靈和情感的觸須。當這些從一個小孔里徐徐綻開的世界不斷地擴充著我們的視覺經(jīng)驗時,人類的眼睛和心靈迎來了一頓饕餮之筵。而視覺的盛筵又直接地催生了對人類情感更新的體驗和更深的挖掘。
現(xiàn)代人將如何面對它所引發(fā)的視覺經(jīng)驗的變化?和因為這種視覺經(jīng)驗的改變帶來的情感上的震動呢?一張薄薄的紙片上藏著何種奧秘使人們的眼睛久久無法移開而且心緒難平呢?當觀者不斷放大、不斷逼近審視之物時,除了看到一顆顆化學顆粒外別無他物,攝影的本質退隱到何處去了呢?照片是神奇的,它的神奇之處也同時帶來了人們對新事物的困惑和思考。攝影有別于其它圖像的本質特征究竟是什么呢?
由于社會性的學術規(guī)范總是在強調基本概念和話語的統(tǒng)一性,即學術上的中立和客觀,因此涉及專業(yè)的討論,學術體系要求研究從社會整體立場出發(fā),以一種冷靜的理性來考察對象,并通過使用大量的專業(yè)術語,以其理性邏輯的尖銳能刺穿事物表面獲取真相。而實際生活中,人們大部分的體驗和認識,都是個人化的,從個人立場和視角出發(fā)的。對感性素材的理性提煉并不是一個短暫而機械化的過程。通常的學術性文章看待、分析事物的方式省略了對感受的細細體味和描述,沒有充分延長感性作用的時間,同時也引發(fā)了體驗深度的不夠,匆匆忙忙作出的理性判斷不但可能導致結論的偏狹和膚淺,更使人覺得得出結論的過程是從理性到理性,難免讓人覺得堅硬冷冰,不愿接近。既然攝影本身就是強烈作用于人感官和情感的事物,那么是不是可以有另外一種洞察事件本質的方式呢?
羅蘭·巴特的《明室》一書就嘗試以這樣一種從個人體驗出發(fā)的方式,通過大量感性的素材使情感自身延展的邏輯成為可供理性追尋的線索。作者以一個普通觀者的身份進入一張張照片,竭力地把感性的觸須伸向每一個可能的角落,飽含深情地尋找著個體與照片遭遇時可能發(fā)生的種種情況,從中步步接近那個未知的神秘內核。
《明室》分為上、下兩大篇,分別由二十四篇短文構成。區(qū)別于那些從近處討論技術層面上的曝光、構圖等技術問題,和站在人類學、社會學立場從遠處考察攝影總體現(xiàn)象的書,作者的立場是“攝影的中介”,“試圖以個人的某些情感為出發(fā)點,羅列出攝影的根本特點及一般概念……”以揭示出攝影有別于其它圖像的本質特征。
該書上篇探討了鏡頭、鏡頭前的被攝者、攝影者以及觀者之間的關系;攝影與電影、繪畫之間的區(qū)別;攝影圖象的意義等問題,重點在于提出了一張照片打動人的兩個要素,STUDIUM和PUNCTUM這一對概念:
STUDIUM:知識的表面,根據(jù)自己所受的教育,從普遍知識、道德和文化的立場來觀察對象,這種觀察有熱忱但并不深刻劇烈;
PUNCTUM:刺痛的點,不需要刻意去尋找它,而是它箭一般飛來刺中觀者,主要與個人感受和特殊經(jīng)歷有關,而與普遍性的知識教育背景無關。與此相關的,是偶然的“奇遇”。
這對概念雖然是作者特殊個體經(jīng)驗的提煉,但著眼于人類情感的共通性,任何人從中都能得到具有普遍意義的啟示。在上篇結束時,作者意識到自己雖然給出了關于攝影這種新事物帶出的各種新關系,但是仍然還未找到攝影的普遍特征,在面對照片時,個體的情感經(jīng)歷中還有需要深深挖掘的寶藏。
下篇由作者偶然發(fā)現(xiàn)的一張母親兒時的照片談起,由此緩緩開啟了通往迷宮出口的大門。已逝母親的形象和照片上那個從未謀面的小女孩聯(lián)系在了一起,帶給作者對母親從未有過的的完整印象。羅蘭·巴特意識到了正是照片提供給他了站在一段歷史之外去關注的可能。
于是這張照片成為了作者的阿里阿德涅(希臘神話里給德修斯線團使他走出迷宮的公主)。沿著這段對母親的情感,作者進入了對愛和死亡的思考,發(fā)現(xiàn)了攝影中最重要的特征——即是曾經(jīng)存在過的真實。在除了那些個人經(jīng)驗留意到的細節(jié)(“刺點”PUNCTUM)之外,照片中永恒存在的“刺點”就是時間。
作者認為攝影的研究不能深化,原因就在于它明明白白地擺在那里。從視覺的角度看,影象的本質全是外在的,但它卻喚起了各種最深層次的意義。在揭露了攝影本質后,作者又重新回到照片的表面,再次進行感性的觀察,探求人經(jīng)由攝影被喚醒的情感。發(fā)現(xiàn)攝影引人瘋狂之處在于從中激發(fā)出了愛的痛苦——憐憫——一種具有宗教感的大愛。
作為一名文學家和后結構主義的代表人物,羅蘭·巴特慣用情感充沛的文筆;和看似閑散實際上邏輯嚴密的組織結構。全書無生澀唬人的詞句,用輕松感性的口吻引領讀者進入了一個需要深刻洞察力才能剖析出的內核世界。這是一種柔軟的理性的力量,使觀者在情感無阻礙地宣泄之余得到了對攝影真實的理性把握。
盡管有人認為《明室》忽視甚至削弱了攝影藝術的魅力,但不可否認的是,攝影術的產(chǎn)生首先是給人類提供了一種記錄方式,攝影最大的魅力即是會這種神奇的“魔法”,證明了曾經(jīng)的時間。攝影的證明力勝過其表現(xiàn)力,羅蘭·巴特對此堅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