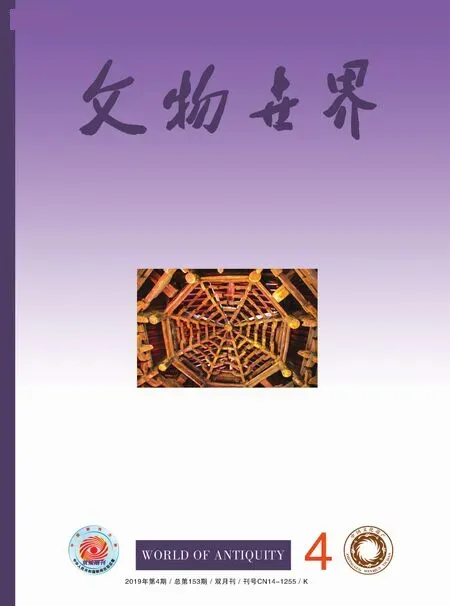漳州祠堂建筑的保護探索和研究
——以漳浦藍氏種玉堂為例
□王豐豐
一、漳州祠堂建筑源流和特點
祠堂作為族人敬奉祭祀本宗族祖先牌位的場所,后逐漸擴演為各宗族的禮法、議事、聚會以及辦學之地。其根據本族中是否出過較高名望的先賢,又可分為家廟和宗祠。作為我國鄉土社會宗法制度下重要的建筑類型,祠堂不僅發揮著宗族載體的重要功能,而且見證著家族族群一生中婚喪嫁娶的各個重要階段。祠堂起源于商周時期的宗廟,歷史上早在商周時期,就開始有祠廟祭祀之制。從河南殷墟發現了目前最早的宗廟祭壇遺址,到漢代正式出現祠堂的名稱,宋代之后受到以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的推崇,于《朱文公家禮》中立祠堂之制,到明中后期“許民間皆聯宗立廟”,至此祠堂在全國范圍內已普遍盛行。
漳州具有十分悠久的歷史。唐垂拱二年(686年),陳元光奏請于泉、潮二州之間設制漳州,州治最初設立于云霄縣西林。同時,在綏安故地設置漳浦縣。開元四年(716年)漳州治移至李澳川(今漳浦縣城),到唐貞元二年(786年),又遷往龍溪(今漳州薌城區),改稱漳州郡。元代改稱漳州路,明清兩代稱漳州府。中原漢族曾四次大規模進入福建,給福建傳播了中原地區的先進文化,也迅速摧動了福建宗族社會的傳播和交融。明清時期,福建成為中國傳統家族制度最為興盛和完善的地區之一,宗族組織也較為發達,家廟祠堂建筑分布十分密集。漳州位于福建的南部,東瀕臺灣海峽與臺灣省隔海相望,絕大多數為漢族,也有畬族、高山族等20多個少數民族。作為著名的僑鄉和臺胞祖居地,漳州旅居海外的華僑、港澳同胞有70萬人。除外,臺灣移民多屬漳州和泉州兩地,尤其漳州許多祠堂與臺灣存在十分緊密的血緣和地緣聯系,使漳州更具鮮明的地域特色以及深厚的文化積淀,其祠堂文化不僅數量眾多,且影響深遠。根據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成果顯示,漳州市共有文物點4731處,其中古建筑有3505處,為總數量的74%,其中古建筑中家廟祠堂就占有1167處,占古建筑類型中的33%,其大多建于明清時期。由于宗祠在族人心目中的特殊意義,使諸多宗祠匯集了營造中最精粹的技藝。其中較為突出的有漳州薌城區的林氏宗祠、漳浦佛曇的楊氏家廟、舊鎮的海云家廟、平和九峰的中湖宗祠、南靖書洋鎮的德遠堂等。因此,漳州地區的祠堂建筑作為宗族社會變遷繁衍的折射和文物建筑技藝的研究和探索,具有十分典型的意義。
在形制特征及工藝特色方面,漳州祠堂建筑與閩南其他地區祠堂建筑相近,多為磚石結構,平面布局多數為兩落三開間,形成門廳、天井、正堂組成的這一相對固定的兩落三開間模式。前落實際為門廳,大門多內縮,俗成“凹壽”。兩側多設一對抱鼓石。后落為主座,即后堂,明間安置祖先牌位,前后落天井相連,兩旁廡廊。面墻墻裙下多砌筑條石,墻裙之上磚砌。在裝飾上,漳州的祠堂建筑較為考究,尤其到了清代,尤重“門面”,精雕細琢甚至華艷,在漏窗、屋面脊飾上多做雕花、彩繪、剪瓷雕等裝飾。根據周躍紅主編的《臺灣人的漳州祖祠》一書中,介紹117座祠堂。有祠堂外觀裝飾的有106座。足見漳州宗祠的重外觀裝飾的特點。“有清一代的民間建筑,因規模形制的限制而將大量的財力、精力投入到細部裝飾上”[1]。
二、藍氏種玉堂概況
石椅藍氏種玉堂,又名藍氏大祖,福建省第七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福建涉臺文物,位于漳浦縣赤嶺鎮畬族鄉石椅村,是閩南地區畬族藍姓的總祠堂。祠堂始建于明嘉靖二年(1523年),原僅門廳、正堂構成。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時任定海總兵的藍理捐俸銀重建,并買下兩側民居拓為祠堂兩廊,取名“種玉堂”,堂號語出“藍田種玉”。種玉堂坐東北朝西南,平面兩進,占地541平方米。祠前有200平方米的鋪石庭埕。種玉堂為土木結構,懸山頂,現由庭埕、門廳、天井廡廊,正堂、左右廂房組成。兩進前低后高,門廳、正堂皆假三川式屋脊,中脊以雙龍搶珠剪瓷為飾,牌仔頭剪粘人物彩繪圖案。高浮雕柜臺腳,石裙堵,鏤花螭虎木構窗。門廳進深3間,面闊5間,前廊懸四組倒垂蓮。位于門廳左側墻體上嵌有一塊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所立“重修祖廟祠碑記”石碑,是祠堂距今為止發現的研究該祠族系流傳淵流最重要的實物性資料,碑文記載了藍氏家族源流、遷徙及建造宗祠經過。正堂七架梁加前后廊,抬梁式結構,花崗石圓柱,下作覆盆式連座礎。后進看架五連枋上一斗三升式,上懸“種玉堂”匾,下設祖宗龕。另前廊中側看架上懸一草書“福”字,傳為康熙御筆,祠中石柱刻對聯六幅,“祠堂聯文是宗族文化的精華,凝聚著宗族歷史、制度、規范和觀念”[2],其內容均與家族源流,裔孫功勛有關(圖一)。
種玉堂作為漳浦藍氏總祠,是中國畬族社區中規模和規格最高的、也是最重要的祠堂之一,并對歷史上臺灣的格局變遷和發展起到舉足輕重作用。“據臺灣省文獻會1977年調查資料顯示,臺灣總人口1695萬,藍姓有31302人,位居全臺灣省姓氏的66位,其分布較為集中的是臺北縣、臺北市、校園縣、宜蘭縣、屏東縣,分布較集中的鄉鎮是臺北的雙溪,桃園的大溪,高雄的岡山和屏東的里港。這些藍姓中有一部分是漳浦赤嶺遷來的”[3]。在種玉堂這500平方米的空間里,記錄著一段段藍氏族人最值得驕傲和稱道的歷史:清康熙二十二年收復臺灣,康熙六十年平定朱一貴起義,乾隆五十二年林爽文起義,均以種玉堂門下為將,出現了藍理、藍廷珍、藍元枚等以武功平定臺灣的人物,以及藍瑗、藍珠、藍璋、藍陳寶、藍璜、藍璣等族下近三十名五品以上在平臺和治臺中戰功顯赫的武官,其中一品大員五人,二品七人,三品五人。“清初著名的政治家,譽為“籌臺宗匠”的藍鼎元,其子藍云錦,后來也遷居臺灣,后裔主要聚居于屏東里港一帶”[4]。這批藍氏杰出的歷史人物,對臺灣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影響都極為深遠。
與其他古建筑一樣,祠堂建筑具有不可再生性。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如何加強保護與合理利用祠堂建筑已成為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本文試以漳浦縣石椅藍氏種玉堂為例,就漳州祠堂建筑的保護利用的相關對策進行探討。
三、保護利用的總體思路和對策
文物法規約束性保護,政府和文物部門政策引導
祠堂建筑的保護工作離不開政府和文物部門進行保護理念的規范和指導。隨著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在民間隨之刮起了一股修祠修墓熱。然而有些民間自發性的文物建筑修繕沒有通過文物部門的指導和審批,往往對其文物保護現狀和文物價值的認識不足,以及無遵從國家對文物保護的相關法規和修繕原則,常自發地任意更換構件,煥然一新,粉刷朱漆,富麗堂皇,甚至改變建筑物原有的形制和結構,從而造成對文物建筑不可挽回的破壞。因此,對本體修繕和日常維護的法規把控尤為重要。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規定,古建筑“對不可移動文物進行修繕、保養、遷移,必須遵守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即對現存古建筑應始終堅持使用傳統的工藝方法,舊材料應盡可能地予以保留。
在對待祠堂建筑的修繕中,我們應以保存祠堂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為目的。以漳浦藍氏種玉堂為例,種玉堂在修繕過程中應在堅持“原真性”原則的基礎上,合理剔除與之相悖的后加元素,如正堂西面山墻后期修建時改為花崗石材質,與此前的夯土墻面不符,可對其墻面進行白灰粉飾,以達到整體風格協調的目的。其次,在古建筑上附加的保護性措施,如造成對文物的破壞或與建筑風格不協調,也應予以修正。
除此之外,文物建筑的保護不能缺少對文物周邊環境的把控。1984年,種玉堂被列為漳浦縣第二批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就此從單純的民間管理提升到了法律保護的范疇,并建立健全文物“四有”工作。頒布之時即確定了保護范圍,即“整座祠堂建筑及門口”,并設立保護標志。2000年8月,由縣人民政府在種玉堂庭埕前豎立“漳浦縣級文物保護單位”保護碑。2007年,將距種玉堂左側約60米的一舊學校改建為“漳臺藍氏暨閩南畬族博物館”(圖二),與種玉堂整合管理。2008年,漳浦縣人民政府遵照申報省級文物保護單位要求,再次下發文件,對種玉堂的保護范圍及建筑控制地帶進行重新劃定,予以了擴大,在范圍線內不得隨意進行設施建設和加高建設,以達到文物建筑和周邊環境的和諧統一。
以族群為代表的社會力量直接參與管理和保護
健全文物保護的社會參與機制,堅持政府主導、多元投入,調動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的積極性,是擴大文物保護渠道,增強社會群眾文物保護意識的重要途徑。2018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文物保護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見》,意見中指出:“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系民族精神,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珍貴財富,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勢資源。”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社會,宗族的凝聚力來源于同一血統,祠堂即基于這種血緣關系而立。從某種意義而言,它是整個宗族歷史的見證者和宗族興衰的載體。祠堂是崇祖觀念和同祖意識作用下的產物,可以滿足每個族人有根可依的心理需要。故在以宗本思想盛行的中國古代社會,家廟祠堂往往在各鄉里村莊占據著一個顯要的地位,在歷史的滾滾車輪下由于受族人有意識的保護而較多地保留了下來。種玉堂歷經500年的風雨,歷史上曾多次重修。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時任定海總兵的藍理捐出俸銀重建,工程由左都督藍瑗、藍珠、藍璜等督造。民國26年(1937年),種玉堂遇火,木結構被焚。同年,旅居印尼的宗親捐資重修。1982年,族人再次全面重修,后又因歷經數次地震災害,墻體等多處損壞,又于1995年、2014年再經重修,其修繕過程得到臺灣、香港、印尼及福建省內外廣大藍氏宗親的大力支持,族群關系成為種玉堂文物修繕和保護的中堅力量。
隨著國家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投入日益加大,政策上更是對省級以上文物保護單位傾斜,但文物修繕經費仍有一部分的資金缺口。需要當地政府和家族宗親共同配套解決,而事實也證實了種玉堂歷史上的幾次大規模維修都是依靠家族宗親的力量才得以完成的。因此,我們應繼續盤活、發揮宗祠的族群聯絡作用,以此作為契緣,可定期邀請海外宗親回鄉尋根竭祖,交流互訪,加強交流,舉辦學術研討會。在廣泛的族群關系中,獲取文化交流和物質財力的支持,共同推動祠堂的保護和外延的文化內涵挖掘工作。在堅持國有和集體不可移動文物所有權不變、堅守文物保護底線的前提下,探索社會力量參與不可移動文物使用和運營管理。
積極宣傳文物保護意義,多形式吸引更多社會力量參與。
除此之外,還可以倡導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參與”的文物保護利用新格局。2019年初,福建省出臺了《福建省鼓勵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實施意見》和《福建省文物建筑認養管理規定》,旨在進一步積極引導社會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工作,建立健全全社會參與文物保護利用的新機制。借此契機,可通過積極宣傳文物保護的意義,增強更多的社會力量參與宗祠類文物建筑保護利用的自覺性。堅持投入、受益相統一,充分尊重文物所有權人、社會參與者雙方意愿,調動除藍氏族人外更多的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文物保護利用的積極性。
盤活宗祠文物資源,加強合理利用
宗祠作為古建筑的主要類型,如長時間封閉沒有使用,由于無法通風,極易潮濕,木結構腐爛。除外,當房屋有漏雨,裂縫等輕微損害時,得不到及時保養維護,極易使病害繼續擴大。因此建議可對修繕完成、具有典型性且歷史價值較高的古祠堂建筑加以利用,如可作為地方族群文化的展示場所,并可用于族群祭祀,對其傳統功能延續和深化;其次,祠堂可辟為老年活動中心,老年人可在祠堂里延續歷史的記憶,借以豐富老年生活;根據宗祠建筑的的優勢及特點,還可作為民間專業性民俗性博物館、保管所或辟為參觀游覽場所,如古建筑技藝展示館、民間書畫展示館、民俗物件展示館等。
以種玉堂為例,可聯合其左側的閩南畬族博物館構筑當地特色文化旅游平臺,進一步加大宣傳推廣的力度,當地政府可繼續完善古祠堂建筑周邊地區的交通、路網等配套基礎設施,重點打造我區祠堂文化游和生活休閑游相結合的旅游路線,使祠堂成為整個畬族民俗旅游村建設的軸心,充分展示畬族民間豐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生活,展示畬族民族特點和特色,在“合理利用”這一主導方針下,拓展文化旅游空間,盤活文化產業資源,以此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四、結 語
對祠堂文物建筑的保護意義在于給后人傳承無法復制的文化遺產,展示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成果,并可充分發揮宗祠作為提升族群凝聚力這一平臺優勢,成為聯系血脈、加強團結的紐帶。這就需要在科學做好宗祠各方保護工作的同時,開拓種玉堂的保護途徑,組織和增強多方力量投入,
盤活宗祠文物資源,加強合理利用途徑。當地政府、族親、文物部門等通過多年不懈努力,使種玉堂躋身于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之列,如今對種玉堂的保護已然走入常態化、法制化的軌道。成績是可喜的。但同時站在歷史發展的角度,我們也應該看到,對以種玉堂為代表的祠堂建筑的保護不能僅停留在保護的本身,而應繼續發掘、提煉并完善祠堂建筑所具有的人文價值,這也是文物保護的主要價值所在。它們是人類共有的文化遺產,應隨著時代的步履走進更廣闊的人群視野中,受更多人的關注和保護。
[1]吳魯薇《明清漳州宗族發展與祠堂建筑》,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年。
[2]郭志超、林瑤琪《閩南宗族社會》,第78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
[3]王文徑等著《漳州涉臺文物》,第42頁,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年。
[4]王文徑《在臺灣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漳浦藍姓家族》,中國文史出版社2017年,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