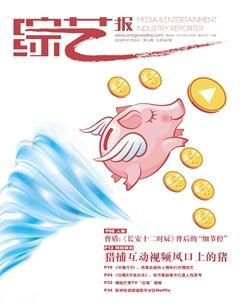對話曹盾:觀眾與創作者“相愛相殺”“相互養成”
《綜藝報》:你說過《長安十二時辰》的主角是“盛唐時期的長安城”,但“盛唐”是個非常璀璨但同時又很短暫的時期,安史之亂后唐朝迎來了轉折點,劇集是否會有這方面的體現?
曹盾:沒有。我們講的就是長安城一天發生的故事,我們在創作初期就確定了一個方向——“只講長安不講唐”。故事呈現的就是一個平民英雄拯救老百姓的故事,我們不需要延展。更多的內容、思考,我們的故事托不住。
關于唐朝的影視作品非常多,如《貞觀之治》《武媚娘傳奇》《妖貓傳》等等,大家更多拍的是廟堂之上、君王的唐朝,但我們重點想拍的就是長安城以及長安城的百姓,展現那個時代普通人的精氣神,我相信這也是《長安十二時辰》的特征和氣質所在。
《綜藝報》:《長安十二時辰》投資規模龐大、制作精細,你認為通過這個項目,是否可以為影視工業化制作留下一套流程或是一個方法論?
曹盾:《長安十二時辰》其實向大家證明了只要尊重觀眾、認真做好項目,就會有好的結果,被觀眾鼓勵、認可。至于這個劇是否可以為未來的影視制作留下一套模式,還需后續更多的復盤,看看是否可以科學地總結出一套具體的流程,為下個項目引入一些更為科學的管理方法。
《綜藝報》:電影常常會強調導演的作者性,相對而言電視劇可能會更加接地氣,尤其在一部商業劇集里,導演的表達空間在哪里?
曹盾:導演更多的工作其實是給項目定一個方向,在我們團隊尤其如此。當接到一個項目,所有人都會問我:導演,咱們這個戲想要拍成怎樣的一種氣質?這時候,你需要有一個清晰的判斷。以《長安十二時辰》為例,我們定下的方向就是盡可能靠近真實。根據這個要求,攝影會去追求光線的真實,服裝會去追求服裝的真實,動作戲導演會去追求動作的真實,演員會去追求表演的真實。不同的部門會在你的要求之下,將工作落到實處。
在內地影視項目制作中,我覺得導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給戲定一個調子,讓大家知道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
《綜藝報》:隨著互聯網崛起,觀眾有了越來越多的發聲渠道,曾經有一段時間業界也一直在探討大數據對于影視創作的影響。在你看來,這個時代,觀眾和導演或者說觀眾和創作者的關系變了嗎?
曹盾:大數據對于未來的創作是有幫助的,它包含很多內容,不僅僅可以為創作提供佐證,也可以為很多工作細節帶來幫助,比如說用軟件檢查是否漏拍了一場戲。對科技的發展要持開放的態度,積極擁抱新技術。
觀眾和創作者始終是“相愛相殺”的關系。作品好,自然會受到觀眾歡迎,反之則會被觀眾拋棄。但從另外一種角度來說,觀眾與創作者也是“相互養成”的關系,一方面觀眾會鞭策創作者;另一方面,創作者也需要有意識地“培養觀眾”。
《綜藝報》:怎么“培養觀眾”?
曹盾:更準確地說是不要拋棄觀眾。比如說,前幾年很流行將題材分類,所謂這是一個男性向的題材,那是一個女性向的作品,大家開始非常功利地為不同的人群提供不同的產品。在我看來,這不是一種創作思路,而是為了謀求某種利益而做出的抉擇。
這樣的創作,等同于拋棄了其他觀眾。就像沙漠里的草木,如果沒有雨水,它看著就像死去一樣;但一旦降雨,它便能馬上恢復生機。如果只給市場、觀眾提供一類文藝作品、那么其他類型的觀眾只能選擇沉默,將自己收縮起來。創作者要真正尊重觀眾,為觀眾提供不同類型的產品,讓不同的人能夠看到不同的內容,而不是只“提供一種飼料”,粗暴地“填鴨”觀眾。
《綜藝報》:現在的團隊從滕文驥導演的劇組便開始成形,團隊的穩定性是否也是核心競爭力?
曹盾:這件事情有兩面。有的項目組、劇組會不斷地尋求新的合作伙伴,這一定會帶來更新的活力和想法,但弊端在于品質不夠穩定。像我們團隊這樣的模式可能能保證品質的穩定性,但弊端在于長此以往,會形成固定的思維和工作模式。我們只能依靠不斷培養年輕人、不斷造血來改善。
《綜藝報》:團隊內部是如何培養年輕人的?
曹盾:通過老人帶新人,在我們內部可以做到知無不言。比如說我對我的攝影,我會把所有的經驗和知識想辦法傳遞給他,同時為他創造一個可以發揮的空間。
在《長安十二時辰》中有一個鏡頭,李必說道:“再也沒有比長安更偉大的城市”,那個鏡頭開始是豎著的后來才橫過來,這就是新人的現場發揮。雖然我和攝影在監視器看的時候都不能理解,但我們還是為他保留了這個鏡頭。剪掉一個鏡頭很容易,但同時剪掉的可能是一位年輕人的熱情。所以,我們會盡量為年輕人創造機會,鼓勵他們創作。
《綜藝報》:下一步的工作計劃是什么?
曹盾:我們目前在籌備一部現代題材劇《再見啦,母親大人》。
《綜藝報》:《長安十二時辰》會有第二季嗎?
曹盾:首先,這得看馬伯庸老師能不能再給我們一個精彩的故事;其次得看這些演員能不能都回來。如果張小敬換了個人、李必換了個人,相信大家的期待值也會降低。其實,我和馬伯庸老師在《長安十二時辰》里埋了一條暗線,就是“何家村”的故事。但具體故事會不會從這個方向展開、怎么展開,還得看項目的后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