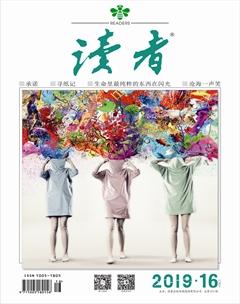壽終正寢
徐文兵
5月9日早晨接到妻子發來的微信,得知我的岳父8日晚上9點在川口家中安詳辭世,享年87歲。妻子怕影響我休息,所以拖到次日早晨才報喪。盡管我早有思想準備,但是悲痛依然涌上心頭。
岳父經營著一家道路橋梁維修公司,一直沒有退休,直到他去世前兩天,還在家中處理公司的事務。去年6月,老人家出現血尿,被診斷為右腎癌伴右腎功能不全,并且有癌細胞轉移。他是我見過意志和精神最堅強的人。我見過的絕大多數病人都是肉身還沒大礙,精神意志先垮掉了。回顧這一年來的經歷,他沒有遭受太大痛苦,就連醫生和護士也都驚訝,他癌細胞廣泛轉移卻沒有出現癌性疼痛。老人家走得很安詳,用“壽終正寢”來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所謂壽終,是指得長壽而終。按照中醫理論,人得天命、盡其天年,應該有120歲的壽命;但因為后天、人為的傷害和不節制,很少有人能活到120歲,多少要打一些折扣。打9折是108歲,打8折是96歲,打7折是84歲,滿一甲子等于打了5折,勉強算是壽,活不到60歲的都不算壽終。所以一般人活到60歲都要慶祝一番,威虎山的百雞宴就是給座山雕過六十大壽。但真正的長壽,至少要過80歲才算。以中國的古禮,80歲以上壽終正寢的,送禮不用白布,而用紅色挽聯、紅帳子,當作喜喪辦。
所謂正寢,就是死在自己家中正屋的炕上或床上,而且死得無痛苦,如同入睡一樣。就是在自己的房子里、在自己的床上睡了一輩子,正常地死在那里。所以,客死他鄉或者死在醫院里——死得很痛苦,插滿各種管子、打著止痛藥,還沒死就痛苦地想著安樂死,那都不算正寢。
中國人講究五福臨門,很多杯盤、字畫上都有五只蝙蝠組成的吉祥圖案,代表五福。據《尚書·洪范》記載,五福包括“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排在首位的是“壽”,排在最末尾的“考終命”就是善終的意思。五福的觀念和排序,代表了中國人的生命觀、價值觀和倫理觀。
《黃帝內經》首篇《上古天真論》一上來就講:“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后來講到真人“壽敝天地,無有終時”,圣人“以恬愉為務,以自得為功,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

近代學者錢穆的祖父37歲謝世,父親終年僅41歲。1928年,錢穆的結發妻子和新生兒子也相繼死去。其長兄錢摯在為弟媳和侄兒料理后事期間,因勞傷過度,舊病復發而亡,年方不惑。家中“三世不壽”,因這些人生變故,加上錢穆本人早先亦體弱多病,他讀書時就頗關注“年壽”之事。他讀陸游晚年詩作,深羨放翁長壽;讀《錢大昕年譜》,知道錢大昕中年時體質極差,后來轉健,因而感悟:“人生不壽,乃一大罪惡。”之后,錢穆在日常生活中注重養生之道,起居規律,堅持修煉,強化生存意識,以掙脫命運的“劫數”。最后,他以96歲高齡辭世。
現代社會,人們的“三觀”與古人的不同。很多人不在乎活得長不長久,而是在乎活得精不精彩。如果在平淡且長壽和短命且燦爛之間做出選擇,他們寧愿選擇像流星一樣劃過夜空,或者像櫻花一樣短暫怒放,迅速凋謝。有些人臨死前會后悔,但是很多人至死也不后悔。所謂求仁得仁,各從其欲,皆得所愿。讓人不能接受的則是,做的是透支精血燃燒生命的事兒,卻同時期望活得長。現在醫療條件好,新藥、新技術層出不窮,但是猝死的中年人越來越多,很多人40多歲就走了,連個壽都談不上,原因就出在生命觀和價值觀上。
至于善終的問題,涉及生命倫理觀。現在很多人鼓噪要通過關于“安樂死”的法律,借口就是不忍心看到病人臨終無藥可醫、掙扎求存的痛苦。我個人強烈反對安樂死,因為這就像授權銀行隨時可以銷毀呆壞賬,不僅不去追究銀行放貸的責任,從而改進工作,反而助長瀆職、貪腐行為。很多患者的臨終痛苦是醫療不當造成的,比如目前美國出現的濫用阿片類止痛藥的問題。不反思醫療倫理以及醫療過失、醫療適當的問題,反而直接一舉終結生命的結果,就是造成更大的醫源性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