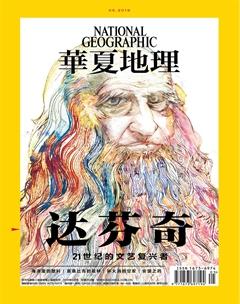古人類DNA偵探
鞠強
現代人類從非洲走出,是目前學術界的共識,但現代人類如何在幾萬年的時間里遍布除南極洲的各個大陸,仍有很多未解的謎團。在出土的化石、文物和存世典籍之外,我們還該從哪里尋找線索?近十年來,王傳超一直致力于回答這個問題。
2018年除夕,一篇研究歐亞草原人群史前歷史的論文在線發表,王傳超為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這項研究歷時三年,共有來自多國37家科研單位46人參與。三年中,王傳超往返奔波于中國、美國、德國和俄羅斯高加索地區,飛成了航空公司的銀卡會員。對于王傳超來說,為科研在野外奔波是常態。2012年,博士在讀的他為調查回民族源,在一個暑假里輾轉中國13個省級行政區,近30座城市,行程20000多公里,從膚白“小鮮肉”變成栗色“小臘肉”。
對于付出,他樂在其中,因為他找到了自己的興趣所在:像偵探一樣,從古人遺骨里提取DNA,通過和現代各個族群進行比較,追溯遠古世界歷史和人類祖先的奧秘。2009年暑假,當時還是海洋生物學專業的王傳超到復旦大學參加夏令營。在這里,他第一次接觸到分子人類學,“我仿佛發現了一個新世界!”——人類遺傳學可以和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等學科交叉綜合起來,一起回答涉及人類起源、遷徙和演化的重要問題。于是,他在本科畢業后來到復旦大學,正式進入分子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之后的王傳超便“開了掛”,從自嘲 “學渣”變成貨真價位的“學霸”,還獲得了被譽為華人生物學在讀博士最高獎項的吳瑞獎學金。
獲得博士學位后,王傳超前往德國馬普人類歷史科學研究所和美國哈佛醫學院遺傳學系做博士后。他記憶最深的是有一次在和哈佛的導師大衛·賴克討論問題時,賴克用手比劃著使勁將鍥子錘入石縫的動作,以此向他說明數據分析就像登山,每一步都要踏踏實實,來不得半點虛假;今年初,王傳超受邀回到馬普人類歷史科學研究所參加會議時,發現自己的照片還被保留在曾經工作過的辦公室門上,他覺得很溫暖。

廈門大學專用于古人類DNA研究的超凈實驗室。王傳超手中的骨頭取自西安幸福林帶,是唐朝初期墓葬中古人的顳骨。
2017年,王傳超入職廈門大學,2018年,剛滿30歲的他成為廈門大學的教授,這樣的履歷在同齡人中很少見,但從事人類學研究背后的困難坎坷非常人所能想象,也許只有他自己才能真切體會。
在多學科交叉研究中,人類學的位置在哪里?科學家希望將分道揚鑣的自然科學與人文重新融合到一起,這同樣也是王傳超努力的方向。他相信,人在歷史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具體到我們自己身上,中國人的祖先從何來、如何來,又是怎樣在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更是事關我們身份認同的關鍵問題。貫穿他研究工作的一條主線正是用人類遺傳學解析東亞人群的歷史。他希望能夠精細地構建出中華民族的遺傳結構圖譜,為中華民族源流提供更多遺傳學證據。
他曾參與對中國男性父系Y染色體大規模的遺傳調查,結果顯示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三個支系快速擴張,奠定了東亞的父系遺傳基礎。通俗來說,就是現今中國一半的男人都是這三個超級祖先的后代,證明漢族甚至是中國人的傳承有著很好的連續性。
除了對東亞地區的關注,王傳超還把研究視野投向更廣闊的空間。2018年底到2019年初,他領導和參與的研究工作成果陸續發表,除前面提到的,還有涉及美洲人群起源和遷徙、波羅的海周邊地區古人基因組和青銅器時代鼠疫桿菌的傳播等不同的內容。王傳超認為,這些橫跨歐亞和美洲大陸的研究看似地點分散,實則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系,可以幫助我們還原出幾千到幾萬年前人群不斷遷徙流動的歷史圖景。
盡管科研任務繁重,王傳超依然要在每學期開學時與自己擔任班主任的兩個班級中的每一名學生聊天。在他看來,發表的論文是現階段探索世界過程中取得的一些進展,而培養學生則是接續人類探索世界的階梯。作為一名研究人類起源和演化的人類學家,他懂得人類認識自己、認識世界都不是靠一代人一蹴而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