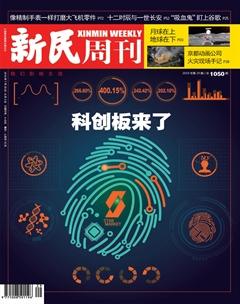唐代宮廷貴婦圖鑒
邵仄炯

《簪花仕女圖》。
最近的《長安十二時辰》熱映,精美的器物,考究的服飾,精致的畫面……又一次掀起一股唐代審美熱。唐朝,或許是每一個中國人心中最綺麗旖旎的美夢。
只要提起唐代的女神,腦海中是不是會浮現起這樣的印象來:胖胖的一張圓臉,豐腴的體態,在那時只有這樣才是大唐的“顏值擔當”。這種所謂的臉頰、體態豐滿的特征在唐以前是沒有的,唐以后也很少見。
那為何偏偏就在唐代出現了這種風格呢?大家不妨一起來讀一讀周昉的《簪花仕女圖》——這幅具有大唐顏值擔當的仕女畫,就可以從中看出唐代貴族女性的美在何處,她們又是如何引領時尚之美的。
從屏風到手卷
先要解釋一下什么是仕女圖。仕女圖是中國人物畫中的一個重要的門類,專以描繪宮廷的貴族婦女生活為題材的人物畫,后來也逐漸擴展到對一般女性形象的描繪。
所謂簪花,是指插花于冠,也就是把花插在云發上。畫面中的五位貴族仕女,她們的發冠上最顯眼的地方都插著一朵朵碩大的鮮花,所以這幅畫被稱為《簪花仕女圖》。
關于這幅畫,有一個點很值得我們關注,就是它前世今生的載體形式。此圖現在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大手卷的裝裱形式,但其實,根據一些研究者分析,以及我對畫面的仔細觀察,可以猜測,這件仕女畫的最初形制很有可能不是手卷,而是一組畫在屏風上的仕女畫。
讀者可能會問,唐代的屏風畫是什么樣子的?我們可以從五代南唐畫家周文矩的一幅重要作品《重屏會棋圖》中清晰地看到當時屏風畫的模樣。唐朝時,人們通常坐在一種被稱為“胡床”的榻上,當時還沒有普及椅子板凳之類的坐具,為了裝飾或者對胡床上坐者的遮掩,榻后面常常會放置一圈屏風。在《長安十二時辰》的電視劇里,宰相林九郎(原型為李林甫)所坐的“胡床”以及其身后的屏風庶幾近之,只是林九郎身后的屏風,畫的是李思訓風格的青綠金碧山水,類似于今天我們所看見的《千里江山圖》。所以有人認為《簪花仕女圖》原來就是幾條單獨的屏風被擺放在榻的后面,后來有好事者把幾幅畫從屏風上拆了下來,又合在一起裝裱,成為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手卷。
如何可以證明這是屏風畫?從畫面上來看,畫中的幾位貴婦的位置并不在同一條連貫的地平線上,人物有高有低,特別是畫面左端的第二位貴婦,形象明顯小于其他人。似乎與周圍的人物大小相比,很不協調。如果是普通形制的創作,畫家這樣的處理似乎沒有任何的道理和必要。接著再仔細看一下,較小的仕女,以及下方的小狗,還有白鶴,周邊的絹面是不是都有裁切的痕跡?據說在1972年此圖進行了一次重新修復的過程,有人發現此圖為三塊絹拼接而成,而且幾處都有明顯的裁切痕跡。
經過一番論證研究,才有了今天此畫前身是屏風畫的論斷。可以說今天我們眼前這一幅《簪花仕女圖》,是好事者對周昉畫作原始狀態的一次改編,是形式上的二度創作。也許藝術上本沒有真正的眼見為實,藝術的呈現實際上很有可能具有極大的偶然性或欺騙性。
大唐“顏值擔當”
接下來再仔細觀賞下畫中的精彩內容。
圖中一共出現六個人物,其中五位是貴婦,一位是侍女,還有兩只小狗,一只白鶴,這些估計是貴婦們的寵物。畫面的最左端,還有半塊湖石和一株玉蘭花,畫面中沒有任何環境的場面,動物、植物都只是點綴,畫家的精力都集中在了這六位女士的身上。
這幾位貴婦身上有哪些炫目耀眼之處?

《長安十二時辰》的華服美飾。
首先是服飾。唐代的女裝一改前代保守風格,盛行裸露的裝束。像今天街頭潮女穿的抹胸禮服、吊帶裙,還有露臍裝等,這些似乎在今天已不足為奇了,但在古代女性的著裝上,唐代的開放是前朝后代都沒有的。在《長安十二時辰》中,無論是宮中貴婦,還是王宗汜將軍的女兒,乃至開香鋪的聞染,幾乎都穿過類似這樣的抹胸裙。正如此畫中的貴婦,身著低胸的長裙,而且裙腰提到了腋下,遮住了腰身,充分顯示了當時以豐盈體態為美的時尚風潮。長裙外罩著半透明的薄紗,肩上還有披肩,這些應該是當時被認為最奢侈的絲綢制作的。而且絲綢的紋樣、款式各不相同,絕對算得上是上流社會“白富美”們的低調奢華了。有兩句唐詩來描繪當時的時尚女裝最合適不過——“慢束羅裙半露胸,綺羅纖縷見肌膚”。
看完服飾,再來看一下貴婦的妝面。畫中女子豐盈的臉頰上都有著厚厚的粉底,但這個粉底并不是均勻涂抹,而是額頭、鼻梁、下巴三處更白一些,這就是人物畫的“三白法”,尤其仕女畫在畫臉時的一種技法,會在臉部最突起的部位加染白粉,來體現臉部的立體感。
同時,女子的眉毛也有些特別,兩片濃而粗短的眉毛,形狀像飛蛾的羽翼,也就是非常有名的“蛾眉”。蛾眉一般以青色來點染,所以又稱之為翠眉。可見唐代的化妝師很會發現自然中的各種美,并善于應用到生活中去。
在貴婦面容的眉心正中還有一點小裝飾,叫做花鈿。花鈿是古代女子臉上的一種花飾,有紅、綠、黃三種顏色,以紅色為最多,以金、銀制成花形,貼在臉上,是唐代比較流行的一種裝飾。這里有個典故,據說南朝宋武帝女兒壽陽公主一天臥在殿角的廊檐下休息,梅花落在她的額頭上,先前覺得有趣不在意,后來怎么抹也抹不去,經過三天的清洗,花瓣才落了下來,但留下了梅花般的印記,美極了!宮女們都覺得神奇,于是也紛紛效仿,后來這種妝飾被稱為“梅花妝”。這一點,在電視劇中,引起長安城一陣追捧熱浪的著名歌女許鶴子的裝扮,就很接近。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發型與發飾。畫中貴婦將濃密的青絲挽成華麗的發髻,高聳在頭頂,猶如一片云彩,所以也叫做云髻。在云髻的發間,還有著滿頭華彩的飾物,一種是在發髻前方,畫家用金粉描繪出不同花飾的金步搖。這種發飾插在發髻中,行走時,一步一搖,非常嫵媚招搖。此外,五位貴婦還在頭上分別插著大朵的芍藥、海棠、荷花、薔薇和牡丹作為裝飾,華貴之極。如果再細看,畫面上形象最小的那位仕女,頭上戴的花冠其實是最華麗的,連侍女的扇子上都是大朵的牡丹,可見她的地位應該最高。
唐代詩人白居易早在《長恨歌》中用了七個字:“云鬢花顏金步搖”,將唐代仕女們風流的形象高度概括了出來。今天欣賞此圖,也許就可以將對白居易文字的想象與視覺的真實合二為一了。
“周家樣”仕女
周昉是唐代重要的人物畫家。在北宋宮廷所藏繪畫作品的著錄著作《宣和畫譜》中記載,說他是一位貴族出身的公子哥,會經常見到上流社會貴族婦女。他筆下的美人圖多以豐滿的體態作為重要的審美標志。畫史上說他“傳寫婦女則為古今之冠”,所以后人稱他筆下的人物形象為“周家樣”,就是完全有自己人物畫的特點。這也是對他藝術的極高的評價。
在《簪花仕女圖》中,除了對人物裝束進行了豐富的細節描寫外,他的高超技藝還在于成功表現了紗幔和肌膚的質感。大家可以特別留心地觀察一下畫中貴婦的手臂,在紗幔的遮掩下的色彩變化。遮掩下的手臂顏色比裸露在外的膚色深,又比薄衫下的顏色淺,生動地將肌膚的滑如凝脂和紗幔的薄如蟬翼再現了出來。

周昉《雙陸圖》。

《揮扇仕女圖》。
此畫經歷了千年流傳,至今依然光彩動人,說起來還得拜古人畫材顏料的鮮亮所賜。明艷的石榴紅來自于朱砂,青翠的綠來自于綠松石,耀眼的黃來自于雌黃,還有一塵不染的白來自于白土和蛤粉。
在《簪花仕女圖》之前,人物造型還是偏重于符號,是一種意象的概括,作者還沒有過多的細節描繪,畫中的女性與觀者視線保持著一種適當的距離,這種距離讓人們體會到一種含蓄朦朧的意象之美。而今天大家面對《簪花仕女圖》,不僅看到了她豐盈鮮活的身姿,還著迷于貴婦身上所有的細節,肌膚的圓潤,薄紗的透明,發式的華麗,還有花鈿、蛾眉的奇美,這是一種近距離的視覺審美體驗。
周昉此圖,無論是今世的手絹還是前世的畫屏,畫中的美人沒有與觀者交流的渴望,她們各自獨立地擺出了展現華服美飾的各種造型,讓人覺得都更像是今天一個時尚發布會,作為此次秀場模特造型的設計師,周昉想展示給大家的是那個時代女性以豐盈、華麗、富貴為美的風向標。以此來印證《長安十二時辰》的許多服飾、造型與裝扮,頗能看出盛唐時代的審美在今天藝術作品中較為忠實的還原與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