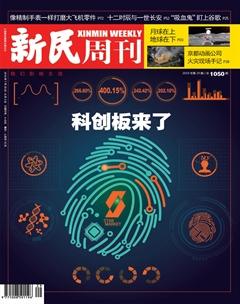面向未來的程十發
王悅陽
一旦進入程十發的藝術世界,其研究角度之廣,立意之深,令人驚嘆。可以說,程十發先生所給予后人的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藝術寶藏,宛如大江大河一樣,有著非常充沛的藝術源流。而后學者、研究者順著每一條支流走下去,則或許可以貫通中國繪畫史甚至中國文化史的滾滾長河。

程十發作品《小河淌水》。
與此同時,放諸大時代的背景之下,程十發跌宕起伏的際遇,飛揚與落寞的命運,智慧與幽默的交融,無奈與痛苦的交織,渺個人而重藝術,輕小我而重情懷的格局……也是其能取得如此博大高深藝術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研究程十發藝術的過程中,千萬不能忽略藝術家在作品中所表達的情感、情懷、思想與訴求。他筆下的歷史人物、戲曲故事、文學名著、少數民族人物,以及對花卉題材的表現,山水意境的營造與追求……一切人、事、物,其實都有他想表達的含義與深意在,都代表著他自己的好惡、感情、追求和他對人生、對藝術的體會。
毋庸置疑,程十發先生是建國七十年來上海誕生的一位當代畫壇大師。但與此同時,亟待梳理和研究的問題是——在這近70年的時代變遷過程中,程十發對于當代中國畫藝術,對于海派文化,乃至江南文化的藝術定位、影響與較為準確、客觀、精到的評價,究竟是怎樣的?在這里,既有學術性的探討,也需要從繪畫的社會角度去看程十發先生的作品社會性意義。他從一個上海美專的學生到畫連環畫成名的青年藝術家,直到晚年成為上海中國畫院的院長,當代海派畫壇的泰斗,最終成為影響至今非常巨大的藝術大師,文化高峰,其人生軌跡是和時代發展,社會環境與個人性格密切相關的。對于這一點,必須建立在新中國七十年的歷史環境當中思考、投身、考量,乃至定位。
程十發的代表作是什么?似乎很難拿一幅來代表。因為他在美術史上更大程度上是體現了一種整體性風貌,包容性性格,以及深廣性影響,這種繪畫風格是一個完整的體系,文化影響更是跨越幾代人的,而不是一兩件作品。
這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程十發先生的兩位前輩“鄉賢”——趙孟頫和董其昌。放諸中國文化史,趙孟頫與董其昌的思想、理論和藝術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以至于在幾百年之后越來越明顯,令人越來越體會深刻。可以說,程十發先生也正是一個以思想、體系,以及文化影響來取勝的藝術家,而不是純粹以個人風格取勝的,盡管他的個人特點非常明顯,但是他絕不是靠單一的作品來完成自己的歷史地位和藝術定位的。
同時,程十發的藝術體系,也并非是完美無缺的。縱觀其一生的藝術追求,應該說仍舊是留有遺憾的:一是他的晚年,由于環境、心情、健康等種種原因,其藝術沒有能夠再進一步的飛躍,取得更大的輝煌和成績。另一方面,程十發一生沒有完整地總結自己的藝術經驗和藝術智慧,缺乏系統的梳理與概括,對未來的學習者與研究者而言,就失去了第一手的寶貴資料,只能通過他有限的文字稿件,演講記錄,詩文題跋乃至畫語錄上,汲取其藝術智慧的吉光片羽,卻難窺其全貌,令人嘆息。
站在程十發這位藝壇巨人的肩膀上,不忘初心,砥礪前行,通過研究程十發,未來的后學者們或許能更加深入、準確地理解中國畫這門藝術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信息
長三角聯袂打造原創昆劇《浮生六記》
近日,由上海大劇院、江蘇省演藝集團昆劇院聯合制作的原創昆劇《浮生六記》在滬首演。近3小時的演出,以跨越生死的深情摯愛、充滿江南空靈優雅氣質的舞美呈現打動觀眾。
《浮生六記》的故事發生在蘇州等江南城市。作者沈復是清代長洲(今江蘇蘇州)人。他以自己和妻子蕓娘的愛情生活、坎坷際遇寫成的自傳體散文,文筆清雅、真摯動人,有“小紅樓夢”之譽。兩年前,上海大劇院決定將《浮生六記》搬上昆曲舞臺,力邀江蘇省演藝集團昆劇院聯合制作。原汁原味的蘇州故事和江南文化,在上海舞臺上實現“嬗變”,見證了長三角文化資源的充分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