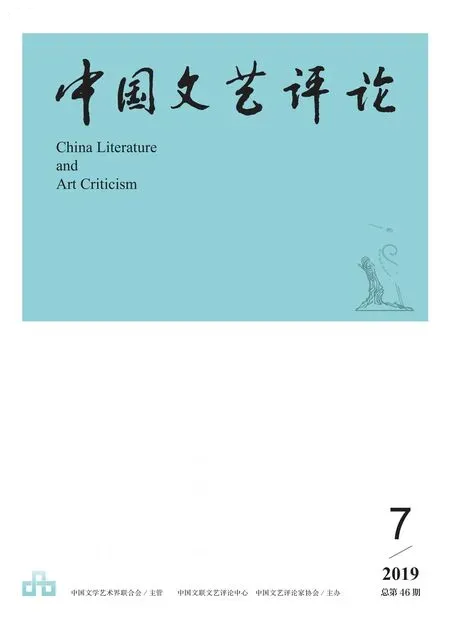互聯網環境下紀錄片的創作與傳播
姜常鵬 李培達
彈幕視頻、微博、UGC內容、短視頻、眾籌等都代表了互聯網時代出現的新文化。這些新型的網絡文化依附新技術特別是多媒體技術,融合進廣泛的社會文化活動中,變革各類文化的既有形態。在紀錄片領域里,原有的形態邊界也被打開,衍生形成許多與互聯網語境更為貼合的呈現形態和運營方式,如微紀錄片、跨媒介敘事、內容眾籌、眾籌點映、資金眾籌,評價標準也由收視率、口碑轉為點擊量、彈幕數量、豆瓣評分、網媒關注度、微博提及量等。可見,互聯網不只是為紀錄片提供了播映和宣傳的平臺,還重塑了它的生產邏輯、傳播方式和讀解方法,讓紀錄片不僅僅是“網絡上的藝術”,而且帶有“網絡藝術”的性征。其中紀錄片的文本內容可以分布至多類媒介,如《風味人間》的內容可以同時散布在科幻網游、網絡直播、電視紀錄片、短視頻、微紀錄片里;受眾則變為積極參與、恣意漫游的網絡用戶,紀錄片的傳播、讀解、盈利范式都產生了改觀。雖然紀錄片影響力和票房的連年增長不可全歸功于互聯網技術與文化的興盛,但它的此種跨媒介形態和運作融合貫通各媒體平臺,將敘事內容分拆至不同類型的文本中,把攜帶不同意義的每一個故事、圖像和聲音廣泛呈現于多種媒介上,給紀錄片發展帶來新的轉機,由此,其背后的動因與意義值得我們思考和探索。
一、網絡化的文本分拆與組合
紀錄片的跨媒介形態和運營首先表現于敘事內容能夠超脫單一的文本而存在于不同類型的文本間,像《我在故宮修文物》《生門》等,既在院線上映,同時也以系列紀錄片的形態于電視、網絡中播出。但是伴隨融合文化的發展,這一跨媒介形態又不停滯于同一個封閉的文本在不同媒介里的直接轉述和傳播,逐漸演化為亨利·詹金斯所說的跨媒介敘事,即一個故事穿越不同的媒介平臺展開,每一個平臺都有新的內容為整個故事做出有差異的、有價值的貢獻,強調作者、文本和受眾間的參與、互動與共享。例如紀錄片《風味人間》的內容會通過美食清談節目《風味實驗室》、微紀錄片《風味原產地》以及《風味之旅》《風味菜譜》、線下“風味食材”推薦、游戲《風味小館》等多種形式得到差異性延展,敘事內容不會像以往的紀錄片那樣在一個文本或是單一的媒介中被受眾窮盡,各媒介上的內容也相互指涉和補充。此種文本內容的分拆能夠連接起電視節目、電影、書籍、游戲、短視頻等,并同紀錄片的核心底本構成一張“文本間網絡”,也讓敘事帶有開放性,具備多種可能的延伸和變體。

圖1 《風味人間》海報

圖2 《風味原產地》海報
具體而言,一部紀錄片的文本拆分在未正式上映前便已開始,因為制作者會通過多種媒介和形式施放與文本相干的差異性內容,受眾得以在多樣化的媒介渠道或文本樣式中獲取相關訊息,甚至參與到作品的生產環節。例如紀錄電影《二十二》未正式開拍前,紀錄片短片《三十二》已在網絡上線并取得極大反響;《我在故宮修文物》上映前發布陳粒演唱的MV。在紀錄片播映后,其底本內容會在不同媒介和形式里得到進一步詳述和擴展,甚至能夠延續到現實生活中,受眾亦會對文本內容進行討論、挪用和重組,讓紀錄片擁有更多樣的文本序列。如《生門》上映之后推出13集系列紀錄片;《風味人間》則更為典型,其內容首先會在《風味實驗室》《風味原產地》《風味之旅》等節目中得到進一步的討論和證實,其次微信公眾號會以圖文形式推送紀錄片的“幕后解密”“風味菜譜”、拍攝花絮等內容,再次,制作方還推出“風味之箸”筷子禮盒,同名書籍,同時每集紀錄片都具備強大的“帶貨能力”,播出后會引發食材的購買風潮,讓觀眾深度參與和體驗紀錄片的內容。
可以看到,紀錄片此類的文本分拆并不是“新瓶裝舊酒”,而是內容的延展與合作,它以紀錄片的文本內容為“根莖”進行擴散,不同媒介上的內容相互促進,形成一種完備、可擴張的網絡化文本體系。其間被拆分至不同媒介上的文本不是彼此孤立的單元,也不駐足于簡單的再媒介化轉述和傳播,它們各自攜帶差異性內容,之間可以進行互相解釋、補充和延伸。這讓紀錄片能夠克服自身在媒介、形式、內容上固有的限制和束縛,打破先前的自足狀態,在新的跨媒介運作中發揮更好的效用。網絡組合式的文本序列也實現了紀錄片內容的跨媒介流動,擴充文本的敘述層次,其中任何媒介上的文本和內容都可作為觀眾進入紀錄片整體敘事系統的一個切入點,從而更好地滿足受眾的個性化選擇。
文本分拆的意義還在于不同文本間可以構成互文關系,同時每個文本都具有自己的裂隙和不足。被拆分的文本及其之間的裂隙為受眾提供了一個選擇和協商的“空間”,改變了以往消極的、接受式的、被規訓的狀態。紀錄片的網絡化文本不但邀請觀眾參與內容生產和意義建構,還為粉絲重組文本提供空間,凸顯了文本本身的“被建構性”。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多樣的文本分拆讓受眾從過去的旁觀、窺視,走向參與,其中充滿裂隙的文本刺激觀眾寫入自己的意義,構建自己的文化,而那些被大眾選擇用來讀解的文本就變成大眾文化,由此推動紀錄片的大眾化步伐。也如布迪厄指出的,大眾文化與高雅文化之間的一個主要區別就在于,大眾文化堅拒美學和日常生活之間的任何距離。紀錄片文本分拆后組成網絡化形態跨越了文本同日常生活之間的界限,制作者也不再以精英身份自居去掩飾從大眾文化中吸取的有益成分,這給紀錄片的生產方式、傳播方式和消費方式帶來轉變。
二、參與式的內容生產與傳播
傳統意義上,文本的內容只取決于文本的生產者,受眾只是內容的接受者和解讀者,而不能“進入”到文本之中。受眾也由此被認為是文本的“囚徒”,即便可以進行多種意義的讀解,文本內容亦不會因他們的需求而發生改變,甚至連意義的生成在伯明翰學派那里也被歸結為文本的收編或受眾的抵抗。同樣,紀錄片跨媒介運營中文本的分拆雖然是作者所為,但多樣的文本類型及其之間的裂隙卻給接受者締造了參與的空間。受眾可以“進入”到內容生產、文本傳播中,還可通過參與來使內容產生特定的變化,如《風味人間》的制作者在知悉觀眾的彈幕內容后從第三集開始增加微觀鏡頭的數量,這樣紀錄片分拆式的網絡化文本也是一種“可進入”的文本。
擱置“真實性”呈現的問題不論,紀錄片領域里受眾的參與性問題在其誕生之初已經存在。早期格里爾遜在領導英國紀錄片運動時就明確告訴其麾下的紀錄片創作者,拍攝的題材必須能促成有知識的公民參與,在他看來,紀錄片的目的不是愉悅觀眾而是促成觀眾的參與。但格里爾遜的“參與”更多是用來促發觀眾參與解決社會問題,甚至迫使政府就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之后尼克爾斯也曾提出參與式紀錄片,這種依據紀錄美學歸類的創作模式對應“真實電影”的理念,關注的是紀錄片創作者在拍攝過程中的直接參與以及被拍攝者與攝影機之間的互動。紀錄片歷史進程中出現的這兩類不同的“參與”也認證了詹金斯所說的,不同形態的文化能夠導致或實現不同方面的參與性。當下網絡文化中每個人都是參與者,盡管地位和影響有所差別,但多樣的媒介形式為每位用戶提供發聲平臺,紀錄片受眾的參與也擴展至文本的生產、傳播以及挪用、重組等層面。
紀錄片跨媒介運營中的受眾參與具備多重性,它包含文本的內容生產和娛樂話題的產業型生產(即話題營銷);粉絲個體文化資本的生產與對象文本影響力的生產。其首先是指生產與傳播過程的參與,其次則是粉絲對文本的盜獵和重組。在跨媒介運作中,紀錄片受眾參與內容生產和文本傳播主要以眾籌的方式進行。如《二十二》眾籌到100萬人民幣的發行資金;《我的詩篇》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眾籌點映。此種超越簡單互動的參與更加自由和開放,滿足了受眾日漸增長的參與需求。同時也讓紀錄片的生產流程和敘事結構由“水平橫向”轉向“垂直縱深”,即通過參與在處于“底層”的大眾和占據“高地”的影片及其制作者間建立溝通的橋梁,使過去未能有效聯系的雙方可以相互交流。唐納德·斯諾登稱此種結構為“垂直學習”,導演柯林·羅將其運用到紀錄電影的拍攝制作中,稱作“垂直電影”,主要特征在于拍攝過程里的影像賦權、敘事活動中個體的顯現以及傳播渠道的多樣拓展。由此紀錄片受眾的參與性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種文化下移現象,大眾正是通過“可進入”的文本將精英化、商業化的敘事轉化為自己可占有的文化。
可以說“參與性”很好地描述了紀錄片跨媒介運營中制作者和受眾間的復雜互動關系,它并不限于某一媒體平臺或某些互動技術,不論在微博、微信、網絡,還是電視和手機中,“參與”是一系列的實踐行為。當接受者通過媒介互動和內容參與滿足自己的需要后便會進入分享階段,參與紀錄片的傳播活動,即分享轉發。因為參與進文本的受眾,一部分參與者可能會出于經濟上的考慮而對紀錄片進行轉發,比如參與《二十二》資金眾籌的大眾自然會主動轉發以得到較大的收益,而更多的人已將分享、轉發視為一種生活方式,當他們看到自己喜愛或是感興趣的內容時便會轉發分享予他人。這與傳統媒體集中控制式的、自上而下的“分發”傳播不同,“轉發”是在普通受眾間無償完成的,其中含有參與、選擇和評價,它將傳播演繹為一個參與者之間共享信息的過程。轉發方式的盛行讓紀錄片的宣傳流程出現自下而上、由草根到主流的反向輸出現象,如《我在故宮修文物》,而《二十二》《岡仁波齊》等則依靠口碑積累、“自來水”轉發和長線效應讓紀錄電影告別“院線一日游”的窘境。正如詹金斯指出的,一旦人們評估某一媒體內容的價值,他們就有助于它在文化環境中傳播,而且在許多情況下會增加其經濟價值。
紀錄片的跨媒介運營還推動受眾走向另一種“參與”,它與眾籌和轉發不同,也不駐足對文本簡單的討論和評價,而是更進一步,對原有文本進行挪用、盜獵和重組,生成他們自己的文本并用以交流和分享。例如粉絲制作的《我在故宮修文物》的文藝Rap,《風味人間》系列的“沙雕視頻”,洋芋攪團版的《情深深雨蒙蒙》、插秧收麥版的《青青河邊草》、流星花園版的《風味人間》等。對文本內容的此種挪用和重組讓觀眾用自己的方式構建與作品的聯系,紀錄片內容則以“二次同人”的形態延展至不同類型的文本上,脫離原先的語境而附加上另類的意義,擴充多樣化的敘述層次。紀錄片跨媒介運營帶來的“可進入式”文本及其多重參與提供了文本內容持續拓展和演變的可能性,也預留了觀眾感知、把握甚至涉入其中的充足空間。此類多重性參與賦予文本更加真實的內容和多元化的形式,讓紀錄片成為萊維所說的“文化吸引器”,把廣泛多樣的受眾召集到一起,催化和促進他們對文本內容進行構建、分享、解讀、重構。繼而讓過去只占有小部分受眾的紀錄片實現更大的社會性,不但使紀錄片集結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也召喚接受者由過去的無視、旁觀或抵抗,走向參與。
互聯網消解了原本涇渭分明的事物之間的界限,無論文本分拆還是受眾參與,它們都依賴于媒體邊界的消釋與融合。如今每一種媒體幾乎都帶有評論、分享的功能,而且可跨媒介進行,為用戶提供互動和參與的可能。從這個角度而言,媒體參與也已成為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這使得紀錄片的跨媒介運作具備“生產使用”的特征,即信息和文化產品在包括傳統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網絡和公共環境中生產出來。縱使當下紀錄片的參與者同制作者還不擁有平等的參與權力,但紀錄片文本的開放參與和公共評價為大眾提供了全新體驗。當受眾在影片上看到自己拍攝的素材和生活時,其以往被規訓或抵抗的狀態,會被從文本內容和媒介參與中所獲得的滿足感削弱,這種效果也會轉化到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如此“可進入式”的文本體驗就延伸到了現實之中,像《我在故宮修文物》播映后,故宮博物院的人才招聘引來大量應聘者,再如紀錄片的“內容帶貨”“內容電商”“文本間商品”等皆是如此。同虛構敘事作品的特別之處也在于,紀錄片受眾的“參與”不局限于內容的生產、文本的傳播和挪用,還包括可真實發生的社會活動,從而建立文本與體驗間的關聯。
三、體驗式的意義生成與流通
其實文化產品,尤其是影視作品的跨界營銷早已不是新鮮事物,例如《星球大戰》《超級女聲》。只是過去的跨媒介營銷更多是出于成本回收的策略,而互聯網語境下紀錄片的跨媒介運營從內容生產階段就是媒介融合的體驗了,再到文本的分拆、盜獵和重組,紀錄片不再是一種單獨關照的對象,而成為一個跨媒介分布的故事或世界,并邀請受眾來參與和體驗。如前所述,被拆分的文本及其之間的裂隙為受眾提供了選擇和協商的“空間”,多樣化的參與讓他們能夠通過自身經歷和實踐來認識文本內容中的事物,由此紀錄片的跨媒介形態和運營是一種網絡化、可進入的文本,更是一種“體驗式”的文本。也可以說,跨媒介運營的意義正在于這種預先安排好了的“體驗”給紀錄片的敘述方式、盈利模式和傳播效果帶來的轉變。

圖3 《我在故宮修文物》海報
首先,紀錄片的文本分拆就像一個“菜單”,觀眾可以從中選取某些特定文本合成自己的意義和快感。德賽都將這種現象比作是文本構造了一個超級市場,讀者可以在里頭游蕩,挑挑揀揀,然后把選出的東西組合在一起,做成屬于自己的“餐飲”。因而文本的不足及其之間的縫隙為受眾提供填充自我闡釋的機會和空間,其中制作者負責“分拆文本”,而觀眾做的是“家庭裝修”。文本的瓦解和分拆讓紀錄片形成多層敘述,如《風味人間》的內容同時散布于清談節目、靜態圖文、微紀錄片、真人秀、網絡游戲和線下食材等不同層次的文本中,彼此間相互聯結,每個類型的文本都可作為觀眾進入整體敘事系統的切入點。分層敘述則造就“游牧式的主體”,它們能夠在網絡化的文本中穿梭往來,尋找和創造迎合自身的意義,讓意義生產變為一個相對持續的過程,能夠被再生產和流通。就像紀錄片文本讀解過程中經常出現的“重聚焦”現象,觀眾只掠走那些對自己有用和有快感的東西,或是轉而關注文本的次要內容。例如《我在故宮修文物》在B站播映時,有的群體關注的是 “故宮男神”王津師傅,有的則對“御貓”情有獨鐘,而其主題曲MV《當我在這里》發布時,彈幕內容多是關于演唱者陳粒。概括而言,紀錄片的文本分拆給予受眾個性化選擇,讓他們真正用個人化視角對內容進行讀解,使其更加貼近個人的真實思想、體驗和感受,從而建立起自我與世界的關系,同時也是受眾參與、衍生品形成、盈利模式轉變的基礎。
其次,紀錄片跨媒介運營帶來的多重參與讓以往處在“弱勢”地位的受眾有機會使用只有專業人士才有資格操控的媒介,深度體驗紀錄片的內容生產、文本重組等,于是此處的觀眾從被動的接受者變為現在的生產者,即意義和快感的生產者。盡管他們的參與程度不太可能超出制作者設定的范疇,相對于先前紀錄片的孤傲姿態,互聯網場域中的受眾已然主動了很多,從而產生更大的快感和極佳的體驗。紀錄片敘事內容是有實際功用的,素材的真實性能夠讓它與社會生活發生切實關聯,因此,參與進紀錄片的敘述內容就能夠體驗到實在的日常生活。例如《風味人間》播出后大眾的購買行為讓紀錄片中的多款美食成為熱銷商品,《了不起的匠人》采用“邊看邊買”的方式,《舌尖上的中國(第三季)》播映后有消費者慕名拜訪王立芳師傅,章丘鐵鍋一度“一鍋難求”。此類文本間商品、內容電商、內容帶貨現象的形成也讓商品變成文本的一部分,成為意義和快感的來源,受眾則具有了多重身份的體驗,是生產者、接受者,同時又是消費者,使得過去只屬于狂熱粉絲的“縫隙市場”擴展至全體受眾,給紀錄片帶來新的盈利范式。
如果說紀錄片跨媒介運營的意義是受眾從文本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關聯性中構建出來的,那么體驗的快感則來自于人們創造意義的生產過程。可以看到紀錄片跨媒介運作里的體驗來源是多方面的:游獵的體驗(在網絡化的文本中獵尋適合自己的東西),參與的快感(同時擁有作為生產者、接受者和消費者的多重體驗),盜獵、重組、分享的體驗(對文本挪用、改寫,賦予個性化的意義)。“網絡化”“可進入”的文本本就是一種具有潛在意義和快感的話語結構,在菲斯克看來,這一話語結構還形成了大眾文化的重要資源。“體驗式”的文本則提供更多切入點,使內容同受眾日常生活的體驗相契合,以便從中創造出大眾化、娛樂化的意義。
紀錄片跨媒介運營的意義生產依賴它為大眾帶來的多樣化體驗,這里的“體驗”也是一種具體文本的接受方式,不同形式和內容的體驗則會帶來不同的感受力。當下互聯網語境里,受眾群的規模變小了,但數量增多了,更不能只將他們視為注意力大眾或群體,須要依靠新技術的力量整合多種品味文化、興趣和信息,為其提供多樣化且具有深度的體驗,以此吸引大眾選擇和參與其中并為之付出。其實當受眾在參與和體驗不同層級的文本時,對紀錄片的意義生產和流通傳播也作出了貢獻。比如只有觀看過《風味人間》后才會更好地理解《風味實驗室》談論的話題,進一步探索美食背后的意義;亦或被某一媒介上的內容吸引后進入到其他類型的文本中。同體驗經濟一樣,“體驗式”文本亦是基于受眾對紀錄片內容的情感認知發揮效用,即便播映之后,體驗的記憶依然會長久保留于頭腦里,增強受眾的忠誠度,利于紀錄片的長線開發。
四、結語
簡單來說,紀錄片跨媒介運營的核心環節是內容在不同媒介中的流動和傳播,以及在接收端呈現出的各種不同的表現形態,其差異性的內容和多樣化的媒介文本為受眾“游獵”“參與”提供空間和平臺。不論這一運作方式背后的動機如何,它正在改變紀錄片生產、傳播和讀解的方式,也推使大眾重新思考自己與媒介、文本間的關系。這一運作范式變遷過程中充滿了機遇和挑戰,問題的關鍵在于制作者、媒介文本以及受眾間關系的重新協商。雖然當下紀錄片的跨媒介運營仍可能是一種不自覺的拼湊或簡單草率的組合,但《我在故宮修文物》《二十二》《風味人間》等紀錄片的成功運作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樣本,它們通過融合貫通各媒體平臺,將敘事內容分拆至不同類型的文本中,由此把攜帶不同意義的每一個故事、圖像和聲音廣泛呈現于多種媒介上,并將各種不同的受眾匯聚到一起,為紀錄片未來的發展提供了新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