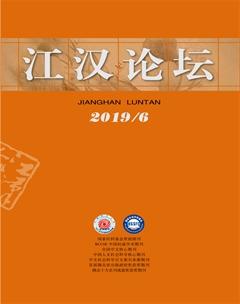從道德自我到生態自我: 梭羅倫理思想的建構之路
鄒建軍 白陽明
摘要:梭羅在自己的一生中融合中西倫理思想,特別重視個人的道德實踐,呼吁個體的精神生活,以獨特的倫理選擇實現了道德的自我建構,從而建立起了自己獨立的人與社會之間的道德倫理關系。在此基礎上,他以個體的倫理責任為起點進行不斷的探索,完成了對生態自我的建構,最終建立起了一種全新的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倫理關系。從道德自我走向生態自我,他對人類缺乏倫理意識和倫理約束力的現象進行了全面反思,為人類在工業文明背景下重建倫理意識與生態世界提供了一種強大的思想動力。
關鍵詞:梭羅;自我;道德自我;生態自我;倫理思想
基金項目:湖北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地理意象與梭羅散文研究”(項目編號:17D040);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美國華人文學與中外文化”(項目編號:04BWW001)
中圖分類號:I206.2?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854X(2019)06-0071-06
亨利·大衛·梭羅不僅是聞名遐邇的美國19世紀自然文學家,也是重要的美國超驗主義哲學家,更因其獨立的倫理思想,而在美國文化與文學史上影響深遠。回到梭羅創作時的倫理現場,按照“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的層深結構”① 思想, 從第一層作品維度,第二層作家維度,第三層作家背后廣闊的文化與哲學維度,可以理出一條梭羅倫理思想之所以生成的線索,能夠回答梭羅倫理思想是如何產生、構成與發展并影響后世這樣的問題。梭羅深受東西方傳統倫理思想的影響,其文學作品深刻地描寫了作家所處的時代,在如實地記錄19世紀美國不同社會階層生活的同時,也反映了由自然文明向工業文明變遷過程中的各種道德現象,并在這個過程中展現了其鮮明的道德傾向。如果對其作品中所描寫的道德活動和道德關系進行審美與科學評價,面對人類現有的生態困境,從理論上進行倫理思考,也許可以解決工業文明給我們所帶來的嚴重問題,從而解決人類的生存和世界的發展問題。氣候變暖、洪水泛濫、海嘯颶風,種種生態災難頻頻發生;大面積地下水枯竭,河流不再行船,泥石流與山體滑坡隨時發生,世界也變得越來越不安全。如何解決這些問題,考驗著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思想家與哲學家。然而,早在19世紀的美國,有一位詩人與作家梭羅,就從美國當年的倫理現場出發,提出了具有開創性的道德自我思想,后來又提出了從道德自我到生態自我的思想,為當今世界所面臨的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一、倫理現場與“自我”的倫理演化
梭羅所處時代的美國,雖然剛剛誕生半個多世紀,卻在從政治到經濟的各個方面發生著巨大的變化。意氣風發的年輕共和國,一邊繼續向西部擴張其領土,一邊快速開展工業革命。重復單一的工業化勞動模式,使美國許多工廠獲取了巨額的利潤,金融資本迅速積累,經濟快速發展。隨著疆域的擴展,革命的深入,美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大增,許多思想家與文學家力圖完全擺脫歐洲思想的羈絆,確立美國的民族精神。而作為歐洲移民最早居住地的新英格蘭,首當其沖成為美國獨立思想產生的搖籃。社會財富的劇增,經濟的快速發展,推進了美國城市化的進程,于是人們走出農舍,離開田野,在詩意的土地上建起一座座廠房與高樓大廈,大多數美國人陷于工業化美夢之中。城市的居民越來越多,人們物質生活越來越富足,然而精神生活卻越來越貧乏。美國人精神空虛,社會物欲橫流,呈現病態,展現給我們的是一個道德缺失的倫理現場。正是因為突然而至的城市化進程,城市居民與鄉村民眾喪失了共同的價值觀,失去了自我精神,丟失了精神家園。在那個時代,社會生活中的世俗化傾向日益嚴重,人們過分追求物質生活,喪失了自己的個性與基本的人性,人們對善的定義也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從而讓許多人失去了自我的道德方向。在作家梭羅看來,19世紀的生活是“不安的、神經質的、忙亂的、瑣細的”②,這樣的生活導致個人走向痛苦與孤獨之中,許多人選擇與社會和自然疏離,失去了對未來的向往與追求。整個時代處于這樣的倫理環境之中,許多美國民眾精神生活貧乏,難以認清自我,于是產生了嚴重的信仰危機。在以傳統基督教為權威的清教倫理和信奉理性的道德作用為圭臬的啟蒙倫理不能解決新問題的情況下,一種新的超驗主義哲學在美國應運而生,希望喚醒美國人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對道德的正確認知。深受歐洲浪漫主義的影響,以愛默生和梭羅為首的美國超驗主義哲學家,試圖從中西哲學中獲取道德資源,建構起一種具有鮮明新大陸特色的倫理思想體系。以梭羅為代表的超驗主義作家,以自己的長期努力,的確是實現了這樣的目標。
從道德主體的層面來看,對自我的理解是倫理學問題的關鍵,西方和中國都經歷了“自我”向“道德自我”發展的“倫理演化”③ 過程,體現了不同倫理訴求下的殊途同歸。在西方哲學中,“自我”是哲學本體論中的核心,西方學者致力于尋求“自我”的本質,一生都會不斷地回答“自我是什么”的問題。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本質在于人的形式,而不是在于人的物理存在,“自我”與物理存在的身體分離,是非物質的實體即“靈魂”,以此出發聯合人的知覺,從而構成了人的特性。沿襲這種身心二元論的傳統,笛卡爾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哲學命題,賦予“自我”以主體性思維,認為自我是一個“在思想的東西”,具有反思能力,從而確立了“自我”的理性主體地位。康德將其進一步發展,認為人的“自我”可以使人與其他生物區別開來。康德的“先驗自我”擺脫了外界的束縛,超越了自身和自然,突出了人類的主體能動性。黑格爾提出“全體自我意識”,認為“自我”與世界相聯系,與他人不可分,區分了自我的三個發展階段,說明了“自我”由個體至他人再至全人類的發展過程。弗洛伊德的“自我”作為“本我”和“超我”的調停人,受到現實環境的約束,失去理智時有道德原則壓制,保護“自我”不受傷害,從而也符合社會需要。隨著西方哲學中“自我”觀念的發展,道德向度的自我開始受到關注,“道德自我”作為善與德性的范疇,獲得了精神主體性和實體性價值。中國傳統文化把自我作為心性修煉的基本目標,試圖回答“自我怎么做”的問題。儒家肯定自我,看重人的社會屬性,認為自我只有為他人和社會而存在時才能實現自身價值,儒家的自我為維系宗法社會里的基本秩序服務。道家關懷個體,看重人的自然本性,認為自我要抑制個人欲望,遠離外物的支配,拋棄是非,忘卻生死,順應自然,內心清靜,道家的自我在對萬物的本質“道”的追求中,達到與道合一的自在境界。佛家克服自我的困惑,擯棄“實我”,否定人性,批判現實社會,認為人生的一切皆是虛無,并且認為人生的一切追求皆無價值,應該超脫生死輪回,信仰彼岸與來世。佛家以至于禪宗的自我只有與“無”成為一體,通過“頓悟”和“妙覺”超越“有”,與宇宙融合在一起,方能達到“天人合一”的“涅槃”境界。中國哲學家們將自我與道德整合,提出“性善說”、“道德說”、“致良知”說等,進行了一種形而上的全新的理性闡釋。在這樣一種思想體系中,隨著自我內涵的逐步充實,自我上升到道德境界,向道德自我演進,“道德自我”作為仁與良知的范疇,有機地統一于人我、群己與天人合一的三維關系之中。
梭羅在西方哲學家耶穌、蘇格拉底和東方哲學家佛陀和孔子的影響之下,從中西哲學對“自我”的理解中吸取必要的養分,通釋古今,貫通西中,以自我為基本出發點,不斷發現自我的新內涵,不僅關心自我是什么的理論問題,同時注重自我怎么做的實踐性問題,以道德自我和生態自我為進路,形成了自己獨立的倫理思想體系,以期能夠如先賢一般,喚醒那個時代許多迷亂的美國人,從而認清自我,回歸正常的個體精神生活,恢復正常的社會倫理秩序。梭羅的道德自我與生態自我思想,不是在空洞的理論中產生的,而是在現實的困難中通過自我的發現,產生并發展起來的。他所處的時代構成了不同于以往的特殊倫理現場,并從美國當時的倫理現場出發,作為一個超驗主義作家的梭羅才提出了道德自我和生態自我的問題。他通過自己的大量作品表明,道德自我可以解決農業文明社會中人們所面對的問題,然而只有實現了生態自我的建構,才能解決工業文明社會中所出現的種種新的問題。因此,探討梭羅的從道德自我到生態自我的倫理思想,不可不考慮他所處的時代環境和倫理現場,在這種不同環境下的自我倫理內涵和倫理觀念,以及這種倫理觀念的發展與變化等重要問題。
二、道德自我思想的生成
西方社會工業文明的發展不斷地使人產生異化,從而發生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和精神問題。西方社會的發展并沒有帶來人的全面發展,反而使人更多地選擇以自我為中心,越來越多的人向片面的、畸形的和單向度的方向發展。反觀梭羅所處的19世紀的美國,人類生活中的社會主體,作為利益主體、權利主體和理性主體而自我膨脹得很厲害。“自知身體之內的獸性在一天天地消失,而神性在一天天地生長的人是有福的,當人和劣等的獸性結合時,便只有羞辱。”④ 梭羅認為,人不能和劣等的獸性相結合,因為那只能帶來羞辱,人只有通過“神性”的成長,即道德的培養,把自己從獸中解放出來,不斷地克服身上的獸性,這樣的人才是有福的,整個社會也才會產生平和與福氣。人的身體里面住著野獸,當“神性”處于沉睡狀態之時,這只野獸就會像毒蛇一樣蘇醒,并且難于驅除。這種獸性,也許會像寄生體內的蟲子,可以在健康時躲開它,然而其固有的“獸性”,卻實在是難以改變的。在這里,“自我”超出了認識論的范疇,具備了一種道德的向度,既具有西方“自我”求“真”的內核,又有中國“自我”求“善”的取向。“人的個體不只是生理性的存在,也不只是心理性的存在,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個倫理性的存在。”⑤ 只有“獸性”的自我向道德自我的方向生成,自我才能由一種生理性的存在,上升到一種倫理性的存在,在道德自我的指引下驅除這種獸性,并且也只有以此為基礎,才能養成一種道德人格,過上一種具有道德感的生活。當個人主體以追求物質利益為目標時,必然會產生身心失衡、道德風險、理論責難與實踐困境。由此可見,道德自我呼喚的是一個道德的主體,一個主體內在意識與物質統一的“自我”。“在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體系中,道德即善,它與惡相對,代表著人或社會的正面價值取向。”⑥ 因此,梭羅“道德自我”的要義在于個體的道德,代表著一種正面的價值取向,一種與“惡”相對的價值取向。梭羅認為美國民族最根本的危機在于道德的缺席,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所有的個體自我都要接受道德的約束,成為“道德自我”。一個“道德”的存在主體是個體生命秩序和社會生活秩序建立的依據,是一種基本的倫理要求,因為道德建構的是自我的精神世界,避免自我精神活動的失衡。如果沒有道德的主體,其結果將是自我身心的失調,人與人和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僵化,只有當自我發展成為“道德自我”,才可以解決美國民眾所面對的種種倫理困境。
在如何造就“道德自我”的問題上,梭羅深受中國傳統倫理思想的影響,主張在遵從自然本性的基礎之上,加強自我修養,保持心靈純凈,從個人身體內部來生成“道德自我”。換言之,就是要求人們通過自我的倫理選擇,來實現真正的“道德自我”。“倫理選擇指的是人的道德選擇,即通過選擇達到道德成熟和完善。”⑦ 人是構成社會的基本元素,以此類推,倫理性存在的作為個體生命的人,當然也就是倫理性社會構成的基本元素。個人在物質和思想方面作為主體,道德的完善來自于道德的選擇,更重要的是將“道德自我”的倫理選擇落實到自己的行動上。愛默生如是描寫梭羅,“唯其因為他完全正直,他要自己絕對自主,也要每一個人都絕對自主……他質問每一種風俗習慣,他想把他的一切行為都安放在一個理想的基礎上。”⑧ 在梭羅這里,“道德自我”的存在與發展,體現在作為作家的梭羅的思想與行動上,既是作為一個作家的梭羅所踐行的,亦是他所提倡的。倫理選擇在他作為生命個體所參加的各種活動中,貫通始終,自覺地做出了道德性的選擇,并以此為基礎,進行全面的善惡判斷。他在自己的一生中,注意協調各種活動,幫助自身發展,從而使道德自我參與到各種活動之中。在他那里,自我總是以道德自我的面相而呈現,從而以此為路徑實現個人所主張的建立道德社會的根本目標。
“道德自我”對人在社會中的要求,不僅是共存的,更應該是共同生活;不僅只是一種理想的物質生活,更應該是一種優雅的精神生活;個體所處的世界呈現為一個道德世界,道德的社會需要個體與個體達成一致。“德行是無法計算的,就像它也難以估價。而人的命運并不是德行或身份。它是全部的道德,只有靠精神生活才能認識。上帝估算不出來。上帝那里既沒有道德哲學,也沒有倫理學。”⑨德性是無法估算的,也不能依靠上帝獲取,要做一個有道德的人,必須擺脫物質生活的誘惑,進行深刻的倫理反思,通過自我的精神生活才能實現。梭羅這里所提到的“全部的道德”,需要對精神生活進行全新的認識,即指通過倫理選擇以獲取基本的德性,以實現“道德自我”。所以他說:“我們的整個生命是驚人地精神性的。善惡之間,從無一瞬休戰。善是唯一的授予,永不失敗。”⑩ 此時,精神成為善惡角斗的戰場,而“善”成為“道德自我”最深層的內涵和最為強大的凝聚力,主體性的“道德自我”也使道德社會的形成,真正獲得了堅實的、內在的基礎。梭羅對道德自我的探索以及對道德自我思想的提出,在那個時代自然具有重要的意義,也是美國以個體生命為本位傳統的一種延續,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發展。然而,隨著作家生活閱歷的增長,特別是伴隨著工業文明發展而出現的種種社會毛病的出現,梭羅日益感到只是建立了道德自我是不夠的,只有在道德自我的基礎上,在建立了一個全新的生態自我之后,從外在的社會到自然,從內在自我到社會,從外在的社會到自然等等所有方面的問題,才可以得到全方位的、根本的解決。
三、生態自我思想的建構
在一般的倫理學理論中,道德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但是,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人們不再滿足于社會資源的積累進步。為了滿足人類的物欲,開始了以人類利益為中心的,針對大自然而發生的瘋狂掠奪。面對日益嚴重的生態困境,自然本身不可能進行選擇,如果人類僅僅依靠倫理選擇的道德自我,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與自然之間所發生的越來越嚴重的問題,所以,梭羅將自我與自然聯系起來,展開了新的倫理探索。“與城鎮里那些依靠滿足極為虛假的社會需求而活并在艱苦時期被解雇的毫無保障的大多數人相比,森林里孤獨的拓荒者和定居者的生活方式更加可敬。他們有真正的難處,而非自尋煩惱;他們直接從大自然汲取生存所必需的養分。”{11} 梭羅認為,大多數人依靠虛假的社會需求而活,而這種生活方式是不能被推崇的,因為這樣的生活方式,遠遠不如在森林里拓荒而居住的人。人類的煩惱來自于過度的社會需求,不管是為了生存還是為了享受,在掠奪大自然的過程中失去了對大自然應該承擔的倫理責任。面對人類為了個人利益而侵襲自然產生的生態困境,梭羅提倡一種能夠深入到自然之中,在自然之中自然地進行生活、思考和感悟,從而重新定位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并由此實現從道德自我轉向生態自我的建構。人類生活的經驗有助于哲學的形成,梭羅的倫理思想的產生也是緊跟自己的時代,并強有力地汲取了那個時代的思想與智慧的結果。
長期以來,西方的人們總是把人與自然分離,人作為脫離于自然的個體而存在。實際上,在東方哲學里,人與自然總是一體化的,人總是作為自然整體的一部分而存在,在中國古代思想家那里,天與人是合而為一的。梭羅在年輕的時期,深受康德主體性道德自我和同時代的作家愛默生的超驗性道德自我的影響,也曾經表達了對二者所主張的道德自我的某種認同。然而在其后的時代里,梭羅感受到康德道德自我形而上學基礎的矛盾,以及愛默生由于過分強調個體自我而忽略了自然在自我中的地位的矛盾,從而轉向東方尋求思想支持。受東方“天人合一”思想的啟發,梭羅認識到自我中的“我”不僅僅指個體的人,也不僅僅指整個人類,其實也包括了人類所面對的整個大自然。出于這種思考,梭羅將“道德自我”發展成為了“生態自我”。他認為道德自我實現的是社會共同體,生態自我實現的則是人與自然的共同體。從自我到道德自我,再到生態自我,實現自我的過程就是逐步縮減所有存在物之間的疏離,擴大自我認同對象的范圍。自我處于社會之中,道德自我生成,自我處于自然之中;生態自我生成,自我存在于所有存在物之中,所有的存在物也就包括自我的存在與形態。
在思考如何實現生態自我之前,梭羅需要厘清人與自然的真實關系。梭羅在日記中通過對詩人生活形態的描述,闡述了自己在面對自然的時候的倫理觀點,“他必須不僅限于自然——甚至是超越自然的。并非是自然通過他說話,而是自然與他同在。……他是另一個自然——自然的親兄弟。他和自然彼此友善地各行其職,都在宣示另一方的真理。”{12} “他”在這里就是指“詩人”。在此,與其說梭羅表述的是詩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如說梭羅闡述的是自然與個體的關系,個體把自然當成親兄弟,將把自然的道德納入到生態自我的范疇。自然是生命的源泉,是個人保持精神獨立性的避難所。只有在自然之中才可以更新人的靈性,也才可以提高人的靈性。自然增進了人的道德,還能醫治在社會中滋生的許多道德罪惡,因為純潔、簡樸而美麗的自然,能夠砥礪我們的道德本性,更新和提高我們的靈性,所以他認為親近自然是人類精神健康的最為重要的因素。所以,他提倡人們要盡最大限度地融入到大自然,因為人類如果融入了大自然,大自然就可以凈化我們的靈魂,從而抑制罪惡的滋生與重大災難的發生。
梭羅對那個時代美國人的社會生活是相當關注的,對人類與大自然的現實關系則是十分擔憂的。他說:“在自然界里,還沒有一個人間居民能夠欣賞她。鳥兒連同它們的羽毛和樂音,是和花朵諧和的,可是有哪個少年或少女,是同大自然的粗獷華麗的美協調的呢?大自然極其寂寞地繁茂著,遠離著他們居住的鄉鎮。說甚天堂!你侮辱大地。”{13}“她”,在這里指的是作家所生活的長達數年的瓦爾登湖。梭羅以嚴厲的措辭對人類破壞大自然和諧的行為進行了批評,從而表明了他的生態倫理觀。梭羅對于工業文明擠壓自然,擾亂社會并侵蝕人心的現實充滿憂慮,面對人與自然相互對立的關系,梭羅將自然納入到自我之中,提出人類應該融入自然,以便使自身的生活內容與生活方式,都可以回歸到大自然的懷抱之中。
梭羅認為,生態自我的實現有賴于人對自然負起倫理責任,這既不是因為人對自然天生具有悲憫情懷,也不是因為自然對人具有的獨特價值,而是因為人與自然本來就是統一的,本來就是不可分割的。梭羅對人與鳥之間的關系,有一段精到的論述。在人類的歷史上,世人與鳥之間的關系,通常是將鳥捕獲關起來,或欣賞,或宰殺,或用作它途。而梭羅卻以鳥雀為鄰居,不是那總是關起來或捕捉到的一只鳥,“而是我把我自己關進了它們的鄰近一只籠子里”{14},將自己和鳥的通常關系進行一次反轉,換一種視角處理人類和鳥的關系,也就是體現了人類和自然的關系。這種人鳥關系的結果,是梭羅聽到了“它們從來沒有,就有也很難得,向村鎮上的人民唱出良宵的雅歌”{15}。這樣的故事及其展開過程說明,人與自然已經密不可分,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新狀態,并且只有這樣,自然才能吟唱出最美的歌曲。對于生態自我的更深層次的論述,來自下面一段更為精到的話語,“還沒有一個人在無思無慮地過完了他的童年之后,還會隨便殺死任何生物,因為生物跟他一樣有生存的權利。”{16} 作為共同構成自然界的一分子,人和其他生物一樣應該是平等的,應該互相尊重,和諧相處,因為生存的權利是生物和人類共有的。之所以提到在“童年之后”,是因為童年之后的人類經過了倫理選擇,并且也是因為經過了倫理選擇才產生了倫理意識,也只有真正產生了倫理意識,才讓人類真正地產生善與惡的觀念,從而才可以獲得真正的理性,認識到其他生物也具備生存權利。也只有如此,人類成員才能做到保護其他生物的生存權,承擔起對自然的倫理責任。從根本上講,人與自然是一種內在的、根本性的生存關系。通過倫理責任,人使分化了的人與自然重新結合在一起,人在這種關聯中獲得一種內在的和諧感和家園感,而自然也只有在這種關聯中才可以重歸和諧,成為人類理想的家園。人對自然的這種倫理責任,要求人類在利用資本的同時限制資本,要求人類在推崇科技的同時駕馭科技,要求人類在擴大生產的同時改變生產,要求人類在刺激消費的同時引導消費。只有這樣,人類才能真正地把自然當作人的一部分,人類不再居于中心之位,生態自我將自我擴展到自然,增加自我的倫理約束力,在工業文明下重建倫理意識,從而建構起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態倫理關系。
四、自我演進之路及倫理思想的重要意義
愛默生曾經這樣說:“正如眼睛是用來看的,耳朵是用來聽的一樣,顯而易見,人是為了社會而存在的”,作家在這里通過一種比擬,說明了人與社會之間的依存關系。雖然愛默生將上帝、人和自然視為一體,但就人類在世界中的角色而言,“更傾向于使人類在世界上扮演一個必不可少的、不斷進取的、具有創造性的角色”{17},人在與社會和自然的關系中居于主體地位,社會與自然的存在是以人為必要條件的。很顯然,這里所體現的是一種以人類為宇宙中心的觀念。與梭羅同時代的杰出詩人惠特曼,堅信自然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在詩作中不斷地歌頌自我、自由和自然,主張在自然與個人以及自然與自我的范疇內獲取個性的解放,然而其落腳點依然是人類自己。作為超驗主義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與愛默生和惠特曼相比較而言,梭羅能夠比同時代的人更進一步,將自我的內涵擴大,并將其內涵進行了全面的發展。在如何生成“生態自我”的問題上,梭羅展示出與同時代的超驗主義者不同的理論視域,體現出一種從實踐出發而又落實于實踐的思想維度。梭羅自我思想的演進,大致經過三個層面:一是個人層面,梭羅在地理漫游的生命體驗中,把握東方與西方歷史上有關“自我”的哲學思想,這是梭羅倫理自我演進的重要基礎。二是社會層面,由于處在19世紀美國特定的社會之中,梭羅的倫理自我呈現出鮮明的新英格蘭地域特色和道德自我的社會需求。三是自然層面,東西方倫理思想對梭羅生態自我的建構影響深刻,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成為人類對自然承擔起倫理責任的應有之義。在他的一生中,三個層面相互交織,相互影響,促使梭羅向道德自我和生態自我的生成。梭羅認為,生態自我生成的實現途徑,是將自我擴展到大自然的實踐活動之中。對于自然的理解,既不能將其排除在人類之外,也不能以精神生活去認同,只能是人類在自然的實踐活動中去認知。在自然的實踐活動中,人與自然互動生成,人類中的每一個生命個體承擔起對自然的倫理責任,人與自然實現了內在的統一,于是整個宇宙不再處于人的存在之外,而是成為人的實踐活動塑造出來的有意義的世界。梭羅在地理漫游過程中對自我有了一種本土性思考,面對19世紀美國存在的道德問題和生態問題,他毫不回避,而是直接地融入自然實踐,在與自然相處相生的種種磨礪中,全面地揭示19世紀美國的生存狀態,針對西方傳統“自我”思想的局限性,創造性地提出自我向道德自我和生態自我的轉換,對歷史上的自我進行了全面的創新,使之內在性地融合東西倫理思想,創造出兼具西方和東方意義的“生態自我”。
梭羅針對以個體自我為中心,拜金主義日益盛行的工業文明時代,針對以經濟利益為動力的人類活動,提倡放棄物質財富的庸俗性,追求一種全新的精神生活,從而建構起真正的道德自我。梭羅是一位文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哲學家。他所有的思想都集中體現在其文學作品中,其獨特的道德倫理與生態倫理思想,也同樣是如此。梭羅并不是一位美國倫理學大家,然而他的確具有獨立的倫理思想,是通過文學作品特別是影響廣大的《瓦爾登湖》和《河上一周》等作品來實現的。從道德自我到生態自我,梭羅實現了對自我的超越,也讓美國的現代倫理思想的發展,實現了一種質的超越。早期的梭羅總是用“道德自我”思想來解決19世紀美國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其思想也達到了相當的高度。然而,面對隨之而來的生態困境,他提出以生態自我來解決美國的生態問題,從而形成了其完整的生態倫理思想。俊羅的生態倫理思想,從總體上來說是對中西倫理思想的融合與超越,是對人類缺乏倫理意識和倫理約束力的深層次反思,“事實上,他才是把田園道德論發展為近代生態哲學的最主要的人”。從道德自我到生態自我,是梭羅為人類在工業文明下重建生態倫理意識所提供的重要思想。將梭羅的生態倫理思想運用于當今世界,可以解決人類放棄道德、放棄生態、放棄倫理規則時所帶來的嚴重問題。梭羅在建構其倫理思想的時候,融通東西哲學,克服西方二元論弊端,攝取東方哲學精髓,尤其是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引領了世界哲學的走向。梭羅關注人類與自然的存在問題,從“道德自我”到“生態自我”,為人類解決生存問題作出了有益的嘗試。生態自我思想的提出與建構,既是梭羅對倫理思想追求的獨到之處,也是其倫理思想的價值之所在。梭羅的生態倫理思想對當代中國應對生態危機,也可以提供重要的啟示。梭羅的生態自我思想表明,人類只有尊重自然、順應自然,才能承擔起對自然的責任,同時也才能擔負起對人類的責任。只有保護了自然,也才能保護人類,才能建立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反過來說,也只有建立了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也才能實現梭羅所提出的生態自我,從而建設一個美麗的中國,一個美好的世界。
注釋:
① 鄒建軍:《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的層深結構》,《世界文學評論》2018年第1期。
②④⑩{13}{14}{15}{16} 亨利·大衛·梭羅:《瓦爾登湖》,徐遲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182、181、167、72、72、177頁。
③ 鄒建軍:《文學倫理學批評理論存在的問題及關鍵詞闡釋》,《當代文壇》2017第5期。
⑤ 樊浩:《中國倫理精神的現代建構》,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386頁。
⑥⑦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247、267頁。
⑧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愛默生文選》,范道倫編選,張愛玲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189-190頁。
⑨{12} 梭羅:《瓦爾登湖的反光:梭羅日記》,朱子儀譯,金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62、29頁。
{11} 梭羅:《緬因森林》,戴亞杰譯,北方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166頁。
{17} 唐納德·沃斯特:《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侯文慈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笫135頁。
作者簡介:鄒建軍,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湖北武漢,430079。白陽明,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漢,430079;湖北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湖北武漢,430068。
(責任編輯? 劉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