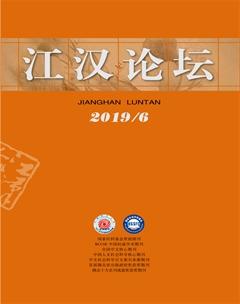曹學程之獄與萬歷援朝東征議和中的朝堂之爭
楊向艷
摘要:御史曹學程因在萬歷東事議和中上疏反對封事及攻擊閣部大臣而惹怒神宗,被逮下獄并處以候監擬斬。鑒于言官因諫言受此嚴懲可謂前所未有,曹下獄后朝堂官員反復申救,歷經十余年方被赦免戍邊。究其下獄之因,既有曹學程任御史期間就神宗怠政、三王并封等上疏批評神宗從而埋下了禍根的遠因,亦有在東事議和中主戰派與主和派間激烈紛爭的近因。在此次紛爭中,神宗為了保證封事順利進行,在支持閣部的同時對反對者極力壓制。東事之初懲處郭實,之后嚴懲曹學程,無不反映出神宗對言官的不滿及打擊他們的決心,這從一個側面揭示了萬歷二十年代初期皇帝與言官之間不可調和的緊張關系。
關鍵詞:曹學程;萬歷東征議和;朝堂之爭;君臣關系
中圖分類號:K248?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854X(2019)06-0093-09
萬歷東征援朝歷時7年,期間有3年多的時間處于議和,此時朝堂上言官與閣部就封事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從一個側面凸顯出朝堂上紛繁復雜的政治局面。作為御史的曹學程堅決反對由神宗支持、閣部主持的議和,并因上《諫封倭疏》而觸怒神宗,被處以候監擬斬的嚴懲。此事在當時轟動一時,盡管神宗欲殺曹學程以泄恨,但大小臣工皆認為曹罪不至死,假如皇上對言官的懲罰如此之重,不僅不利于圣德的展現,還會導致言路不暢,因而極力申救,持續十余年之久。曹學程之獄不僅是萬歷中期君臣關系惡化的一個縮影,背后亦有著復雜的政治糾葛,值得深入探討。鑒于學界對此獄尚未有研究,筆者擬對該獄的具體情況加以探究,以此來展示萬歷中期的君臣關系和政治生態。
一、曹學程的事功及因言下獄
曹學程,字希明,號心洛,廣西全州人。萬歷十一年(1583)進士,歷知石首、海寧。① 在海寧任上“治行稱兩浙最,召拜廣東道御史,督理屯馬”。后以“建言觸上怒,詔逮于獄,擬辟典。在獄者十年,蒙恩得釋,謫遠戍,竟卒于戍所”。② 有《曹侍御忠諫集》存世,由其子集錄,其中保存了他任御史期間所上的四道奏疏,均是對當時朝堂大事的建言,表現出他作為一名言官恪守己任的良好品格,對此,時人蔣以化亦稱贊說“見其篤行,君子也”。③
耿直不屈、敢于諫言的品格讓曹學程榮任言官,同時又給他帶來了災禍。萬歷二十四年五月,東征議和情況有變,前往日本冊封的正使李宗城出逃,神宗大怒,欲派一給事中充使前往勘察情況,并完成封事。對此,曹學程忿然上疏說:“邇者封事大壞,而方亨之揭,謂封事有緒。星、方亨表里應和,不足倚信。為今日計,遣科臣往勘則可,往封則不可。石星很很(狠狠)自用,趙志皋碌碌依違,東事之潰裂,元輔、樞臣俱不得辭其責。”④ 曹所上該疏名為《諫封倭疏》,除收錄在《曹侍御忠諫集》外,還被廣泛地收錄在多種文獻中,成為書寫和彰顯其事功及歷史地位的重要文本。
疏上后神宗大怒,下旨曰:“今差科臣乃是上意,且累朝往封朝鮮、琉球諸國,或內臣、或文臣充正使、付使,今李宗城以紈绔乳子偷生辱命,故欲著一風力科臣前去,一以完封,二以看彼中情形。何君命方下,這廝每紛紛阻撓推諉,好生不忠。且當時每以細微之故喋喋煩擾,欲伏斧鍎不辭,既至委用,又推延不遵,其附和取榮,背君棄義明矣。況奉旨著推科臣,未著御史去,這廝輒來徇私抗違,好生可惡,內必有暗囑關節。曹學程著錦衣衛差的當官校扭解來京究問。”
錦衣衛奉旨將曹學程拿送鎮撫司后,神宗要求好生著實打,著究問主使阻撓之人。⑤ 審訊中曹學程備受嚴刑,被“拶夾,加敲二百,杖四十”。⑥ 錦衣衛王之楨隨后將結果上報,指出曹學程承認他于萬歷二十四年內“因見倭情變詐,關系社稷安危,再遣科臣恐非國體”上疏諫停,“一時詞語過激,致干圣怒”,“并無他人主使”。王之禎遂以“曹學程章句迂儒,不諳大體,濫叨耳目,重寄弗殫。謀國忠猷,意在附和避難,故為臆說以逞。止知倭情已變,封事宜停,獨昧圣意有待而成命當遵,陳言雖云盡職謀國,豈宜狥私?研究主使之人雖無,抗摭違慢之罪難逭”為由,建議將其開送刑部,從重擬罪。⑦
疏上后因為曹學程不承認有主使之人,神宗指責他“傲慢肆言,全無畏敬”,如果他真為國家著想,就應該“效古義勇往辯真偽,以釋大疑”,而不是“專以口吻浮言為忠,抗違避難為義”,好生不忠,同意將其拿送刑部,從重擬罪。⑧ 曹學程遂被轉到刑部,刑部尚書蕭大亨等對其進行了再審,上報情況指出,曹學程“直憨之語太過,疏野之罪難辭”。冊封一事上他“既止科臣之差,又主罷封之說,執風聞確論,敢激切而妄言,傷皇上兼容虛受之懷”,確實有罪,“惟念律系祖宗之法,臣系奉法之官,遍檢大明律例,并無應擬罪名”,請求神宗對曹寬以斧鉞。⑨
曹學程因言下獄后刑科都給事中侯廷佩遂上疏申救,指出曹學程是為了解皇上之憂“乃輒信道路之語,徒恚痛苦之憤,搆詞過激含詈,傷沮時事,此圣心之所以不平,逮系之命所以下也”,“然詳其深故,程亦無罪,亦不至刑辱”。他請求神宗寬赦曹學程。在曹系獄三月后,都察院左都御史張養蒙則站在朝廷政務亟需官吏管理的角度請求神宗赦免他,指出,“自曹學程逮系以來公署塵封,敕印無寄,文移概從阻閣,奸宄日見縱橫,緣系題差,例難私攝,目今十差九缺,亦自無人攝之。臣等日夜焦心,捉襟露肘,陛下念及于此,必不忍令其久系廢事也。且學程言官也,以言為官,即言或未當,亦宜曲容。況原疏為止遣科臣,科臣業已罷遣,為勘東事,東事多屬難成,拷禁備嘗,足示懲創。”請求神宗“俯從刑部原擬,重加罰治,早令復還原職”。⑩ 二疏上后未見回復。
蕭大亨前疏上后五月未奉諭旨,又見曹學程因深受菙楚之苦,棒瘡潰烈,形神羸弱,慘不忍睹后,他再次上疏指出“學程之罪,止在言事憨直,非作奸犯科者比”,如果他以“一忤旨之故下獄淹羈,寬恤無期”,則非所以尊朝廷而慰眾望也。為此蕭大亨不避鼎鑊,上請“將學程免其擬罪,超釋生還,或仍重加罰治,姑責后效”。不料疏上后反而更加激怒了神宗,他徑下圣旨云:“曹學程抗違詔旨,避難忘君,無忠無義,著照逆臣失節斬罪,監候處決。”{11} 正如王在晉在張輔之《太仆奏議》奏疏序中評論說:“如侍御心洛曹公以憨直忤上指(旨)系獄,言官爭之甚力,上愈怒,竟坐辟。”{12} 由神宗自擬罪名并將曹學程處以死罪的行為可知,他對曹學程可謂是深惡痛絕至極。
二、官員持續申救
雖然神宗以處死方式懲處曹學程泄了心頭之恨,但在朝臣看來,這種行為非盛世所宜有{13},于是他們積極對曹加以申救,并以此緩和言官與皇帝之間的緊張關系,只是這種申救成功與否,依舊必須由神宗來決定。
得知神宗將曹學程“徑置重辟”后,朝臣“莫不相顧駭愕,變色失聲”,紛紛上疏為他請命。左都御史衷貞吉等上疏力爭說,曹學程不識事機,未合圣意,確有躁妄之罪,但若謂其抗違避難,則諒其萬萬不敢也。如果皇上以此加罪,恐言路人人自阻,臣工人人自危。建議神宗將曹學程重加謫罰,以警其后。吏部左侍郎孫繼皋等上疏希望神宗“收回監候嚴旨,稍從末減”。左僉都御史郭惟賢亦指出,曹學程之論東封“誠難辭輕率之罪”,但“檢閱其原疏,不過欲罷封,不過欲罷科臣之遣也。今科臣就已奉旨免遣,而近據兵部所奏,則封事漸有次第,煩言亦且日息矣。若謂其狂躁當罪,則對簿拷禁諸苦備嘗,亦既足為輕言者之戒矣”,請求皇上“矜之憐之,早賜釋放”。{14}
因見蕭大亨疏云曹學程垂死之狀讓人心酸,侯廷佩亦再次申救,指出,“節而逃者(李宗誠)身且有完膚,為逃而諫者臀乃無完肉,令學程告斃獄中,使皇上有殺諫臣之名,大臣有順上旨之誚,即東事果竣,亦非完典。”被曹學程視為在東事中碌碌無為的趙志皋亦上疏指出,曹學程作為言官,即使狂憨妄言,“但身無差遣之命,非有所違抗而辭避,慎重科臣之行,意在隨事而效忠”,若以“疏謬妄言禠奪降黜”已是過分,怎能處以大辟?請求神宗“將曹學程罪從末減,重加譴罰”。{15} 輔臣沈一貫亦云:“皇上臨御之初,豈無妄言之人,止于不用而已,自數年來,或罰、或降、或黜、或戍,亦已甚矣,又可坐之以殺乎?”希望神宗“略其過失,曲加原赦”。{16} 可惜疏上后神宗皆不理會,正如陳鶴所指出,“尚書蕭大亨請宥,帝不許,命坐逆臣失節罪,斬。給事中侯廷珮等訟其冤,志皋及陳于陛、沈一貫言尤切,皆不納。”{17}
諸臣疏上后未見神宗回復,曹學程隨時面臨被斬的危險。此時封事已壞,楊方亨上疏彈劾石星,東事再次進入防御備戰狀態中。議和翻轉,曹學程等言官所言應驗,借此機會,官員們亦對其進行了新一輪的申救。京畿道御史連標上疏希望皇上分清忠邪,“將石星斥逐回籍,以待東事完日議罪。將曹學程釋縲紲,復還原職”。云南道御史劉景晨則指出自李宗誠出逃以來石星之策就已失敗,但他仍寄希望于封事,而曹學程則料封事不成,遂上諫止封,是效言官之職,皇上雖“以休兵節餉為心,欲創一人以安星心,以完封事”,但這并不表明曹學程有罪。況“今倭奴狂逞矣,封事迄今無成矣,石星以誤國論罪而并禁學程以謝誤國之人”,天下人心難免疑惑不得其解,因而請求皇上將曹早賜寬釋。{18} 不過,這種論調并不能達到打動神宗的目的,反而只會讓他更痛恨言官,原因在于,石星等人是他在東事中依賴的主要負責人,為了支持石星等的決策,神宗不惜以其專制皇權壓制言官反對決策為代價,其結果換來的卻是欺騙和東事議和的失敗,這對神宗來說簡直就是恥辱,因而此時疏救曹學程不會有結果。
萬歷二十六年四月,司禮監太監田義等傳奉圣旨,要求將“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罪囚笞罪無干證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蕭大亨接旨后遂上疏請神宗釋放曹學程,他指出學程有母年將八十,“自被明旨以斬罪監候,母哀子罪,而風燭之老境益危。子念母哀,而圜墻之淚血幾徧。母子二命旦夕可虞,視一時在監罪囚,其情尤足矜憐者。”企圖以孝道來打動神宗,讓他矜恤曹學程。{19} 該疏上后不見神宗回復,于是侯廷佩又上疏請求神宗如部臣所請,將學程寬釋。因為神宗遲遲不寬宥曹學程,曹學程的兒子曹正儒決然上疏救父,其疏指出,其父系獄三年,祖母七十有九,衰病侵奪,風燭不定,思子心折淚枯,而自己為了救父,“徒步跋涉,積勞成疴,望隔九閽,感動悲激,嘔血數升,昏仆就死”,請求神宗將其父“敕下刑部,稍從末減”,“若以罪重不赦,乞系臣代戮,釋放父歸”。{20} 正儒以子代父死上請,足見其殷殷孝心,但神宗依舊不為所動。十月,逢刑部審錄重囚,蕭大亨于初五日上《為審錄重囚事》,將曹學程列入開除名單上報,神宗大怒,斥責蕭大亨“將斬罪曹學程擅自開除”是“竊擅威福”,讓他就此回話。蕭大亨遂于初七日上《為遵奉明旨乞恩認罪回話事》,向神宗解釋說,“犯人曹學程當會審之日,僉稱罪在不宥,情稍可矜。臣等仰體皇上好生之恩,俯從輿論,擬附矜疑之末,例不開入情真,依次具奏,取自上裁,即今祗奉嚴旨已將學程不敢并列矜疑。伏念學程重辟,臣等豈敢擅釋?但一時識見昏庸,失于詳慎,致干天怒,罪何所逃?伏冀圣明少寬斧鉞之誅,曲賜矜原。”疏上再次激怒了神宗,他下旨說,“曹學程避難忘君,保身忘國,不忠不義之畜,大奸大逆之輩,死有余辜”,著監候處決,并下令將刑部“堂上官姑且罰俸二個月,該司官著降一級調用,不許朦朧推升。其余的姑且各罰俸四個月”。{21} 神宗重罰曹學程,并牽連到刑部官員,足見他依舊對曹學程充滿了無法釋然的憤恨。
萬歷二十七年九月,因該歲未冬,行刑較往歲甚急,曹學程有被處斬的可能。{22} 又值兩宮落成、元嗣大婚之際,加上此時東事大功告成,朝廷論功行賞,于是大臣再次紛紛上疏申救曹學程。先是“兵部復以皇仁覃施,為石星、曹學程、許守恩、蕭應宮乞貸,上不許”。{23} 廣西道御史袁九皋以曹學程有八旬老母望其歸為由,希望“皇上以孝治為心,念及其母而因宥及其子,特恩緩死”。吏部尚書李戴等亦以曹學程形容枯槁,數千里外有80余歲老母望其生還為由,祈請皇上寬狂肆之罪而宥他。因李戴等人“合詞兩為罪臣曹學程請命,俱未蒙允”,于是他們又再次上疏請救曹學程,其疏指出,會審時見曹學程“囊頭搶地,僅存皮骨,即使不伏斧鉞,奄奄氣息亦不久即登鬼箓”,假如皇上此時殺他,則會有“貽學程以建言被禍之名而自貽以誅殺言官之累”,顯然不利于皇上的圣德善政,請求神宗圣慈矜憐,使其緩死須臾。{24} 總憲溫純亦上疏為罪臣曹學程請命,祈請神宗“誠施浩蕩之恩,令天下罪囚今歲暫免行刑,使曹學程亦得與于緩死之列”。{25} 曹學程之子曹正儒亦再次上請子代父死,期望感動皇上。{26}
害怕曹學程此次會被處斬,輔臣亦為之請命。首輔趙志皋于九月二十二日上疏指出,“曹學程以言獲罪,禁錮有年,今東事已完,有勞者既酬之以恩榮,則有罪者宜示之未(末)減。”“且聞學程母年已八十,遠居南粵,音信不通,兩地悲號,奄奄待斃”,希望皇上俯察其情,將學程從末減之律。二十五日,趙志皋見前疏未有回復,又再次疏救。{27} 輔臣沈一貫亦于二十二日上疏指出曹學程以直言冒犯皇上不足為惜,所惜者為御史、為國體。二十三日,沈一貫再救曹學程,希望皇上俯察眾心,免學程不死。對于二輔臣的上疏,神宗只是回復知道了,并無具體指示。二十五日沈一貫遂三上救曹學程疏,請求神宗“大弘天地之仁,免其即刑,以全縉紳之體,為慰滿朝文武之望”。{28}
大小臣工的肺腑之言最終打動了神宗,他同意將曹學程改為緩死,得知消息后滿朝文武官員在文華殿前“歡聲如雷,連呼萬歲”。{29} 雖然曹學程被改為緩刑,但還是面臨被斬的危境,一到每年的復審死刑案件之際,官員遂持續為之申救。萬歷二十九年十月朝審,兵部尚書田樂等疏云,曹學程“以未諳事體,仰拂圣心,知罪由自作,追悔無及”,況如今拘禁縲紲已五年,其母年逾九十,“號泣于萬里之外,亦可矜也”,祈請“皇上特霽天威,少垂睿鑒,待以不死”。不料疏上又惹怒神宗,他下旨曰:“曹學程食祿忘君,庇黨妄奏,死有余辜。況屢有明旨,今爾等諭其速示典刑,故輒來群激瀆擾,本當會官便決了,姑念已有明旨暫免行刑,且著一體牢固監候處決,以后朝審、大審若擅自開除,借言請旨瀆激,即便決了。”{30} 這是繼蕭大亨將曹學程列入開除之列受到懲處之后神宗再一次責備申救官員,表明他對大臣動不動就瀆擾他感到極為厭煩。
此后朝臣均不敢上疏申救曹學程,以免起到反作用。到石星死了五年之后即萬歷三十二年,“曹依然沉獄,閣臣卿貳臺省交章救曹,而主上堅不聽,惡曹如初。”{31} 直到三十三年十二月,因皇孫誕生頒詔大赦天下,刑部左侍郎沈應文遂借恩詔申救曹學程,疏上后月余未奉旨,他又上疏希望皇上寬宥學程,將其末減戍邊。{32} 此時已任首輔的沈一貫亦疏請說,學程禁錮十年,已經悔罪。每逢秋審之時,在廷文武諸臣無不為之凜凜惴慄,諸臣并不是有私于學程,而是為御史惜。“望皇上姑略其罪,不惜一特恩也”,將其乞從末減,坐之戍遣。{33} 疏上神宗未有任何回復。
萬歷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為皇太后上徽號,朝廷再次頒布恩詔,大赦天下。沈一貫等因此前為曹學程請命未蒙諭旨,遂再上疏指出,“近聞學程顛連困頓,存亡未卜,倘一旦病死獄中,人將謂其以建言東事而死,誰不憐之?況有九十瞽母,望子不至,亦必相盼而死,又誰不憐之?傳之天下后世,豈不為圣德少累哉?”希望神宗在普天肆赦之際,將學程末減充戍,“使得歸與老母一訣,上以隆圣德、彰大信,下以開法網、慰人情,斯其所全者多矣”。{34} 刑科左給事中宋一韓等指出,閣部為了救曹學程,以君父之怒為怒,以君父之喜為喜,希望皇上看在閣部順之上意,“特赦學程生還里門,則釋一人,千萬人服其于新政”。刑部江西司提牢主事南居益亦疏請神宗“將前閣部揭疏俯賜批發,從其擬議,俾學程早遂生還,與母相見”。{35}
四月五年一度的大審遲遲不予舉行,于是宋一韓等又奏云,萬歷二十九年大審未舉行,導致人情惶惑,此次大審不應再稽留,并趁機為曹學程請命,說“皇上臨御以來,何嘗無罪而死一諫臣”,希望能將曹矜疑。司禮太監陳矩見曹學程十載窮囚,創懲已極,亦上疏希望神宗能將曹學程寬釋,抑或罪不加誅,情難全貸,量從改遣。大理寺卿鄭繼之會同欽差司禮監內臣及部院科道等官從公審錄罪時見曹學程系獄十年,處于瀕死狀態,上疏云今日釋與不釋,總屬一死,然與其禁死,不如釋死。希望神宗憐學程桑榆暮景,鬼箓將登,敕下刑部,徑行釋放,或薄加懲究。{36}
八月熱審,不少重犯俱獲矜疑,而獨曹學程不在其列,沈應文等疏云,諸囚獲宥乃圣德仁慈,皇上天覆地載之仁,必不遺曹學程這個狂愚之人,況曹學程如今形體枯槁、母子天涯,倘若皇上將曹學程如李宗城遣戍之條處置,使其有重生之日,則天下幸矣。其子曹正儒亦奏云,懇乞圣慈“將臣系獄,代父死罪,留父蟻命,免死充軍,則臣父荷生全之賜,臣祖母釋倚閭之悲,兩命俱生,一家感戴,世世誦恩”。疏上未有回復,直到十月,神宗就沈應文前疏回復說:“曹學程背旨懷私,妄言瀆奏,本當監候處決,但念東事功成,姑照原擬,遣戍終身。”接旨后沈應文十分欣喜,即刻叫司官將曹學程從獄中放出,并諭之曰:“圣恩非常,待爾不死。”曹學程亦叩頭謝恩。因為激動的原因,沈應文將此本上奏時內字樣有差脫,神宗特命其認罪回話。沈應文認罪回話疏上后奉旨:“既認罪,姑免著改正行。”{37}
至此,經過內閣、刑部等官員的反復申救,神宗將曹學程由死刑改為遣戍,曹總算保住了性命。
三、曹學程下獄的背景及根因
關于曹學程為何觸怒神宗,可從神宗下令逮他及定罪的旨意中清楚得知,既有“每以細微之故喋喋煩擾,欲伏斧鍎不辭”的遠因,亦有違抗君命的近因。可以說,神宗借封事懲處他是舊恨新仇一起累積的結果。
神宗之所以對曹學程有“每以細微之故喋喋煩擾,欲伏斧鍎不辭”的指責,主要因為曹學程在任廣東道御史后就神宗不上朝、不立國本以及魏學曾被逮等事上疏對其多有指責,得罪了神宗。曹學程于萬歷二十年任廣東道御史,二十一年督理屯馬{38},上任伊始,他就連上三疏,積極建言。在所上《為星變疊見人紀必壞懇乞宸衷亟宜修省回天意以保神器以安社稷事》中,曹借出現災沴而批評神宗朝政久輟、郊廟不臨、不向太后請安、不御朝。所上《為皇儲久虛承祧罔嗣懇乞圣明亟行冊立正東宮以崇國本以安宗社事》直指在立國本一事上神宗態度不斷變化,又不能效法皇祖,“外惑于讒佞而內溺于袵席”,晏處深宮,致黨邪滋蔓。并說三王并封“詔下,陛下欲以愚天下而適以自愚也。夫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日之太子即千秋萬歲后之皇上,何獨不念六歲時乎?竟忍輕元子以輕天下,而悉拒維京、學曾等之忠諫也哉”。{39} 維京即朱維京,三王并封議出后他首先上疏反對,惹得神宗大怒,將其謫戍極邊。學曾即王學曾,他與少卿凃杰合疏爭三王并封,因忤旨皆遭削籍。{40} 曹學程不僅認同支持二人的行為,并身體力行,追隨朱、王二人上疏抵制三王并封。所上《為泰運方臨天心仁育懇乞洪恩俯賜曲貸以光圣德以崇國體事》則是疏救主持寧夏之役的兵部尚書兼右僉都御史的魏學曾,他因戰事進展緩慢為監軍御史梅國楨以“玩寇”罪彈劾,神宗悉知后大怒,下令將魏學曾逮系至京。曹學程在疏中詳述了魏學曾的戰功,請求神宗復還其原職。{41} 可以說,這三疏無論是對神宗本人的指責,還是不遵君命上疏瀆擾,都犯了神宗的大忌,這就為曹學程后面被逮埋下了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