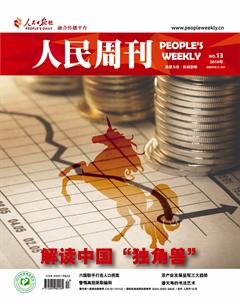想念,近在咫尺
徐光惠
二十多年前,父親到我生活的地方來看我。
那時,我在一個小鎮上班。單位事情繁雜,忙得暈頭轉向,我有一個多月沒有回家。那天,我下班往家走,突然發現家門口站著一個似曾相識的背影。
走近看,正是父親。他穿一件洗得發白的灰色襯衫,肩上挎著一個帆布口袋。“爸,你怎么來了?”我吃了一驚。“惠兒,看你好長時間都沒回家,我來看看。”我趕緊把父親讓進屋。
“惠兒,我摘了些金銀花,天熱,你泡水喝啊。”父親微微佝僂著背,從口袋里倒出金銀花。“爸,這樣熱的天,你還去摘金銀花,中暑了怎么辦?”“不礙事的。”想到父親冒著酷暑去摘金銀花,又坐大半天的車給我送來,我眼眶一陣濡濕。
我煮好稀飯,炒了一盤青椒肉絲和兩樣小菜,與父親相對而坐。父親興致很高,突然說想喝酒,平時他一個人是不會喝酒的。我去小賣部買了一袋花生和一瓶白酒,給他倒上一杯。父親邊喝酒邊與我閑聊,他的酒量并不好,一杯下去就已經微醺。
晚上,我讓父親睡臥室的床上,但他執意睡在客廳的沙發上。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卻毫無睡意,腦海里不斷浮現出兒時的片段。
我輕輕推開房門,躡手躡腳來到客廳。父親身子往里側著,似乎睡著了。“惠兒,你怎么還沒睡?”許是我推門驚動了他,父親從沙發上坐起來。
“我出來喝水。”我極力掩飾著自己,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我其實只是想出來看看他。
“爸,你也沒睡著啊?”“嗯,一時半會兒的睡不著。”“要不,我陪你坐會兒吧。”父親點點頭。我在他旁邊坐下。
父親不善言談,我遺傳了他的基因,話也不多。我們安靜地坐著,偶爾說幾句家里和我工作上的事。我們就那樣坐著,大概七八分鐘。那是父親第一次來我家,也是最后一次。
父親過世已經二十多年,在他生前的日子里,真正陪他一起說話的時間屈指可數,我從來沒在他面前說過我想他,就像他也從來沒對我說過他想我。
如今,對父親的懷念只剩下那些溫暖的記憶。這些年,我常常自責,那天晚上我為什么沒有勇氣對父親說我想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