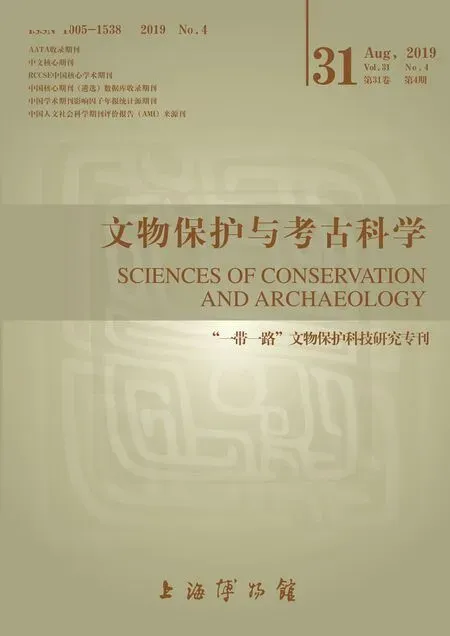印尼“黑石號”沉船及其文物綜合研究
陳克倫
(上海博物館,上海 200003)
0 引 言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和婆羅州之間的勿里洞島(Belitang Island)丹戎潘丹(Tanjung Pandan)港北部海域的海底發(fā)現(xiàn)大量陶瓷和一些木船構件,推測該沉船可能因撞上西北150 m處黑色大礁石而沉沒。沉船被稱為“黑石號”(BatuHitam)或“勿里洞沉船”(Blitang Wreck)。持有印度尼西亞政府頒發(fā)的考察和發(fā)掘執(zhí)照的德國“海底探索”公司聞訊后對沉船遺址進行定位,并于1998年9~10月間開始海底遺址的發(fā)掘工作[1]。沉船位置在南緯2°41′,東經(jīng)107°35′,沉船海域水深約10 m,對沉船的勘察和沉船文物的打撈并不十分困難。經(jīng)過約一年的發(fā)掘,水下考古工作基本完成。
1 沉船及其年代
沉船已經(jīng)腐朽無法打撈。據(jù)勘察,船只建造沒有用木釘和鐵釘,而是用植物纖維編織的繩索來固定船板;對木材的檢測也表明造船材料主要來源于南亞和阿拉伯地區(qū)。勘察者從船的制造技術、船體形狀和建造材料來判斷,船來自阿拉伯地區(qū)[2]。
沉船中的八卦四神銅鏡和長沙窯阿拉伯文碗為沉船年代提供了證據(jù):在八卦四神銅鏡鏡背的外側一周鑄有文字“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於揚州揚子江心百煉造成”;長沙窯阿拉伯文碗的外側下腹部刻有“□□□□寶曆二年七月十六日”等字樣。乾元元年為公元758年,寶歷二年為公元826年。考慮到長沙窯作為一座以外銷為主的瓷窯,時效性很強,其裝船應該距燒成時間不遠。因此該船裝貨的時間可以推斷為公元9世紀前期,即唐代中晚期。
2 沉船文物
從“黑石號”沉船中打撈出來的文物超過60 000件,其中瓷器占絕大部分。長沙窯瓷器為最大宗,有55 000余件,大部分是碗,各類壺約700件;越窯青瓷約250件,白瓷約300件,綠彩瓷器約200件以及其他瓷器約500件。特別是在沉船中還發(fā)現(xiàn)了3件唐代的青花瓷器,引起世人矚目。
沉船中發(fā)現(xiàn)的金銀器中有金器11件,金箔2 kg;鎏金銀器約20件,銀錠18件。其他還有銅鏡29件、漆器2件、石硯1件、碎墨若干等等。據(jù)估計,在第一期發(fā)掘中被發(fā)現(xiàn)的文物大約占全部貨物的2/3[2]。
2.1 長沙窯瓷器
沉船中長沙窯瓷器的碗(圖1)一部分被用稻草扎成圓筒裹住堆放在船艙里,堆得很高接近船板。還有一部分被螺旋狀碼放在在青釉大罐里,一個大罐往往可以裝多達130只。只要大罐沒有破損,碗的釉面就不會受到海砂的沖擊和磨損,因此長沙窯碗的釉面大部分完好如新。絕大多數(shù)碗以及裝有碗的大罐都是從船的中央和船尾部位打撈上來的。
700件壺堆放在船艙的前部,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包裝物遺存。還發(fā)現(xiàn)了散落各處的小瓶子,很可能是放在其他有空間的器皿之間。一些帶有雙耳的小罐被堆放在一起,許多被牢牢粘附在石灰混合物上。
中晚唐時期崛起的長沙窯產(chǎn)品流行書寫當時流行的民間諺語、俗語、俚語、詩文等,甚至還有書寫器物的用途和窯戶作坊的廣告,迎合了百姓的欣賞口味,也傳播人生哲理及個人情感。
由于長沙窯產(chǎn)品面向普通百姓,以低價參與市場競爭,因此盛銷于國內(nèi)市場,并很快成為外銷日用瓷的大宗。特別是“安史之亂”之后,陸上絲綢之路逐漸衰落,湘江岸邊的長沙窯通過水運能與揚州、廣州、安南等地連接起來,使沉重易碎、不適合大規(guī)模長途陸運的陶瓷器找到了新的出口方式,海上絲綢之路逐漸興起。“黑石號”沉船上長沙窯瓷器的巨量發(fā)現(xiàn),說明了當時這類瓷器外銷的事實。
長沙窯瓷器的造型相對比較簡單,主要是碗和執(zhí)壺。多達50 000多件碗的造型單一,圓口(極少作花口)、弧腹、淺圈足,高約3.5~5.0 cm、口徑約12~15 cm。碗內(nèi)滿釉、碗的外壁半釉。執(zhí)壺為圓口稍外侈、直頸、圓肩,直壁、平底,執(zhí)壺的一側有六方形的短流,另一側則有用兩根泥條做成的執(zhí)手,在流和把手的另外兩側各有一個雙復系。執(zhí)壺高約20 cm。
長沙窯裝飾為釉下彩,以氧化鐵和氧化銅作為呈色劑。在氧化氣氛中,鐵呈現(xiàn)褐色,銅則為綠色。在偶然的情況下,銅也會被還原而呈現(xiàn)紅色。長沙窯碗繪彩在碗的內(nèi)壁,題材除了常見的簡筆花卉與樹葉、云氣紋、山水紋、漩渦紋及市井流行詩文、俚語等,還有佛教題材的卍字佛塔、摩羯魚、蓮花等。一些過去認為是簡筆寫意山水畫、云氣紋和在一些隱藏在圖案中的簡筆紋飾被專家破譯,認為是阿拉伯文[3]。
壺通常采用模印貼花裝飾,及用模具印出裝飾泥片,施青釉后在貼花部位再施褐釉,高溫燒成后紋飾更加醒目。貼花的內(nèi)容較多表現(xiàn)域外文化因素,如獅子、椰棗樹、婆羅樹、波羅蜜樹、葡萄、寺廟以及胡人舞樂等。
2.2 越窯青瓷
“黑石號”沉船中出土的越窯瓷器數(shù)量并不多,造型卻十分豐富,包括海棠式大碗、海棠式杯、花口碗、玉璧底碗、香熏、大型唾盂、刻花盤、刻花方盤、執(zhí)壺、蓋盒等。
海棠式大碗1件。碗作海棠式,碗口呈橢圓形,對稱有四出花瓣,圈足外卷,足底施釉。與此碗造型相似、大小相當?shù)膬H見于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海棠式大碗,高10.8 cm、口徑23.3 cm×32.2 cm。仔細比較兩者,存在的區(qū)別有以下二處:其一,上海博物館之海棠碗釉面瑩潤光亮、釉色純正;“黑石號”出土之海棠碗釉面呆滯失去光澤,釉色略顯發(fā)白,蓋因經(jīng)海水長期浸泡所致。其二,上海博物館海棠碗的花口比較明顯;“黑石號”海棠碗僅在碗口下沿作花瓣狀凹入,口沿部分的凹入并不顯著。
海棠式杯,出土數(shù)量相對較多。器形較小,花口十分明顯,圈足較淺,足底施釉。“黑石號”還有一類海棠杯,器物呈橢圓形,只是在其口沿部分象征性地對稱刻出四處缺口,好似花瓣之間的凹下部分。類似器物在浙江慈溪上林湖唐代晚期窯址中都有發(fā)現(xiàn)。海棠式大碗和海棠杯的造型始于唐代,應該是受到西亞地區(qū)金屬制多曲形器皿的影響而出現(xiàn)的。
“黑石號”上的花口碗造型比較豐富,主要有蓮花式碗、深腹碗及花口碗。蓮花式碗口沿稍斂,碗口作四出蓮花瓣形,花瓣造型比較細致,腹部不見凹入的花筋。深腹碗腹壁陡直,口沿外撇,圈足外卷,其腹部有四處出筋,口沿沒有作花口形。花口碗通常為敞口,口沿作四出或五出花口,腹部有相應的出筋,圈足較矮,有的碗的內(nèi)壁還有刻劃花卉,以寶相花、蓮花多見。除蓮花式碗較少見外,深腹碗和花口碗均是常見器物,在浙江越窯唐代晚期窯址中都有發(fā)現(xiàn)。
玉璧底碗是越窯最常見的器物,“黑石號”中發(fā)現(xiàn)的玉璧底碗足底心施釉,是越窯同類器物中比較精致的一類。一些玉璧底碗還做成花口形,有四出花瓣。
缽為斂口,弧腹,圈足外卷。通體青釉,釉面滋潤勻凈。
出土的越窯青瓷盤有圓盤和方盤兩種,盤均較淺。圓盤作成四瓣花口形,盤心有刻劃花,常見線條奔放的牡丹紋;方盤多作成倭角方形,亦有刻劃的花卉紋裝飾,其造型與同船所出的金盤相類似。
四系大碗口徑估計為30~40 cm。敞口、翻沿,圈足,口沿下兩側對稱各有兩個雙復小系,估計為穿系繩索便于提攜所用。通體素面無紋,青釉勻凈、瑩潤。
唾盂,器物甚大,撇口、束頸、圓腹、淺圈足。通體青釉,釉面光潤,足底無釉露胎。如此碩大的唾盂在越窯青瓷,以至在唐代瓷器中均十分罕見,其用途似乎超出了唾盂的范疇。
香熏,整體呈覆鐘形,直壁、高圈足外撇、蓋頂圓隆、有鈕,蓋上花形鏤空各異,焚香時香氣從中溢出,有的圈足足墻上亦有長條狀鏤空。器物通體施青釉,蓋沿及圈足內(nèi)圈有條形支燒痕。
執(zhí)壺(圖2)造型為唐代越窯所常見,敞口、翻沿、束頸、斜肩、鼓腹、平底,一側頸、肩之間有雙股曲柄,另一側肩部有多棱形短流。還有一類執(zhí)壺壺體稍大,肩部稍挺,腹部呈瓜棱形,頸、肩間對稱各有一個雙復小系,也是越窯的常見器物。
背壺,杯形口、束頸、扁腹、平底,壺身兩側各有兩個橋形系,便于穿帶所用。壺身有刻劃的花卉紋。
蓋盒,盒盤較淺、盒蓋隆起、底內(nèi)凹,子口處無釉露胎,底部滿釉,有一周不規(guī)則的三角形支燒痕。
越窯青瓷是唐代南方瓷器的代表。公元8—9世紀時期的越窯青瓷沿海上陶瓷之路外銷到亞洲至非洲的廣大地區(qū),是中國外銷瓷的重要品種。大部分唐代越窯外銷瓷器保留了本土的風格,有一部分越窯外銷瓷器考慮到銷往地的宗教文化因素,其造型和紋飾具有異域文化特點。
關于唐代越窯瓷器的外銷,文獻上缺乏記載;國外一些遺址發(fā)現(xiàn)的越窯標本提供了研究的資料。在以往幾十年中,先后在東非的埃及福斯塔特遺址、蘇丹阿伊扎布遺址,西亞的伊拉克薩瑪拉遺址、伊朗尼沙布爾遺址、希拉夫遺址,東亞的日本九州博多遺址、筑野遺址、奈良平城京遺址,南亞印度河流域的班布爾遺址、阿里卡美遺址,東南亞的菲律賓卡拉塔岡遺址、馬來西亞沙撈越尼雅遺址等地發(fā)現(xiàn)越窯瓷器的標本。唐代中國主要的貿(mào)易港口明州(寧波)、揚州等地的遺址和沉船中也發(fā)現(xiàn)了數(shù)量不少的越窯瓷器。
從“黑石號”上瓷器所占的比例看,越窯數(shù)量較少,由此尚不能據(jù)此認為越窯瓷器在當時中國外銷瓷市場中所占的份額并不多,在世界各地發(fā)現(xiàn)的唐代越窯瓷器標本足以說明越窯瓷器也是當時中國外銷瓷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黑石號”上的越窯瓷器品種與供應中國市場的基本一致。同船的長沙窯瓷器卻在器物的裝飾上迎合了阿拉伯地區(qū)的喜好。這樣,可以從中得出如下結論,中國瓷業(yè)在唐代已經(jīng)有較明確的分工,越窯產(chǎn)品主要是供內(nèi)銷,它不會或很少為外銷特別生產(chǎn)不同的產(chǎn)品。而長沙窯則完全是為了外銷而興起,其彩繪裝飾及其圖案內(nèi)容是根據(jù)輸入地區(qū)的喜好、流行時尚而設計制作的[4]。
2.3 白瓷
“黑石號”沉船中發(fā)現(xiàn)的白瓷約有300件,造型主要有杯、杯托、碗、執(zhí)壺、罐、穿帶壺等。
杯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無柄的斂口杯,一類是單柄的撇口杯。杯托呈盤形,盤沿坦平,盤心凹入以承杯體,盤口作四瓣花口。單柄杯和敞口杯在國內(nèi)也有發(fā)現(xiàn),如江蘇徐州奎山唐墓出土的白瓷單柄杯[5]和1957年河南陜縣湖濱區(qū)出土的白瓷圈柄杯[5]即是。
碗的腹部較淺,斜弧壁,有的口沿外卷,均為四瓣花口。
為進一步驗證本文所提出的具有自適應P-SSHI控制的有源整流電路的優(yōu)勢,本文還進行了對比實驗,將所提出的電路與全橋整流電路、僅具有有源整流結構電路在相同實驗條件下搭建實驗平臺進行測試。
執(zhí)壺作敞口、短頸、鼓腹、斂足、平底,肩部一側有圓形短流,另一側有雙復柄與口部或頸部相連。
罐的口部較小,口唇外卷,肩部圓弧,腹鼓出,下腹收斂,下承小平底。
穿帶壺僅見一件,造型為圓形而與傳統(tǒng)的穿帶背壺略作扁體有異,口部膨出,細頸,斜肩,腹下部隆起,下接圈足。肩部兩側有用于穿帶的扁形方系,系下腹部各有兩條細突棱,與之對應圈足兩側有扁方孔用于穿帶。
除執(zhí)壺和罐為平底外,其他器形均有圈足,圈足一般較淺。碗多為玉璧形底;杯少量為玉璧底,大部分為較寬的“玉環(huán)”形圈足;杯托則都為“玉環(huán)”形圈足。
從胎、釉及制作工藝上看,這些白瓷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精白瓷,胎質(zhì)細白,釉質(zhì)潤澤,器壁較薄,造型規(guī)整;另一種制作較為粗糙,胎質(zhì)較粗松,器壁較厚,釉質(zhì)較濁,胎、釉間通常都施白色化妝土。由于這類白瓷釉質(zhì)地的原因,打撈起來時釉層大都已經(jīng)剝落。
從中國陶瓷發(fā)展的歷史來判斷,這些唐代白瓷應該基本上都是中國北方窯口的產(chǎn)品,但是它們是否都是一個窯口的產(chǎn)品,抑或產(chǎn)地不止一處?如果從造型上看,杯、杯托并不是傳統(tǒng)唐代白瓷中常見的,它們更接近于當時的金銀器造型;花口碗雖然與唐代的造型一致,但依然無法確定它是邢窯或者是曲陽窯的產(chǎn)品;其他如執(zhí)壺、罐等也是如此。有學者從胎、釉及制作工藝上來區(qū)別,認為精白瓷屬于邢窯產(chǎn)品,而施化妝土的粗白瓷屬于河南鞏義窯產(chǎn)品。但是,在邢窯窯址采集的標本中,既有精白瓷,也有上化妝土的粗白瓷。因此尚不能以是否有化妝土作為判別產(chǎn)地的根據(jù)。
筆者有機會得到兩件“黑石號”沉船中的白瓷標本:一件是胎薄釉潤的精白瓷;一件是施有化妝土的粗白瓷,由于釉層已被海砂侵蝕殆盡,表面即是化妝土。通過QuanX型能量色散X射線熒光光譜儀(XRF)對這兩件標本的胎、釉及化妝土成分進行分析,結果見表1。

表1 “黑石號”沉船白瓷標本分析結果Table 1 Composition analyses of two white porcelain samples from the Batu Hitam shipwreck (%)
1) 邢窯和曲陽窯無論是胎還是釉,它們各項指標都非常接近,至少從常量元素上很難對二者進行區(qū)分;
2) 鞏義窯與邢窯、曲陽窯在鈉、鎂、鉀、鈣、鈦和錳等元素存在明顯的差別,足以區(qū)分產(chǎn)地;
3) 從標本胎的氧化鋁含量較高看,“黑石號”白瓷標本無疑都屬于北方的產(chǎn)品;
4) “黑石號”沉船中精白瓷標本的胎、釉成分與邢窯、曲陽窯標本存在較多的相似性;
5) “黑石號”沉船中粗白瓷標本胎的成分與邢窯、曲陽窯標本差別較大,而與鞏義窯標本比較接近,特別是鈉、鎂、鉀、鈣、鈦和錳等元素。
由于所得到的“黑石號”白瓷標本十分有限,因此以上只是初步分析。盡管目前尚未能確定“黑石號”沉船精白瓷的確切產(chǎn)地,但是通過以上分析至少可以知道當時外銷的白瓷既有河北的產(chǎn)品,也有河南的產(chǎn)品[6]。
2.4 白地綠彩瓷器
從“黑石號”沉船遺骸中打撈上來的遺物中發(fā)現(xiàn)了約200件白釉綠彩瓷器。
白釉綠彩瓷器的裝飾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通體內(nèi)外飾綠色,表面通常有垂流現(xiàn)象,并露出彩下白釉。另一種是在白釉上飾以不規(guī)則的綠彩斑塊。器形主要有杯、高足杯、盤、碗、蓋盒、蓋罐、執(zhí)壺(圖3)等。
從這些白釉綠彩瓷器的造型看,杯的造型直口、深腹,與沉船發(fā)現(xiàn)的白瓷斂口杯稍有區(qū)別,由于白釉綠彩杯的口徑稍大,其高度顯得稍矮。另外,白瓷杯的表面沒有任何裝飾。單柄杯和敞口杯的造型與白釉杯相似,而與國內(nèi)出土的敞口杯相比,“黑石號”沉船中白釉綠彩杯的口徑和腹徑略大,高度要矮一些,杯柄上的“指墊”也不一樣,前者是利用圓環(huán)泥條一端上挑自然形成,后者則特別加上有印花的圓形泥片作成。高足杯在唐代陶瓷器中比較少見,特別是高足吸杯在唐代陶瓷器中幾乎不見。盤、碗的造型為唐代常見。沉船中發(fā)現(xiàn)的蓋盒較大,與唐代流行的作化妝品盛器的蓋盒不同。蓋罐與唐代的無異,1992年在河南省鞏義市(原鞏縣)北窯灣唐大中5年(公元851年)墓中出土的白瓷蓋罐[7]與沉船中發(fā)現(xiàn)的綠彩蓋罐器形完全相同。類似沉船發(fā)現(xiàn)的獅柄執(zhí)壺在國內(nèi)也有出土,如陜西省西安市004工地主廠區(qū)出土的“白釉執(zhí)壺”和陜西省西安市西郊熱電廠唐墓出土的“白釉獅柄執(zhí)壺”[8],應該都是河北邢窯的產(chǎn)品[1]。
在“黑石號”沉船中發(fā)現(xiàn)的白釉綠彩瓷器國內(nèi)發(fā)現(xiàn)并不多,見于報道[8-9]的有:1957年河南安陽薛莊唐墓中曾經(jīng)出土一件白釉綠彩瓷執(zhí)壺;1987年河南省三門峽市化工廠工地唐代墓葬中也曾經(jīng)出土白釉綠彩瓷碗;1983年在江蘇省揚州市三元路曾經(jīng)出土一件白釉綠彩貼花龍紋碗,口沿作四出花口、外侈,腹壁斜直,碗心盤龍云氣紋貼花與“黑石號”發(fā)現(xiàn)的同類碗幾乎完全一樣[1]。
關于唐代白釉綠彩瓷器的產(chǎn)地有幾種推測,一種認為其裝飾與河南鞏義唐三彩相似,可能是鞏義窯的產(chǎn)品;從個別器物底部刻有“進奉”、“盈”等款識來看,也可能是河北邢窯的產(chǎn)品,因為在邢窯窯址出土的白瓷標本[10]和一些地區(qū)出土的白瓷[11-12]上發(fā)現(xiàn)刻有“盈”、“翰林”等字款。如果從鞏義唐三彩的裝飾特點看,通常比較多的是在綠色上加白色斑塊,而白底綠彩的確實很少見[1]。傳世文物中,故宮收藏的白釉綠彩瓷罐[5]與“黑石號”沉船中發(fā)現(xiàn)的造型相仿。
近年,有學者通過測試分析比較邢窯、鞏義窯、耀州窯及“黑石號”標本的化學構成,認為“黑石號”上發(fā)現(xiàn)的白釉綠彩瓷器是河南鞏義窯的產(chǎn)品[13]。由于所分析的“黑石號”標本樣本只有8個,還不足以反映“黑石號”白釉綠彩瓷器的全貌。2011年在河北省內(nèi)丘縣發(fā)現(xiàn)唐代邢窯窯址,出土的白釉綠彩瓷片標本特點與黑石號發(fā)現(xiàn)的幾乎一致[1]。
以上,說明唐代“黑石號”沉船上的白釉綠彩瓷器中既有河南鞏義窯的產(chǎn)品,也有河北邢窯的產(chǎn)品。鞏義窯產(chǎn)品胎質(zhì)較粗,有的在胎的表面施白色化妝土;而邢窯產(chǎn)品胎質(zhì)較細、較白,一般不用施化妝土[1]。
2.5 關于“盈”和“進奉”款瓷器的討論
唐代“盈”字款的瓷器,曾引起長期的討論,一般認為這種瓷器會進入皇室的大盈庫,故有“盈”字。由于多出土于邢窯窯址之中,人們的認識逐漸趨于一致,即帶“盈”字款的器物,即為邢窯產(chǎn)品,年代為9世紀初之后,是供皇室享用的瓷器。“黑石號”沉船上發(fā)現(xiàn)帶有“盈”字款的器物,似乎應是河南鞏義窯的產(chǎn)品,也就是說帶有“盈”字款的器物并非僅有邢窯獨有。此外還應該注意的是,如果按以往的結論,帶有“盈”字款的器物是要進入皇室的大盈庫,供皇室享用的瓷器,那么為什么會出現(xiàn)在“黑石號”沉船上?“黑石號”沉船上的物品是商品,也就是說在市場上也可以買到“盈”字款的器物。參照以往的發(fā)現(xiàn),“盈”字款的白瓷,除了在唐長安大明宮外,在西安西明寺、青龍寺、唐新昌坊也有出土,而且也在邢臺市、河北易縣并非是高級貴族的唐墓中發(fā)現(xiàn),可見把“盈”字直接與大盈庫對號入座的看法還應仔細斟酌。也許帶有“盈”字款的器物在唐代供皇室宮廷使用,卻并非是專用,在民間和市場上也有使用和出售。同樣道理,“黑石號”沉船上還有刻“進奉”字款的白釉綠彩瓷,說明“盈”、“進奉”字款的器物也會流入市場[14]。
2.6 青花瓷器
最引人注意的是在“黑石號”沉船船艙的尾部發(fā)現(xiàn)了三件青花瓷盤(圖4),這是迄今為止首次發(fā)現(xiàn)的中國最早、最完整的青花瓷器。三件青花盤的造型基本一致,紋飾不完全相同,但其構成和母題如出一轍。
在1975年揚州唐城遺址發(fā)現(xiàn)青花碎片之前,關于中國青花瓷器的發(fā)生及發(fā)展通常認為是元、明、清時代。1975年和1983年在揚州唐城遺址先后發(fā)現(xiàn)了青花瓷殘片[9,15],紋飾中的棕櫚葉紋、菱形紋、梅花點紋、豎條紋等具有伊斯蘭風格,學者們在肯定這些青花瓷片的年代為唐代的同時,推測它們是為滿足國外市場需求而燒制的[16]。“黑石號”沉船中的青花瓷盤紋飾與揚州唐代遺址出土青花殘片紋樣風格十分相似,而這種紋樣在唐代陶瓷器中罕見。“黑石號”沉船中的三件青花瓷與中晚唐瓷器同處于一艘船上,說明其來自中國,證實唐代已經(jīng)用鈷料作釉下彩燒制青花瓷,并且已經(jīng)輸出海外[14]。
考古發(fā)掘證明,河南鞏義黃冶窯既燒白瓷又燒三彩陶器,在其晚唐地層中還發(fā)現(xiàn)胎質(zhì)純凈、火候較高的白釉藍彩殘片,呈色劑是氧化鈷[17]。從條件上說,黃冶窯具備了燒造青花瓷的條件[14]。“黑石號”沉船上青花瓷盤其中一件釉面有剝落,可以看出其制作工藝是成型后先施一層化妝土,在化妝土上用氧化鈷繪彩,施透明釉后入窯高溫燒成。這與鞏義黃冶窯的制作工藝一致。
2.7 金銀器
“黑石號”沉船上的金銀器包括一件金杯、三件海棠式杯、兩件方盤、一件圓盤以及兩件類似耳墜的殘件等。
金杯(圖5)八方形,一側有以圓形金條盤筑的圓環(huán)形柄,柄環(huán)上端與一圓形印花指墊相連,這種做法與單柄白瓷杯類似,杯體下承花型圈足。金杯的每一個面都有胡人手持樂器或果盤跳舞的形象。金杯的裝飾與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金杯相似,具有粟特風格,但器物更大、更重。三件海棠式杯作橢圓形,敞口、直壁、在四角各有一道凸棱,圈足,其造型與沉船中發(fā)現(xiàn)的越窯海棠式大碗基本一致,其中一件素面,兩件刻有飛禽花卉圖案,紋飾分三個層次,口沿內(nèi)側為連續(xù)的珍珠地弧形三角紋,內(nèi)壁為四組花卉,內(nèi)底外沿一周花瓣,中間為珍珠地花卉,兩只飛鳥上下穿行其間。兩件方盤通體珍珠地,委角、盤身較坦、翻沿,口沿一周葉紋,四壁為四組花卉,盤中央為以闊葉紋組合成的卍字,在四組花卉之間和卍字的四角各有一個振翅的蜜蜂。在一件方盤外沿的一側刻有“七兩二銖”(約303 g)。圓盤亦為四出花口、坦身、翻沿,通體珍珠地,內(nèi)沿一周勾連如意紋,盤壁有四組闊葉環(huán)繞花卉的橢圓形圖案,中間為一方形以扇形紋飾圍繞的四瓣花卉,在橢圓形圖案之間各有一個振翅的蜜蜂。
沉船發(fā)現(xiàn)的鎏金銀器由于海水侵蝕,表面金大都已經(jīng)脫落。有海棠形、菱花形、扇形的蓋盒,圓盒、盤和提梁壺等。盒蓋在珍珠地為浮雕式的立體花紋,通常為纏枝花卉環(huán)繞的動物,有飛鳥、奔鹿、蜜蜂等;蓋盒底部則以線刻花紋裝飾,有纏枝花卉及飛鳥、蜜蜂等。圓盒較大,盒蓋珍珠地,以不同的花卉、飛鳥及鴛鴦組成圖案,非常逼真。提梁壺有蓋,蓋面圓隆,圓環(huán)為提手。扁體,兩側有環(huán)形耳與扁形提梁相連。壺身通體珍珠地,以線刻的花卉、飛禽裝飾。在一件銀圓盤殘器上有犀牛紋樣,這并不多見。
金銀器紋飾是采用鏨刻的工藝做成。除了方盤比較少見,其他器物在唐代考古中都有發(fā)現(xiàn)[14]。裝飾紋樣有的具有外域風格,這與唐代對外交流頻繁,吸取各種文化因素有關。
這批金銀器的有可能是在揚州一帶制造的。據(jù)記載,8世紀中葉以后,嶺南道、江南道一躍成為金銀器制作原料新的供應地。9世紀初出任淮南節(jié)度使的王播,曾三次進獻皇室金銀器皿,數(shù)量多達5 900多余件[18-19]。
2.8 銅鏡
在沉船上發(fā)現(xiàn)了29面銅鏡。發(fā)現(xiàn)時大部分鏡子被石灰質(zhì)沉積物覆蓋,鏡面已經(jīng)腐蝕,許多已經(jīng)變成了黑色。最初,銅鏡大多是銀色的,使用面平整而光亮,用于映面照形。為了達到如此明亮的顏色,在制作銅鏡的合金中加入了更多的錫。唐代銅鏡平均由含69%銅、25%錫和5.3%鉛的青銅鑄成。
沉船上的銅鏡多是唐代流行款式,有圓形、菱花形、葵花形、蓮花形和方形等。銅鏡背面的裝飾題材有海獸葡萄、獅子葡萄、綬鳥、真子飛霜、八卦四神等。此外還發(fā)現(xiàn)了一件漢鏡。
八卦四神鏡上有一周銘文:“唐乾元元年戊戌十一月廿九日於揚州揚子江心百煉造成”,不但為確定沉船的時代起了作用,而且成為文獻記載的“江心鏡”考古實物。產(chǎn)于揚州、揚子江制造的“江心鏡”費工費時,難以制成,又被稱為“百煉鏡”,供給宮廷使用[20]。它出現(xiàn)于8世紀的唐玄宗時期(712—756),唐德宗(779—805)繼位時,因提倡節(jié)儉而被罷去[19]。《異聞錄》記載“江心鏡”的樣子:“唐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玄宗覽而異之……”[20]。唐人對這種銅鏡熟知并喜愛,白居易作有“百煉鏡”詩,詩的最后勸導天子不要沉迷于奢侈,而要關心四海的安危。
3 “黑石號”沉船的出發(fā)港和目的港討論
關于“黑石號”的出發(fā)地,有三種推測:其一,“揚州說”認為“黑石號”沉船在揚州裝載長沙窯(長沙窯產(chǎn)品沿湘江而下,經(jīng)洞庭湖而入長江到揚州)等貨物后出海,然后沿著海岸線至明州、廣州等地停靠,并裝上當?shù)氐呢浳铮旭傊两裉K門答臘附近沉沒。在揚州發(fā)現(xiàn)較多長沙窯產(chǎn)品的遺存和與“黑石號”相同的綠彩、青花瓷器以及揚州地區(qū)生產(chǎn)金銀器,為“揚州說”提供了依據(jù)。
其二,“廣州說”認為“黑石號”在廣州裝上溯湘江而上,經(jīng)靈渠到廣州的長沙窯產(chǎn)品,再按照“廣州通海夷道”中的路線行駛至蘇門答臘附近[21]。一部分長沙窯碗被裝在廣東生產(chǎn)的青釉大罐再裝船,為“廣州說”增加了可信度。
其三,認為“黑石號”沉船上的貨物是在室利佛逝(唐代末年以后改稱三佛齊,即蘇門答臘島)的港口一次性裝載的,而這些裝上船的貨物則是由不同的船只從揚州、明州和廣州分別運到室利佛逝的[21]。
有學者認為,如果是揚州出發(fā),不能解釋廣東青瓷大罐如何到揚州再裝載長沙窯碗;如果是廣州出發(fā),在廣州的的唐代遺址很少發(fā)現(xiàn)長沙窯產(chǎn)品;而第三種較為妥當,但亦有可斟酌之處[21]。
室利佛逝等東南亞港口有作為中國貨物輸往西亞、中東、歐洲中轉港的悠久歷史,這種情況至少維持到明代。中國的貨物輸往西亞、中東或者歐洲,依靠中國商船的航海能力可能有一定的困難,而西亞和歐洲的商船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因此在東南亞中轉成為海上貿(mào)易最好的選擇。事實上在這些港口的古代遺址中經(jīng)常發(fā)現(xiàn)中國的外銷瓷器。如果“黑石號”確實是在室利佛逝港裝載了來自各地的貨物啟航的,那么,不久它就觸礁沉沒了。
也不能排除“黑石號”是從中國的港口啟航的。船上的貨物如金銀器、“江心鏡”產(chǎn)自于揚州,各地窯場的產(chǎn)品運到揚州也不存在很大的困難,而且在揚州唐代遺址發(fā)現(xiàn)了除廣東青瓷外其他“黑石號”裝載的瓷器品種。唯一的疑惑是關于廣東窯青瓷大罐內(nèi)裝有長沙窯碗作何解釋?也可以設想“黑石號”在揚州裝上除長沙窯之外的其他貨物,留出中間的艙位到廣州再裝載長沙窯瓷器和廣東青瓷。
關于“黑石號”的目的港,從目前的考古證據(jù)看,應該是西亞、中東地區(qū)。“黑石號”裝載的長沙窯、越窯瓷器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遺址、蘇丹的阿伊扎布遺址,伊拉克的薩瑪拉遺址、伊朗的尼沙布爾遺址和希拉夫遺址等地被發(fā)現(xiàn)。在柏林佩加蒙博物館的陳列室里有在伊拉克薩馬拉遺址出土的、與“黑石號”一樣的白地綠彩瓷器和白瓷,而在歐洲至今尚未有類似發(fā)現(xiàn)。因此,“黑石號”的最終目的港應該是阿拉伯帝國的某個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