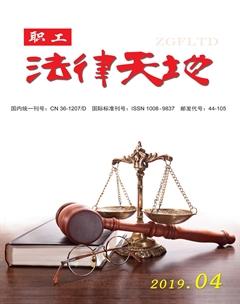民事審判中法理思維的面向
摘 要:民事審判中法理思維是對法治本質和美德的追求,并不是單純意義上所指的法律的理、法治的理和法學的理,法理思維高于法律思維和法治思維,民事審判中法理思維的面向法官,具體表現法官的裁判中的自由裁量、經驗法則、理性和案例性指導。
關鍵詞:民事審判;法理思維;自由裁量
一、引言
2019年3月16日至17日上午,第六屆“法理研究行動計劃”暨“法理思維與法律方法”學術研討會在華東政法大學召開,此次會議由華東政法大學科學研究院和法律方法研究院、《法制與社會發展》編輯部、《法律方法》編輯部共同主辦,匯聚了全國各大高校和研究機構的一百多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會議主要圍繞五個議題展開,包括法理思維、法律思維、法治思維、法律邏輯和法律方法,指明了法理思維的特征,深刻論述了法理思維、法律思維和法治思維三者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加強了法理思維與法律方法的聯系。參加會議的專家學者分別從不同的學科和領域對法理進行了論證,闡釋了法理思維在理論和實踐中的價值。使“思維”之葩裝扮了“法理”之苑,綻放出一派繁榮的學術盛景。[1]早在2017年張文顯在《清華法學》第4期就發表了名為《法理:法理學的中心主題和法學的共同關注》這一大作。張文顯教授在該文中提出,中國的法治問題實際上是法理問題,在法學研究中,要注意凝煉“法理”,要將“法理”作為中心主題,提倡法理學與部門法學要共同關注與聚焦“法理”問題,并為中國法學迎來法理時代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為中國法治實踐提供法理智識。[2]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建設法治中國離不開法理思維,法理思維的獲得需要研究和關注法理,法理是法治中國建設的理論源泉和制度基礎,通俗地講,法理思維就是把法理知識轉變為法治成果,這是一個“吸收”和“消化”環節,這個環節顯得尤為重要,民事案件的審理不僅僅只是如何適用法律,現今更多的應把重點投向法律的“理”。
二、民事審判中的法理思維
在民事案件的審判中,法官必須具有法理思維,法理思維對法官審理民事案件不可或缺,就民事審判中,法官的法理思維主要是四個方面的要求。
(一)民事審判應對經驗法則保持開放
美國著名大法官霍姆斯曾說:“法律的生命不是邏輯,而在經驗”,這充分說明了在民事審判中,經驗要素在事實的認定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民事審判的經驗是法官在長期的辦案過程中日積月累形成的,是法官對案件進行抽象、歸納而得出來的一般性結論,在民事審判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它要求的法官必須是一個生活經驗和執業經驗豐富的人,不僅需要熟悉法律知識,還能夠在民事審判中運用經驗法則進行審判。[3]南宋時期鄭克編著的《折獄龜鑒》中記載:一個賣鹽的挑夫和一個賣柴的挑夫走累了,兩個人一塊兒到樹下休息,兩個挑夫因為一塊羊皮起了爭執,相持不下,遂找到了衙門,正值雍州刺史的李惠并沒有直接審問二人,通過“拷打”羊皮,散落的鹽屑來判斷羊皮屬于誰,得出了真相。在《圣經》中也記載了依靠經驗辦案的事例,據記載,兩個女人為了爭奪一個孩子起了爭執,都稱自己是孩子的母親,裁判者所羅門見狀建議將孩子劈為兩半,兩個母親各得一半,孩子的親生母親由于愛子心切,立即放棄孩子的爭奪權,以保全孩子的性命,由此真假母親不言而明。以上所列舉的事例都是運用經驗進行審判的經典案例。
(二)法官民事審判中法官應發揮好自由裁量權
在民事案件審理中,自由裁量權并不是一個很新的概念,在西方,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就自由裁量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在裁決公義的時候,國家的法官應當擁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博登海默在《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指出法官應當擁有自由裁量權。西方國家裁量權主要是指“法官造法”,此處所討論的自由裁量權是指法官在民事審判中依據實際的情況作出的最終判定的意義上的結果。[4]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必須依據案件的事實和法律,就事實來講,實踐中案件的事實認定是最為困難的,對于已經發生過的事實我們無法復原,只能依據收集到的證據對案件進行推理,即使在現代科學技術無法捕捉人的內心活動,只能依收集到的證據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判斷。法官適用法律并非無限制的自由,而是在法律規定的范圍以內行使自己的裁量權。同時,法官自由裁量權體現在立法上,最高法和最高檢的司法解釋,對民事審判有著很大影響。
(三)法官民事審判應保持理性
法官在民事審理案件中應保持理性,2007年南京彭宇案,法官理性尤為重要,一審判決彭宇補償原告40%,合計45876元。此案主審法官放棄“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案件處于真偽不明的狀態,證明責任由誰來承擔,并不明確,焦點在老太太是自己摔倒還是彭宇撞到,沒有結論,案件在事實不明的情況下作出判決,程序不合理,實體結果很難公正。通過彭宇案,我們可以看出,民事案件的審理,程序公正尤為重要,這時法官需要保持理性。[5]
(四)法官民事審判應適用指導性案例判斷類案
關于指導性案例判案我國自古就有,并非源于現代,早在秦朝就有依據案例進行審判,名“廷行事”,經歷了漢朝和隋唐時期,一直到清朝,判例的作用依舊很高。“凡引律必全引其本文,例亦如之,有例則置其律,例有新者則置其故者”。在清代據史料記載,除了例,還存有案,主要指那些各省呈報上來的疑難案件,需請皇帝批準,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三、結語
法理思維的生命力在于實踐,民事審判作為解決民事糾紛的主要途徑,法理思維需要不斷升入民事審判中,法理在民事審判中絕不僅僅表現為民事審判制度,它是民事審判制度的升發,它是一種對法的美德的追求。
參考文獻:
[1]呂玉贊.第六屆“法理研究行動計劃”暨“法理思維與法律方法”學術會研討會述評[J].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9年(03).
[2]張文顯.法理:法理學的中心主題和法學的共同關注[J].載清華法學,2017年(04).
[3]魏加科.論經驗法則在事實認定中的作用[J].載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05(02).
[4]張軍.守法主義與裁量主義[J].載法律科學,2018(02).
[5]張靜煥.彭宇案之公民邏輯[J].載政法論叢,2008(01).
作者簡介:
郭慶(1991.9~ ),土家族,湖北巴東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法理學、法人類學。